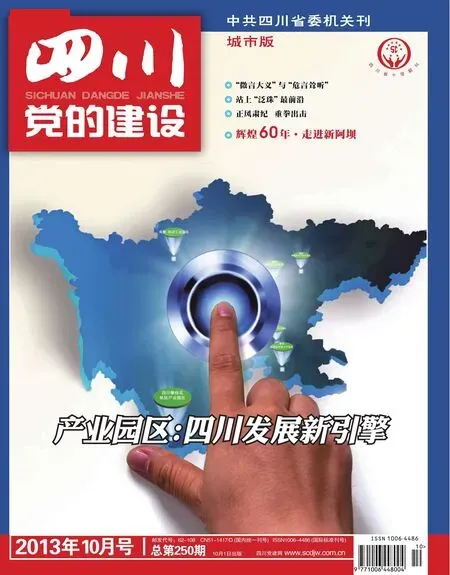八面來風
八面來風
成功與習慣
●楊新元/文
一位世界第一的推銷大師,在他結束自己的推銷生涯時,全球有5000位保險界的精英來參加他的職業生涯告別會。當許多人問他推銷的秘訣時,大師微笑不答。這時,全場的燈光暗下來了,從會場一邊出現了四位彪形大漢,他們合力抬著一個鐵架走上臺,鐵架下放著一個大鐵球。
這時,大師走上前,用一把小鐵錘朝大鐵球敲了一下,鐵球發出輕輕的響聲,卻紋絲不動。以后,大師每隔5秒鐘就用小鐵錘對著大鐵球敲一下,如此不斷。可鐵球還是一動不動,人們開始騷動,陸續有人離場而去。但大師還是一言不發,靜靜地敲著鐵球。人越走越多,留下來的所剩無幾。終于,大鐵球開始慢慢晃動。經過40多分鐘的不停敲擊,大鐵球搖晃起來,而且越晃越厲害,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能讓它停下來。這時,大師面對僅剩下來的幾個人說,他一生成功的經驗是:簡單的事情重復做!以這種持續的毅力,每天進步一點點,當成功來臨時,你擋都擋不住!
成功其實很容易。就是先養成成功的習慣!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是習慣,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也是習慣。
(摘自《人民日報》)
駕馭誘惑
●達芬奇/文
兩年前我開始玩微博,獲得了10萬粉絲,不算很多,但隨便說點兒什么都有人覺得來勁,感覺不錯。然后我的世界開始沉陷在3.5英寸的小屏幕之中。我總是舉著手機,連吃飯時都不例外。
我總是發條微博,然后期待著轉發和評論。這讓我感覺不佳。
我喝過一次某種優酪乳,好喝得要死,就再也不喝了。自然界不會產生那么美味的東西,只有化學才會。
微博也是這么回事。它制造了愉悅,但那是會讓人沮喪的愉悅。
往日生活培育了我靜水深流的怒氣,在中國這并不奇怪。我們都帶著隱隱的怒氣長大。問題是,平時可控的怒意,會在微博上爆發出來。微博像攝魂怪。我幾次陷入紛爭,當時有點兒得意,事后會后悔。
八卦、吐槽、譏諷、抖機靈,太多的表達正義感的“他媽的”,一個向往正義卻流露出惡意的地方,這就是微博。
我厭煩了。放棄微博的第一個星期我讀完了《物種起源》。我還看了一些好小說,好詩。
重要的是,入睡前的片刻你嘴角帶著微笑。這種自我認同千金難換。
如果世界上有”真正的生活“這東西,我想那就是擁有自由,自由不只是滿足誘惑,也是駕馭誘惑。
(摘自《人物》)
生活總在路口
●吳永進/文
在大街的十字路口,紅燈亮起。橫馬路上沒有車輛,于是自行車快速穿過去了,摩托車魚貫穿過去了,行人也爭先恐后地穿過去了,就連一個 “老外”東張西望了一下,也步履矯健地過去了。
只有你一個人站在那里等待,30秒,像一棵孤零零的枯樹,寂寞而形影相吊。綠燈亮了,你過馬路時已經空無一人,這時你或者自我欣賞,或者后悔不已,或者五味雜陳,或者已然習慣。
我們的日常生活往往也是這樣,在許許多多的場合中,它等待著你的選擇,取決于你的態度。有時你輕輕松松隨大流,頃刻間就習以為常地淹沒在滾滾人流之中;有時你不同尋常,那你就有悖時俗,就要承受心靈的孤寂,或許還要經受世俗的眼光。如果在思想和觀念上你要堅守什么,不想附和大多數人的聲音,那你就更可能因為清醒而成為另類,就要準備在自己的精神家園中享受孤獨了。
(摘自《解放日報》)
綁住自己的手
●馬德/文
秦國有個叫李斯的人,位高權重,臨被處以腰斬的時候,才感慨人生最美的圖景,不過是貧窮的時候,帶著獵狗,領著兒子在老家城門外追野兔玩。真可謂千年一嘆。
然而,在權力中追逐的人,不是誰給上一節課就能明白的。記得白巖松說過一句話,很形象:人人都在背后罵當官的,但看到當官的之后,都齊刷刷地站起來。
飯桌上聽得一通高論。一先生談及自己練書法的原因說,只是為了捆綁住自己的手。他說,人的手,總是想要拿些東西的。譬如,看見女人的腰,就想掐一把;看見錢,就想抓一些;看見代表權力的大印,就想據為己有……現在,我讓它抓住筆,它就不會想別的了,就會專心致志地潛心于字上。蚯蚓可以鉆到很深的地下,就是因為它卸去了所有的手腳,赤條條的,阻礙少了,就鉆得深。
眾皆驚服。
(摘自《今晚報》)
積極生活就是愛
●韓松落/文
有段時間,很喜歡法國電影,卻對法國電影里總要出現的“愛”感到不耐。
以法國女歌手伊迪斯·皮亞芙生平故事為主線的電影《玫瑰人生》里,記者向坐在海灘上的皮亞芙發問:“您對少女們有什么建議嗎?”“愛。”“您對青年們有什么建議嗎?”“愛。”“您對孩子們有什么建議嗎?”“愛。”……在法國電影里,愛是最重要的事,電影里的男人女人,不斷地告訴自己和別人,要愛,要示愛,要落實愛。
后來讀到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的書《愛的多重奏》,這是他在71歲時一次訪談的文字稿。此時的他,清澈洞明,對這種“愛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深刻的闡述。他所論述的愛,是愛情,但又不僅僅是愛情。人本來是單個的,以單數形式存在,而愛情,卻讓人從“一”變“兩”,在這個過程里,人得打破自己身上的封閉,試著通過另一個人的角度去看世界。兩個人的愛,是“最小的共產主義單位”,但這種形式,卻是一種更大規模的集體之愛的演習,讓“從兩個人過渡到人民”成為可能。
在他看來,愛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得靠忠誠去維護,得不停地宣示愛意,“盡管在一開始就已經宣布,愛仍然需要不斷地被重新宣布”。而這,顯然需要巨大的行動力,需要不斷激發自己身上的熱情和能量,所以,他所謂的愛,是一種更樸實的態度:積極生活。去愛,去行動,去寄托,去反省,去剔除焦慮,去解決不安,去認識命運,去抵抗死亡。
(摘自《廣州日報》)
我為何依然相信讀書改變人生
●王強/文
北大出了許多企業家,這讓我非常自豪。
以北大的32樓為例,當年我和俞敏洪作為北大青年教師住在該樓的第二層。后來俞敏洪創辦了“新東方”,成了知名企業家。第三層樓,當年住著一個來自山西的青年,他叫李彥宏,天天在水房里光著上半身用冷水沖澡,唱著“夜里尋他千百度,你在哪兒呢”,天天念“百度”兩個字,于是后來誕生了百度公司。他是圖書館系古典文獻編目專業的。第四層樓住著北大中文系的憤怒詩人黃怒波。這些年來黃怒波令人刮目相看,成為中坤集團的創始人,在冰島購置土地。更匪夷所思的是,北大中文系的女生樓里一個長相平平的人叫龔海燕,她充滿激情,創辦了世紀佳緣。
英文系、圖書館系、中文系都是與金融、融資、管理無關的專業,但是學這些專業的人怎么會創建成功的企業?我想,是讀經典,讀那些能夠改變我們生命軌跡的書籍,這成為北大人走出校門后,不管走進哪個領域,能比別人走得稍微遠一點兒的保證。
我不讀暢銷書,不是我看不起暢銷書,而是我知道生命有限,只能讀人類歷史上經過大浪淘沙的作品。如果你讀的不是真文字,遇到的不是真語言,那么最后見到的也一定不是真實的世界。
(摘自《中國科學報》)
(責編:張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