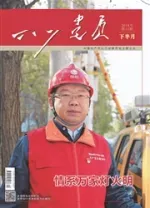“救命車”難暢行
2012年12月7日,北京一名騎車人遭遇車禍。救護(hù)車及時趕到,在趕往醫(yī)院的路上卻遭遇堵車,鮮有車輛避讓。傷者最終因延誤救援而導(dǎo)致死亡。
20 12年12月7日17時58分,北京急救中心接到呼救電話,醫(yī)生王雨竹、司機(jī)張少軍等人僅用5分鐘就趕到車禍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一位55歲的女性被罐車輾軋,已生命垂危。王雨竹與同事一邊進(jìn)行緊急搶救,一邊催促司機(jī)開往距事發(fā)地點(diǎn)僅3公里的武警總醫(yī)院。
然而,當(dāng)時正值周五晚高峰,路上水泄不通。據(jù)王雨竹回憶,盡管急救車響著警笛,但很少有車輛避讓。“傷者脈搏微弱,每分鐘呼吸只有兩三次。”王雨竹讓司機(jī)逆行進(jìn)入對面車道,爭取搶先通過前方路口。可一變綠燈,對面的車輛便快速駛來,堵住了去路。
搶救一刻不停地進(jìn)行,傷者的生命跡象卻在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消失。“急救車走走停停,約40分鐘后才把傷者送到醫(yī)院,但傷者心跳已經(jīng)歸零。”這是王雨竹從業(yè)以來“最慘烈的一次搶救”。“一路上,及時避讓的社會車輛不超過4輛。”
急救車上的北京一夜
2012年12月11日晚8時到12日早8時,記者全程跟隨一輛北京的120急救車,親歷了“與死神搶時間”的艱辛路程。
11日19時57分,急救車接到任務(wù),趕往3公里外的車禍現(xiàn)場。此時,交通晚高峰還沒結(jié)束。急救車被堵在車流中緩慢前進(jìn),在有應(yīng)急車道的地方,司機(jī)還能一邊拉響警笛一邊勉強(qiáng)從車縫間穿過,更多時候,在普通路段,這輛車只能混在社會車輛中行進(jìn)。在路口,急救車敢闖紅燈的情況是極少數(shù),因?yàn)椤皞?cè)面來的車可不減速”;在人行道前,泛濫的“人車搶道”現(xiàn)象,也沒給急救車“開特赦”。
在閃燈、鳴笛等手段并用后,急救車于20時12分趕到車禍現(xiàn)場,耗時15分鐘。司機(jī)小唐評價:“這已是不錯的成績。”“最夸張的一次,五六公里的路我跑了1個多小時。”小唐說,他和同事們戲稱二環(huán)內(nèi)的道路為“流動停車場”,且“全天無休”;五環(huán)外略好一些,但晚高峰時也“基本沒戲”。

北京的晝與夜,確實(shí)對急救車通行展露了不同面目。在7次急救任務(wù)當(dāng)中,記者對該車從出發(fā)到抵達(dá)病人身邊的平均速度進(jìn)行粗略計算發(fā)現(xiàn),夜班平均每公里僅需耗時兩分鐘,其中凌晨四五點(diǎn)鐘時僅需1.1分鐘;在白晝的頭與尾,則已逼近每公里5分鐘。
急救者心中的擁堵地圖
北京急救中心每個司機(jī)和醫(yī)生心里都有一個“擁堵地圖”。王雨竹說:“一聽出事兒地點(diǎn),就能判斷是否麻煩。”“永定路、定慧橋……”急救車司機(jī)張少軍隨口就能說出一串愛堵車的地區(qū)。甚至即使到了醫(yī)院門口,也常常遭遇堵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交通管理工程系副教授高萬云說,在國外,應(yīng)急車道是生命線,沒有車輛會占用。而在國內(nèi),只要堵車,應(yīng)急車道必然停滿了車。
消防車同樣遭遇堵車?yán)Ь帧?012年2月16日晚,北京市簋街一家飯館起火,消防車快到火災(zāi)現(xiàn)場時遭遇堵車。消防車打方向燈希望并線,但后面的小車堅決不避讓,還并線超車。“每輛消防車都有各自的任務(wù)和分工,到達(dá)現(xiàn)場后需要協(xié)同作戰(zhàn),如果一輛車被堵,可能就會耽誤整個滅火救援工作。”北京市東城公安消防支隊地壇中隊消防車司機(jī)徐熙說。
北京市公安消防局西直門消防中隊中隊長張永說:“我們的轄區(qū)不大,但正好在二環(huán)內(nèi),特別是晚高峰時,出一趟火警要比平時多花出一倍的時間,出警的時間大部分耽誤在路上。”
為“救命車”讓道是為自己讓道
王雨竹坦言,可能確實(shí)有人想避讓急救車,但不知道怎么讓路。“有一輛轎車為了避讓我們,竟然沖到便道上,差點(diǎn)造成翻車。”記者隨機(jī)采訪的多名司機(jī)表示,最好是在駕校時就培訓(xùn)司機(jī)避讓特種車輛。
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范達(dá)說,立法懲處不避讓急救車的行為是一方面,而制定并向公眾普及避讓急救車的方法,教人們?nèi)绾巍昂戏ū茏尅保瑯又匾?/p>
“的哥”王宏奎師傅表示,很多時候不是不愿意讓路,而是怕由此引發(fā)交通違法行為甚至事故。王宏奎等司機(jī)表示,希望完善交通法規(guī),打消司機(jī)“讓車后造成違法可能挨罰”的疑慮。
張智新說,一方面,要完善交通法規(guī),對避讓特種車的司機(jī)免責(zé);另一方面,對占用應(yīng)急車道的行為要加大處罰力度。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遇險,為‘救命車’讓道,歸根結(jié)底是每個人在為自己讓道。”王雨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