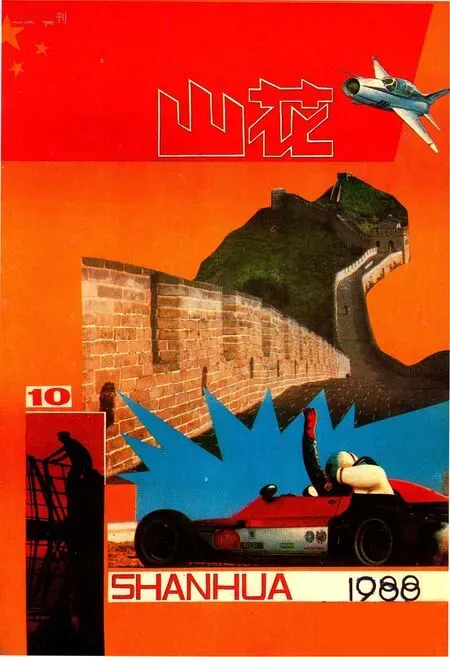因拙出古、因古出簡——黔東南苗族圖案造型的審美特征
陳明春
黔東南的苗族圖案造型形態各異,相較于其他少數民族的裝飾圖案顯現出鮮明的個體性特征,這種現象的發生是與其自足的民族文化圈密不可分的。這些圖案主要依附于苗族刺繡、織錦、蠟染、剪紙等藝術載體之上,其圖案造型藝術呈現出統一形態之下的多元化,而這個統一的形態特征可歸納為:古、拙、簡的象征主義風格特點,即因拙出古,因古出簡。下面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究其類型特征。
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圖案風格類型
首先,拙、古、簡的審美特征主要來自于黔東南苗族裝飾圖案的風格特征,從構成元素與觀看方式上來看,苗族圖案造型大致可以分為幾何抽象型圖案和非幾何抽象型圖案。
(一)古拙簡單的符號化幾何抽象圖案為主的類型
黔東南苗族的幾何化圖案類型可以大體分為以下幾種。
1.柳富型,主體圖案常常為菱形紋樣或回紋變體等幾何紋樣,底色通常為青黑色,先在其上挑花再施以錫片,挑花顏色一般為深藍、深紫和黑色。
2.舟溪型,紋樣通常采用獨立的幾何花紋排列,如三角紋、井字紋、卍字紋、三角齒輪太陽紋、井字勾云紋。單個花紋單色,常用紅、黃、綠、藍、白以線條的方式表現而非色塊。
3.黃平型,通常使用黑色中帶有青紫色的底布,紋樣以紅色為主調,間或夾雜一些藍色,而鎖線施以橘紅色,配以白色短折線,圖案常常具有交錯型視錯覺的意味,例如單個紋樣看蝴蝶圖案,其中線條又與周邊幾何色塊組成其他紋樣。
4.公俄型,善用水流旋渦紋樣,紋樣用黑布剪出來,貼在紅布底上,再用梗線扣住輪廓邊線,梗線多加金箔紙包裹。
5.芭莎型的服飾和獵帶上的挑花與其他類型的幾何紋樣有較大區別,常在深色土布上繡上白色的曲線形狀,帶有強烈鋸齒狀邊緣。
6.黎平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通常以菱形紋樣為基礎,一切輔助性紋樣都是沿著菱形的邊框做基型,這些輔助形主要包括曲折三角波紋與抽象的鳥紋等。
綜合幾種類型的圖案造型對比,可以發現:幾何型圖案最大的特點便是簡單而稚拙,無論幾何形體的構成還是色彩的搭配,都體現出古拙與質樸的特征,簡單的造型基礎,加之單純的整體造型效果,正說明其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整體風貌,這一點與中原地區原始彩陶上的裝飾造型紋樣還是存在某種姻親關系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為什么中原地區強烈的幾何型圖案造型最終走向了勢微,而苗族的幾何型裝飾圖案卻始終經久不衰地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筆者認為,這從幾何型圖案在藝術史中的演變過程可見一斑。原始幾何紋的最早發現其實可以認為是原始藝術家主體對客體形象的簡單模仿,是繪畫和文字的最早雛形,但是隨著象形文字及書寫的自足以及審美獨立性的不斷彰顯,中原地區的幾何圖案基本走下了神圣的祭壇,而與之相對的是,苗族藝術中始終沿襲著這套運用幾何圖案代替文字系統表情達意的藝術史,因此因拙出古的幾何型圖案是由苗族藝術史的邏輯關系所決定的,而因古出簡的幾何造型特征則是苗族藝術在藝術史的沉淀中對幾何紋樣不斷探索、精簡與再現的結果,是幾何型圖案在藝術史的演變中不斷現代化的選擇。
(二)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超象形圖案類型
從視覺文化學角度上來講,非幾何抽象形圖案可定義為超象形圖案。通過實地考察,筆者以為,苗族圖案造型在本質屬性上并不存在可以定義為具象的圖式,而某些特定的圖案樣式也不可以僵硬地套用既有概念,定義為非此即彼的類型,因此經過多年的研究,筆者提出超象形圖案這一概念。那么,何謂超象形圖案?超象形圖案是特指在苗族裝飾圖案語境中,苗族藝術家通過在具象、抽象與意象藝術形式中運用解構和抽繹等創作方式,塑造、組合、重構而成的,具備超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體系。而超象形圖案造型是黔東南苗族人民借助拙、古、簡的審美觀念,借助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手法,在具象、抽象與意象藝術形式中選擇圖像元素,進行組合的圖案造型方式。黔東南苗族裝飾圖案正是借助幾何抽象化圖案與超象型圖案來體現其古拙厚重與簡約的審美觀念的,下面分別就這一點對苗族圖案風格的兩種類型加以具體分析。
1.凱棠型,黃平型的一支,主要紋樣有鳥紋、魚紋、龍紋、銀杏葉紋等,輔助紋樣一般使用幾何紋。
2.都柳江上游型,長于表現動物紋樣,通常出現的內容有鳥、龍、蝴蝶、魚、龜、蛙、貓頭鷹眼、蛇,甚至穿山甲等,造型比較粗獷野性、豪放不羈。
3.施洞型,相較于其他類型,更有繪畫性。本類型的重要特征是所有動物都是天馬行空的超現實塑造,拼接、抽象化的動物居多。比如人、動物、植物的組合、不同動物的形象組合、動物軀干內部如同懷孕一樣包含其他動物或人、雙頭或雙身動物,甚至單獨的一個獸頭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本類型與都柳江上游型、巴拉河型有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龍圖案紋樣出現的頻率之高,在全國少數民族藝術中是絕無僅有的。
4.巴拉河型,表現內容主要以動物為主,但類型比施洞型少,主要集中于龍、魚、雞、飛鳥、蝴蝶、蝙蝠、蛇、狗、獅子等。尤其是龍的變化比較多,比如蠶龍、飛龍、雙身龍等,配合的植物紋樣主要為桃子、葫蘆、石榴與其他小花草等。
從以上幾種超象型圖案的造型特征中,我們不難看出超象型圖案在造型特征趨向于圖案的組合、超現實的變型及符號的指代,但是圖案與圖案間的可識別性及意義的指代卻是相對具象而容易辨認的,這說明超象型圖案的表現手法是單純而直觀的。通過資料考證,這種圖案的表現形式與苗族藝術史上所載的圖案形式并無二致,此裝飾表現手法正是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集中體現。在超象型圖案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苗龍圖案,與中原文化中龍所表示的權力象征意義截然不同,苗族所奉的龍一直保持著純樸的自然神格和神性,視龍為保寨安民、賜福賜子予人的善神,它既是水神,又是山神、土地神、家神、寨神、祖先神、生殖神。苗龍圖案更多地體現出古拙與簡率性特征,而中原地區的龍圖案則與權力和政治息息相關,所以未曾出現苗族龍圖案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裝飾造型意味,二者只是在整體外觀形象上接近而已,其表現方法和造型意義實則天壤之別。
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審美特征
(一)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高度概括與抽繹
苗族圖案紋樣具有高度概括的特征,這并不能解讀為表現手法的簡單,相反,高度提煉與概括形象,使之純粹化是幾千年來苗族藝術史的積淀,體現出苗族藝術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高度概括與抽離的審美取向。
苗族圖案造型中常見的有龍紋、鳥紋、魚紋、蠶紋、回紋等,尤其是龍紋、鳥紋與回紋(云雷紋),雖然與中原藝術圖案存在造型上的酷肖性,但是造型的審美趣味是完全不同的。毫無疑問,苗族圖案的審美趣味與神話是密不可分的,苗族圖案中的鳥紋樣反映的基本上是對鹡鵒鳥的崇拜,但是由于鹡鵒鳥的形象在傳說中并無明確限定,所以在實際圖案概括上,往往出現多元化的形象特征,苗族藝術家往往汲取孔雀、錦雞等的造型特征,加以形式上的參考與糅合,卻并無統一的審美要求,反映出苗族圖案審美中自然、原始、隨意的審美特征,它并沒有中原相對一元化的造型和審美標準那樣嚴苛。
造型的抽離主要體現在對動物形象元素,進行著超象化的變形夸張和抽象概括,例如苗龍造型與任意動植物進行結合,從而形成牛龍、鳥龍、蝴蝶龍、蜈蚣龍、蛇龍、樹龍、蠶龍、人頭龍、虎龍、魚龍等怪譎而動人的形象。
苗族裝飾圖案從藝術美學的角度看,比中原地區的審美趣味更具有因拙出古、因古出簡古格厚重的審美傾向。
(二)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苗族女性裝飾圖案
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苗族女性裝飾圖案主要體現在何處呢?苗族女藝術家通常更專注于點、線、面與色彩搭配是否合乎規范與美觀的搭配,這更加接近藝術創造的本質。由于苗族社會經歷了較長時期的母系氏族社會遺存,苗族婦女對家族事務與藝術傳統的影響力是漢族婦女不能比擬的。這些社會學特征也同樣反映在了苗族圖形藝術中,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圖案的構成方式中得到論證。
苗族圖案藝術中的人物或動植物形象都通常具有圓弧的外輪廓,具有柔軟的形象特征,氣氛是追求和諧愉悅的、不具有侵略性的主體在創作中的意志比表現客體更占有絕對的支配地位。這種女性藝術的特征同樣可以見于中原地區的剪紙藝術,剪紙藝術作為主要是女性參與的活動,曾深深地影響過西方立體派的發展。剪紙作為刺繡之前的準備工作,并不是中國的主流藝術形式,同男性藝術中或雄奇或秀美的藝術審美形式也存在很大的不同。由于女性本體特征和社會特征所限,苗族女性藝術家大多根據裝飾特征要求,結合苗族地區的苗歌文化等日常文化經驗,進行大小與形體的安排,她們去除了男性藝術中令人畏懼的形象特征,更多表現出一種母性的柔和與親切的藝術審美趣味,這樣反而讓裝飾圖案具有古拙簡率的民族女性裝飾韻味。但幾者間存在著共通的地方,便是它們都來自于傳統藝術史的邏輯體系之內,因此無論作為女性藝術的剪紙還是苗繡,它們的視覺審美中都無所不在地滲透著古拙、簡單、樸素,正是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集中體現。
重復是設計圖案常用的一種基本手法,苗族圖案通常都慣于使用重復這一基本手段。但是,應該注意的是,在苗族圖案中的主要形象中,重復手法使用得極為頻繁。這應該說與女性藝術中不突出對比而重視和諧有密切關系。而且重復手法的使用,始終調和在女性藝術的整體審美基調——拙古、簡率之中,因此,凡是我們可以發現在苗族女性藝術家所創作的裝飾圖案中,無論造型形式如何變換,始終控制在或圓形或方形或三角形的原始構圖形式之內,隨著幾千年的苗族藝術史發展而依然亙古不變,信守著那份古拙而又簡率的審美情懷。這種審美特征于作為他者的我們來看或許是單純的、簡單的,但是對于苗族藝術的審美范疇來說卻是華麗、厚重與完美的。
除此之外,苗族圖案風格造型中還有鮮明的古拙、簡率的寓意特征,這是與苗人的審美需求密不可分的。
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圖案造型寓意轉換
(一)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娛神寓意特征
苗族圖案藝術走向娛神寓意特征的體現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內容:首先是族父崇拜。在苗族圖案藝術的題材中常常出現某些龍形象像懷孕一樣掏空來放置人的形象,不是代表龍把人吃了,而是代表人馴服龍、戰勝龍的騎龍形象,而這基本上都是贊頌姜央這一苗族傳說中人類祖先的光榮事跡,又如紀念蚩尤的部分,傳說蚩尤部落的圖騰是龍、鳥與楓香樹,而炎黃聯軍抓住蚩尤后以楓香木作枷鎖鎖住蚩尤以羞辱三苗,這些圖騰紋樣在苗族服飾圖案中流傳至今。其次是圍繞農業生產、生殖崇拜與消災祈福等意象的鬼神信仰,苗族崇拜龍和牛,農業意象是龍主水、牛主力的本體意識功能化、具象化。苗族鬼神不分,萬物有靈的觀念下,信奉的鬼神數量多不勝數,且每一種都有專門的剪紙神像、祭品、祭祀方式和禱詞,而苗族相信鬼神有善惡之分,使用正確的方式對待,就有良好的祈愿消災效果。再次是有關圖騰崇拜的范疇,在苗族人民的圖騰形象中,是以多個形象組合在一起表現的,苗族人民對圖騰形象的表現是可以多個同時出現的。最后是對巫術祭祀活動進行裝飾,增加神秘的氛圍,最常見的是在鼓藏節等苗族重大節日中的裝飾運用。通過以上分析,可以顯見古代苗族的圖案造型寓意深受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輻射,其審美取向和實際功能都是文化史帶給其的深深烙印,無論是族父崇拜的寓意指向還是圖騰形象中的寓意擇取,都沒有脫離古拙、簡率的統一寓意指向而泛化為娛神。但是,隨著本土化藝術的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古代苗族藝術娛神的寓意指向也在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統一形態下,逐漸發生從娛神向娛人寓意的轉換。
(二)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娛人寓意特征轉換
在苗族藝術儀式性的發展史中,藝術也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劇,發生著轉換,即便如此其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美學基調仍占有支配地位。黔東南苗族圖案藝術這種“藝術的衍生品”逐漸減淡或脫離原有的巫術意味,不斷增加了“娛人”的意味。
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苗族藝術觀念正是黔東南苗族裝飾圖案造型的依據和目的。這些我們均可以在黔東南苗族的圖案風格類型和審美特征以及因拙出古、因古出簡的圖案造型寓意轉換中搜尋到苗族藝術家在圖案造型藝術上對這一審美特征的終極探索。
[1]王世德.美學辭典[M].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223-224.
[2]鐘濤.苗繡苗錦[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4.
[3]張錦華.苗族民間美術[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7:55-56.
[4]羅義群.中國苗族巫術透視[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96.
[5]張錦華.貴州民族民間文化考察錄[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