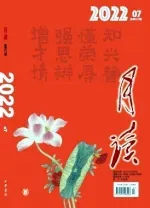木蘭柴
〔唐〕王維
秋山斂余照,飛鳥逐前侶。
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品讀
自蘇軾以“詩中有畫”論王維后,以畫境、畫藝闡發(fā)王維詩者代不絕人。但詩和畫的區(qū)別,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形式和技藝上。詩歌的本質(zhì)是抒情的,其語言有敘述性特點;繪畫是以線條和色彩一次性展示的,目的在于呈現(xiàn)某種存在的狀態(tài)。或傳情或示境,各有側(cè)重,這在王維之前是十分清晰的。而以繪畫的方式寫詩,可能意味著:一要有抒情的需要,二是不希望讀者看到自己的情感過程,由此導(dǎo)致迷戀于情感被消解時的姿態(tài)。打個比方,“詩中有畫”就如一池清水,不管水的深處經(jīng)歷了怎樣的動蕩,它所顯示出來的,只是水面上一圈圈優(yōu)美的漣漪。
王維最先勘破了這層秘密,并對這種手段樂此不疲。
《木蘭柴》是一首典型的“詩中有畫”之作。畫卷從一個秋天的傍晚鋪開,夕陽西下時,山嵐重疊處,層林盡染,倦鳥知還,寧靜的畫面上流淌著讓人感動的脈脈溫情。“時分明”即言“一時分明”,“無處所”則指“無所定處”。詩歌的后兩句是說:隨著光線漸漸下沉,林間妖嬈的色彩也隨之黯淡,就在它們即將完全湮滅的時候,山間生出了飄渺的煙靄,裊裊蕩漾,宛如仙境。這是一個完整的畫境,它似乎再現(xiàn)了陶淵明《飲酒》詩中的“真意”,是一首自然的頌歌。但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比起陶詩來,王維的“畫境”少了感悟的過程,因此,這份“真意”來歷有些可疑,而且表現(xiàn)得也不那么確定。看起來圓滿的“畫境”,其實無法掩飾由殘陽、孤鳥、迷霧所透露出的殘缺和脆弱。
詩人將情感的線索刻意隱藏了起來,給我們留下的是一個只能觀賞的畫境。但是,被畫境掩飾起來的情感線索對讀者有著吸引力,而重擬這一情感事實也就成了解詩者最大的誘惑。雖然它可能永遠(yuǎn)得不到證實,但每一種合理性都會提供一重意義,不是為王維,而是為讀詩的人。
有什么值得王維掩飾呢?最讓王維不能忘懷的大約就是安史之亂中的經(jīng)歷了。有被叛軍俘虜?shù)拿惯\,卻沒有從容赴死的勇氣,王維只能做一個貳臣。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王維一直沿著佛性的微光穿越生命的甬道,以為已經(jīng)放下了塵世萬千俗累,卻終究在這個難以回身的時刻,與自己貪生怕死的肉身狹路相逢。這一次,他得以真正認(rèn)識自己的懦弱,并毫不留情地展示在眾人面前,這種糟糕的感覺,化為石猴頭上一圈致命的金箍。更可悲的是,他無從辯駁。能說什么呢?他就是一個失節(jié)的人,再多的理由也改變不了這一事實。更何況,不需要他的解釋,大家已經(jīng)仁慈地原諒他了。杜甫“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yīng)有作,試誦白頭吟”(《奉贈王中允維》)的勸慰,還有“肅宗嘉之”的恩典,魚貫而入,鎖住了他正要發(fā)聲的喉。于是被囚禁時所受的羞辱和折磨,擔(dān)任偽職時的怯懦和煎熬,劫后重生的愧悔和心悸,都像初冬樹上掛著的寒蟬,張大了嘴,卻再也用不著歌唱。在對自己的厭惡與憐憫中,他感受到虛無和孤獨。
在此后的詩作中,王維一層一層地掩蓋起甚至是否定自己的自責(zé)、反省、悲哀等感情,但他卻無法擺脫這些沉重的感覺,于是,就在這欲言又止的感嘆中,打磨出一個又一個越來越圓融的畫境,宛若天成。《木蘭柴》正是這樣的詩。詩人隱入山谷落日里,把自己的心事交付給尋尋覓覓的飛鳥,木蘭光澤的明滅也一定觸動了他什么,但詩人將一切都藏在漂浮不定的云氣里,只一句“夕嵐無處所”,隱約地暗示了人生的殘缺和夢幻。王維早年就擅長的描寫手法至此發(fā)揮到了極致。《輞川集》二十首,幾乎首首如此。那些切齒痛恨或者切膚痛惜過的情感,通通化蛹為蝶,抽身而去,只留下薄薄的軀殼,搭成一片片云淡風(fēng)輕的風(fēng)景,而他則永遠(yuǎn)地退到一旁,成為了自己的觀眾。
我們的猜測也只能走到這一步。唯有退回到警戒線以外,放棄追問,才能重新看到這幅略帶憂傷但終究是明媚鮮妍的畫,還散發(fā)著夕陽漫過山谷的溫度。這正是王維所希望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詩中的畫境是他的無弦琴,隨著時間的滌蕩,所有難以啟齒的歌唱都會變成無跡可尋的《廣陵散》。當(dāng)我們再提起王維,腦中只會浮現(xiàn)出一個又一個無限優(yōu)美澄澈的畫境,空靈若夢。那些他不愿提及也無法言說的,都不復(fù)存在。這些無限近乎于完滿的畫境,總會留下這樣那樣的光影交錯的破綻,在這無法彌合的破綻中,隱藏著王維自我救贖之路,也能使我們“看見自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