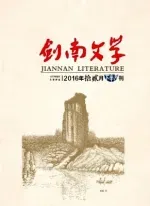一朵落寞凋零的玫瑰——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 《紀念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
■魏笑甜
引言
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蜚聲世界文壇的一位美國文學大家。他在文學上成就突出,且因其善于將南方的歷史記實和社會現實相結合作為自己的不竭創作之源,而成為美國南方文學的偉大代表,并于194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20世紀上半葉這個沉浮激蕩的社會漩流中,其作品對女性問題作出了極多的描繪與關注。在其最重要的創作成就即規模宏大的 “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中,他為讀者呈現出了一幅幅逼真的南方社會變遷的歷史畫面。其中社會環境不一、人物類型豐富、意識描寫出奇、哥特式的恐怖等特點都為這一創作世系披上了多面的研究價值。人物類型與精神層面的多樣性描寫之一,就表現在這些畫面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她們人物豐富、個性突出、階層不一、命運不濟。這些多重的女性形象貌似一個極富特色的女性王國,每一個形象都充滿了不泯的愛恨情仇,但這樣的、在當時被視為弱勢者的女性們卻往往以悲劇收場。到底是何源流致使了這樣的女性命運悲劇?
《紀念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 (以下簡稱 《艾米麗》)是福克納最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之一。艾米麗是南方種植園主格爾尼之女,也是一位南方沒落貴族,她的一生是離群索居的、充滿悲劇性的一生。時代賦予她 “南方淑女”的言行桎梏,但她卻以一生的怪異、孤僻、為愛瘋狂來予以其痛心疾首的反擊。這樣一個受盡舊傳統束縛的 “南方淑女”凄苦悲慘的一生,卻以縮影般反饋著當時美國傳統觀念所遺留下來的陳腐思想與門第觀,反映著社會對女性基本生存權利的無情剝奪,更反映出抗爭男權社會的南方婦女的渺小和不幸。基于此,本文試圖從女性主義批評角度對此問題做一思考,進一步探討造成愛米麗悲劇一生的致命之源。本文大致將其悲劇成因歸結為以下兩大方面根源:一、舊傳統觀念;二、女性愛的本真與死的反抗。
舊傳統觀念
舊傳統觀可以說是造成艾米麗悲劇性的基礎根源。傳統觀念是一個社會長期發展著的本元反映,但陳舊腐朽的思想觀念卻是毒害人心的致命之膏。在美國社會的長期發展中所形成的某些 “清規戒律”剝奪了艾米麗作為一名自由女性的生存權;而社會中無意識的男權制更是成為了艾米麗悲劇一生的催化劑。福克納曾經說過“這是一個被性政治制度殘害、背叛的一個女人的故事”,這里 “性制度”最重要的一面無疑是指在當時社會的清教束縛下的“清規戒律”。父權制讓艾米麗孤僻寂寞、離群索居一生,而清教思想卻 “成就”了她發瘋、怪異、病態的一生。艾米麗就是這樣一個在精神與肉體上受盡南方傳統觀念迫害的結合體,其精神存在與生物存在皆受到社會的畸形對待。
“清規戒律”的束縛
美國南方社會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信仰,其清教思想更是占據信仰主流。清教思想下的婦女觀對女性的束縛使之不能擁有女性正常的自由輿論、平等婚戀等權利。基督教完全將女性視為男性的附庸品,把女性置于從屬地位: 《圣經》中女人依附于男人的故事大量存在,如 《舊約》中男人用肋骨創造出女人、女人原罪說等無一不體現著女性地位的低下與附庸狀態。另外,清教下的婦女還必須遵守著 “貞操是道德之最”、 “淑女風范”的思想桎梏,“南方淑女”將女性束縛在不自由的言行禁錮下,婦女的貞潔更是神圣而不可侵的禁域。這種婦道觀下的南方女性失去了自由的婚戀、平等選擇等種種權利,更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了。艾米麗是這種畸形觀念擠壓下的典型受害者。
艾米麗自小生活于清教的氛圍之中,父親將其視為 “淑女風范”的培養品,鎮上的人們也將其視為 “一個傳統的化身,是義務的象征”,無論她的一舉一動還是一言一行,勢必受到人們的窺視與評論,一切清教規范以外的言行則會受到人們惡狠的指責;貴族社會特有的道德標準也 “規范”著她作為貴族女人以外的一切行動,她的普通女人資格是被剝奪了的,因為她必須是 “淑女般”的 “高貴、完美、貞潔”的化身。
傳統勢力與清教觀念一步步破壞了艾米麗的愛情,使艾米麗的希望稍縱即逝。身心受到極度壓抑的她變得更加孤僻和厭世。哀莫大于心死,最后艾米麗以毒死戀人的手段來保住得來不易的愛情,并與情人的尸體共枕來使其長久。在一切的希望破滅后,艾米麗終于一步步邁入了精神扭曲的深淵。
男權制的壓迫
《圣經》里有這么一個常理:正是因為夏娃經不起誘惑,人類才失去了伊甸園,墜入了無窮的苦難之中。婦女因此而成為萬惡之源,世世代代備受責難。女人附庸于男人這一觀點從遠古開始便顯得是天經地義的,因此對基督教根深蒂固的歐美國家來說,從創世紀的伊始便決定了女人永遠是男人的附屬品。男權制的社會里,夏娃誘惑亞當偷食禁果而雙雙被逐出伊甸園后, “原罪”、 “紅顏禍水”似乎成為了女性的代名詞。而父權制的社會里,男主女次的二元論思想根深蒂固,女性不再是生物上的女性,而是社會賦予她們自身的女性主體。她們所能做的只有無限制地服從男權的統治,女性的反抗力及獨立性的思想一點一滴地被磨平,從而女性這一群體的被壓迫、被束縛這樣的有意識便慢慢轉入無意識,甚至對男權統治的服從已慢慢被女性群體接受、直至被視為天經地義的社會理規。
父權主義思想是美國南方這個男權社會最顯著的傳統。艾米麗的父親便是這樣一個父權主義思想充斥的典型形象。他在家里是主宰一切的中心與權威,包括主宰他的女兒艾米麗的一生,甚至是在這個暴君式的人物死去以后,他仍然控制和影響著艾米麗,是艾米麗悲劇一生的重要根源。例如, 《艾米麗》中有這么幾副經典畫面:
“長久以來,我們把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畫中的人物:身段苗條、身著白衣的艾米麗小姐立在背后,她父親叉開雙腳的側影在前面,手執一根馬鞭,一扇向后開的前門恰好嵌住了他們倆的身影。”
“全鎮的人都跑來看看覆蓋著鮮花的愛米麗小姐的尸體。停尸架上方懸掛著她父親的炭筆畫像,一臉深刻沉思的表情”
第一幅畫面中:艾米麗 “身段苗條、身著白衣”象征著她的 “南方淑女”風范;“身穿白衣的艾米麗小姐立在背后”表現了父親對她的絕對統治以及她對父親的依賴與順從;艾米麗的父親 “叉開雙腳的側影在前面”則體現了父親在這個家庭里的統治權威; “手執馬鞭”象征著父親的絕對統治權和高傲的貴族態度,他無視那些求婚者,認為沒有人有資格來高攀他的家庭和女兒,他趕走了所有的求婚者,但是他卻從未過問過艾米麗的真實情感。因此,種種跡象表明了父親對艾米麗的絕對統治。在父親的威嚴 “保護”下,艾米麗沒有與外人和社會接觸、交流的機會,再加上從小受到的 “淑女”教育,艾米麗便慢慢成了一位高傲、乖戾、孤僻的女性,這也為她后來病態般的行為埋下了伏筆。在艾米麗父親眼中,她必須秉承一切規則來延續貴族家庭中的風范,這么一個大眾化的“南方淑女”教育使艾米麗失去了正常的人格特性,雖然她后來的行為并非符合 “淑女風范”的教育結果,但她的個性卻向相反的另一個極端無限發展。這么一幅畫生動地顯示出了男權社會對艾米麗的直接作用。
艾米麗喪失了自我意識,一切都以父親為標榜和中心,在父親死后,她更是無法接受這一現實。 “艾米麗小姐在家門口接待她們,衣著和平日一樣,臉上沒有一絲哀愁。她告訴她們,她的父親并未死。”以至于,她最后甚至拒絕掩埋父親的尸體。艾米麗這一舉動表明了他對父親統治的依賴,失去父親她不知該如何面對生活。波伏娃說在她的 《第二性》中提出: “一個女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是說是 ‘形成’的”。那么可以說艾米麗這個前半生乖巧、后半生瘋狂的女性便是在男權中心社會中所形成的一個特殊的顯示體。“愛米麗小姐的停尸架上方懸掛著她父親的炭筆畫像”,這么一副震撼人心、對比強烈的畫面足可以看出艾米麗至死都被父親的陰影籠罩著。
女性愛的本真與死的反抗
女性在后天社會中被動形成 “女性”的觀點是女性主義最成功的解說之一,對男權社會中女性問題的透徹分析更加加速了女性主義批評的深刻性與價值性。日本學者常認為 “死是最高的藝術,是美得一種表現,死是生的延伸”,其審美傾向也表現出 “生追求美、美是虛無、虛無即死、死就是美”這樣的特點。女性主義批評家雖并非如此哀婉、如此崇尚死亡之美,但不可否認,對艾米麗來說死亡的確意味著超脫,意味著生命的延伸,甚至意味著對愛情的永恒擁有。
愛的本真是女人的天性,一段純潔至上的愛情往往是每一個女性的向往與追求,這種權利本不該受到任何阻拌,但現實往往是殘酷的。艾米麗并非柔弱、順從一輩,她的孤僻、乖張、瘋狂可謂是一種對男性社會的反抗。她把收稅的人 “連人帶馬”地打敗了。當藥店的藥劑師尋問她買砒霜的目的時,她那冷漠的臉 “像一面拉緊的旗子。……艾米麗小姐只是瞪著他,頭向后仰了仰,以便雙眼好正視他的雙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開了。”如果不是對愛情的本真向往遭到破壞,她一定不會用死亡來使自己擁有愛情。
艾米麗對愛情的勇敢追求和自由選擇就是她最突出的女權意識的具體表現。如果說父親的在世對艾米麗來說是一種愛情觀的桎梏,那么當父親死后,鎮上的人民與宗教嚴規仍然是阻礙她獲得自由愛情權的利器,但艾米麗并沒有妥協,而是執著地追求自己的愛情——荷默·伯隆,這位男士雖是一位 “拿日工資的北方佬”,但艾米麗決然不顧周圍輿論的壓力和非議,執著而熱烈地敞開心扉去接受著自己的愛情:“以后每逢禮拜天下午他們乘著漂亮的輕便馬車馳過:愛米麗小姐昂著頭,荷默歪戴著帽子,嘴里叼著雪茄煙,戴著黃手套的手握著馬韁和馬鞭。”艾米麗完全沉浸在愛情的喜悅中,當然,她認為荷默也是熱烈地愛著她的,但最后才明白他只是個 “無意于成家之人”,他為了保全一個男人的完整性而拋棄了艾米麗,直到此刻當艾米麗連追求愛情的自由也被無情打擊后,她作出了一個瘋狂的反抗:買砒霜毒死荷默,把他的尸體藏于一間 “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里面陳列著 “玫瑰色窗簾,玫瑰色的燈罩,梳妝臺,一排精細的水晶制品和白銀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與荷默的尸體同床共枕40多年。可見艾米麗祭奠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愛情竟是這么讓人感到悚然與悲劇。這樣的反抗、這樣的追求,雖然太過于極端,但不可否認這是艾米麗性格中女權思想的一個因子。
對愛情的向往與追求是艾米麗最本真的人性呈現,而利用死亡去擁有自己愛情的永恒則是艾米麗最無可奈何的反抗。這個男權社會 “賦予”了她種種被遺棄的漠視,更將她一步步推向人性的懸崖,直至走到生命的盡頭。如果說 “一些人命運變化的決定性緣由,是我們始終未能看到‘自我’意義上的選擇和實現⑾,那么愛情與死亡終究是一種 “自我”意義上的選擇和實現,而非人性的毀滅。
結束語
福克納筆下的人物往往是一個復雜體,艾米麗就是這樣一個形象典型。她的一生充滿悲劇色彩,同時卻更加凸顯出女性這一群體對命運不懈的追求或反抗。男權社會剝奪了她追求愛情的自由權利,清教門規又摧毀了她追求正常生活的美好初衷。當一切的希望都已破滅,艾米麗走向悲劇的深淵是如此的堅定和必然。但在這些重重禁錮中,艾米麗試圖拼命反抗,用她的“病態”的、 “精神扭曲”的行為與社會輿論、宗教束縛來抗爭,這樣一個女性形象除去她的乖戾與癲狂,她的堅強、自由、獨立等人性光輝足可以為當代女性代言。
女性并非天生的弱勢群體,在男權社會與宗教意識盛行的任何國度或年代都會有一些女性閃爍出追求自由的人性光芒。女權主義要求 “男女平等”的初衷,在我們當今的社會雖不可說已達到完美,但至少它正在不斷地長足發展。一朵玫瑰無奈凋零,讓我們獻上一朵玫瑰祭奠她自由的人性光輝吧。
——細讀《孔雀東南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