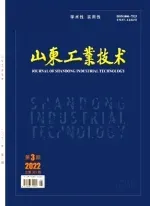淺析佛教中國化的“進化”——以宗教社會學的視角
閆 雪
(西北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1 宗教社會學的“進化”理論
宗教社會學進化論是宗教社會學中最早出現的一種理論,也是宗教社會學建立的基礎。在宗教社會學領域中最早使用“進化論”觀點的社會學家是孔德與斯賓塞。孔德的“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變遷要經歷三個階段或歷史時期:遠古時代的神學階段、中世紀以來形而上學階段和18、19世紀之交時開始逐步形成的科學階段。斯賓塞認為,祖先崇拜是宗教的原始形式,一切宗教都是以祖先崇拜為基礎的。
此外,美國當代宗教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重新描述了宗教進化發展的五個階段:一是,神圣世界與現實世界尚未區分的原始階段;二是,古代階段,出現了宗教專職人員;三是,歷史階段,出現了獨立性較強的宗教團體;四是,現代早起階段,神圣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體系崩潰;五是,現代階段,宗教變得高度私人化。
進化論在宗教社會學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它解釋了宗教起源、發展的過程,但進化論把事物的發生“畫成”了一條簡單的直線,其結構是從小到大、從無到有、從簡到繁,這種簡單直接的分析方法在用于揭示宗教這樣復雜的文化現象時,就顯得過于單一。
2 佛教的傳入
2.1 佛教的傳入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產生于公元前6世紀的古印度,公元前3世紀被定為印度國教,并開始向各國傳播。
佛教究竟何時傳入中國?這一點尚無定論,學術界中影響較大的有“西漢末說”、“西漢末東漢初說”和“東漢初說”。這三種說法由于因年代相近,又都有正史、野史材料證明,因此一時難分伯仲。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是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
2.2 中國佛教的宗派及基本教義
佛教傳入中國后,起初沒有大乘小乘之別,也無各種宗派的分立,隨著佛教在中國的不斷發展與融合,形成了大乘八宗:三論宗(法性宗),瑜伽宗(法相宗),天臺宗,賢首宗(華嚴宗),禪宗,凈土宗,律宗,密宗(真言宗)。 “唯識”近于科學;“三論”近于哲學;“華嚴”、“天臺”近于文學;“真言”及“凈土”近于美學;“禪宗”是中國佛法的重心。任何一宗均可匯入“禪”的精神;“律宗”遍屬各宗,是整個佛教的基礎。
早期的佛教教義主要包括說明人生本質及其形成原因的苦、集二諦,指明人生解脫的歸宿和解脫之路的滅、道二諦,共為四諦。四諦是佛教各大宗派公認的基礎教義。四諦的主要內容是:苦諦,將人的自然成長過程以及人的欲望皆視為苦;集諦,用“五陰聚合說”、“十二因緣說”、“業報輪回說”解釋苦產生的原因;滅諦,提出涅槃,就是熄滅一切欲望與煩惱,達到出世的最高理想;道諦,就是闡述通往涅槃之路。
3 佛教中國化的“進化”過程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對社會的思考和認知是以古印度文化特征為基礎的,而古中國的文化結構,尤其是秦漢以來,思想上中國人恪守皇權至上、天下一統的儒家思想觀、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觀、法理治國的法家思想觀等觀念的交融;經濟上則是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社會關系上是以家族血緣關系為主的倫理關系。所以,佛教必然要適應中國的文化,才能開始其在中國的傳播及進化的過程。
3.1 兩漢及三國時期
學術界一般認為兩漢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時期,這一時期佛教對中國的影響較小。但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政局風云變幻,人民飽受戰亂之苦,以出世為主的佛教在民間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當時的經文翻譯,大小乘兼備。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佛教的宣傳、研究,為兩晉時期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礎。
3.2 兩晉時期
兩晉時期的中國佛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發展,也更加體現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的合而為一。比如,此時佛經的翻譯,結合了中國的玄學、儒學思想;佛教音樂也加入中國音樂的元素;在佛教理論方面更是成績璀璨,東晉的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佛學思想,使得原本零散的佛教理論得以完整,他強調宗教對社會教化的作用,促進了佛教中國化的“進化”過程;鳩摩羅什的譯經幾乎囊括佛教全部關鍵名詞,其翻譯解釋深入淺出,堪稱佛經經典,他更是發展了中國化的佛教理論,中國的佛教也因鳩摩羅什而煥然一新。
3.3 南北朝時期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君主大都崇信佛教,隨之出現了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同時,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云、惠生等都曾去北印度巡禮,帶回大量的佛經。這個階段中國佛教開始摒棄苦修成佛的理論,而是通過個人內心的自我完善來頓悟成佛。佛經方面,強調涅槃與法性的統一,將佛教的業報輪回注入中國的宗法觀念中。
3.4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寺院眾多,僧尼眾多,信徒眾多,尤其是佛經翻譯數量之多,佛教各個宗派形成之眾,是以前任何時期都無法媲美的。據記載,此時我國共譯出佛經總數達435部2476卷,翻譯家共46人。所以,隋唐時期是我國佛經翻譯最輝煌的一個時期。我國佛教史上一些有影響的教派,也大多數在隋唐時期形成。比如隋朝時形成的天臺宗,和唐朝形成的唯識宗、華嚴宗、禪宗、密宗、凈土宗、律宗等。這些佛教宗派各有高僧,如天臺宗的智、唯識宗的玄奘、華嚴宗的法藏、禪宗的慧能、密宗的不空、凈土宗的道綽、律宗的道宣等,都是佛法高深的殿堂級大師。
可以說,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的成熟時期,這一時期佛教完成了中國化的“進化”過程,完全融入中國文化,并且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國化的成熟表現為佛經的重新翻譯,并影響延續至今的佛教宗派的建立和成熟。
4 佛教中國化“進化”的社會學審視
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進化論”的身影。初期佛教建構在印度文化之上,以古印度人的思維方式形成的佛教在進入中國后開始結合中國文化,并以古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對佛教重新進行認知,繼而產生了中國特色的佛教。
在這一“進化”的過程中,佛教在教義,教理,神話傳說,佛經故事等方面都做了中國化的調整和改變(如“拈花微笑”的故事,就體現了中國的禪宗精神),其中古印度文化逐漸褪色,中國文化則不斷閃爍加強。在這一漫長的融合過程中,佛教漸漸吸納儒家,道家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內容,將其納入自身的文化體系中,最終“進化”成中國佛教獨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并成為中國人恪守遵循的道德力量。這種道德力量成為民間崇拜的道德統治,這種權威統治繼而又彌漫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并滲透到各個社會群體中。可以說,佛教在中國的進化過程,也是中國人主要宗教思想的進化過程,兩者共同“進化”,共同發展,同時又互相作用。這是佛教中國化進化過程中的社會學意義。
[1]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M].康樂,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2]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時期的傳播與適應[M].李四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3]高師寧.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J].上海大學學報,2007(3).
[4]朱文斌.杜爾凱姆與與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比較——原始宗教本質探源與資本主義精神尋根[J].社會科學論壇(下),2007(7).
[5]李向平.中國當代宗教的社會學詮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