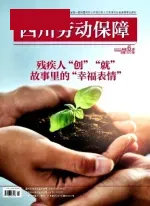薪酬情緒:一個值得關注的主題
■李艷 杜敬軍
薪酬可以看作是普遍價值判斷下個性化交易的結果。普遍價值判斷是指對為“什么”付酬以及薪酬差異程度的共同理解。伴隨每個交易之后,交易者往往都會形成一個滿意度的評價,可以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潛在的。薪酬一般是長期、穩定交易的形式,滿意度的評價是持續進行的,這種評價既是個性化的表達,也包含了社會化的觀點。特別是在一個愈加開放的社會中,當交易的信息匯總在一起進行比較,更多的人一起交流各自的交易感受時,個人的評價標準和評價結果被社會化了,基于薪酬本身的個體情緒擴散演化為社會情緒,而某種導向的薪酬情緒氛圍又反過來進一步影響個體的薪酬情緒的形成。
薪酬情緒的內涵
薪酬是市場經濟下的產物,但薪酬情緒則是社會規則的評價。人們對于交易過程和回報結果的評價感知形成了薪酬情緒,該情緒不僅涉及到薪酬公平的評價,還涵蓋了薪酬水平所決定的社會身份和階層定位與心理預期之間的比較。由此來看,薪酬情緒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其產生首先是建立在相關信息的基礎上,了解或者自以為了解別人的能力、努力、薪酬水平等等;其次是事關薪酬標準即薪酬制定的依據,明確薪酬交換的內容;三是比較對象的選擇,通過與其比較后得出主觀的結論。
當前收入分配中諸如體制、身份以及規范等問題陸續浮出水面,薪酬情緒問題已表現的特別明顯,在一個物質欲望無限放大、價值規范嚴重失衡的背景下,社會薪酬情緒氛圍逐漸變得偏激,個體對于薪酬的認知處于扭曲狀態。
薪酬情緒的表現
前些年的網絡“曬工資”暴露出行業收入的詳細信息,尤其是當人們發現收入的巨大差距并非是基于學歷、績效、崗位等“正義”的前提時,大家理所應當地認為自己可以而且應該以憤怒的姿態來表達情緒了,薪酬收入不合理并要求進行改革的聲音不斷得以強化。
薪酬情緒的高峰點出現在2011年的春節前后,一方面是國內一些研究機構發布了行業年終獎的數據,金融業以人均不低于5萬元位列第一序列,在敏感時點為此類情緒推波助瀾;另一方面,媒體曝出“銀行利潤高的都不好意思說了”的論調,導致社會中出現了一種全民的薪酬憤怒情緒。網絡社會傳播中的另一焦點是炫富,公眾由種種臆測形成的薪酬情緒經由網絡瘋狂的傳播,進一步積累和異化。
某保險公司董事長千萬年薪事件激活了社會對于高管薪酬的關注,大部分人認為高管拿高薪是不合理的,而國企高管公布幾十萬的年薪更是遭到批判,既質疑數據的真實可信,也指責在職灰色消費和隱形福利部分是個黑洞,強化了社會薪酬情緒。公務員的薪酬也不斷陷入輿論的漩渦中,少數官員的負面形象嚴重激化了薪酬情緒中不平聲音。隨著我國養老問題的凸顯,事關公務員與其他身份人員的養老金繳費與權益問題同樣引發了社會爭議。
薪酬情緒的成因及擴散
不平等現象是薪酬情緒發酵的主要因素。假如民眾的收入差距不大,人人都可以去差別不大的學校讀書或醫院看病,這就會讓大家感覺到民眾之間基本上是平等的。這些共有的體驗,既讓人們感覺到自己能夠分享到社會的權益,又使人們認識到自己為社會所應該分擔的義務。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人們之間的相互協作和共同工作就變得更加容易。如果是在極其不平等的社會狀況下,那些相對弱勢的群體就會深感社會的不公,也無意參與到社會公共活動或者自發的公民行為中來。同樣的,對于那些為社會付出很多卻得不到應有回報的人來說,也會深感社會的不公。
消費主義的興起導致人們對于金錢的過度渴求。為了維持期望的消費水平,人們不得不在工作上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使得我們遵從了“賺錢-花錢”的生活方式。消費文化帶來了社會關系的緊張狀態,消費不再只是物品的物質消費,而是一種象征性的符號,使社會地位及個人身份與消費品聯姻,由此導致消費的地位競爭,進一步助長人們相互炫耀、相互嫉妒、相互攀比與相互模仿的社會風氣。這種消費文化由于展示了社會的不平等而可能引起社會的不安。當人們的期望遠遠高于他們的實際所得時,便會造成人們對社會的不滿,甚至導致一些人采取過激的手段來獲取想要的物品。人們總要斤斤計較自己行動的成本與利潤之間的關系,人際關系也就變成了待價而沽的交易關系。
公共服務缺失以及由此導致的公共精神的淪喪是薪酬情緒擴散的根本原因。在傳統的長期雇傭體制下,員工得到較好的培訓和福利待遇,但新型的靈活性的就業給員工造成了社會壓力和不安全感。職業上越來越多的不穩定因素以及績效薪酬上的個性化發展趨勢,讓個人所面臨的社會風險高度積累,急需公共服務的支持。而我國涉及人民群眾基本生活的教育、住房和醫療等領域的市場化發展加重了社會公眾的不安和焦慮,甚而形成了一種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社會心態。社會的公共精神隨之喪失,公民對社會基本價值觀念的認同感和對公共規范的維護意識逐漸下降。缺少了這種公民美德和社會資本,社會不良風氣和氛圍的傳播具備了良好的條件,人們的情緒化選擇性信仰既是對不安心態的一種過度發泄,也同樣推動了社會不良心態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