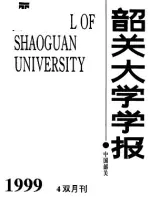嚴繩孫傷今懷古詞探析
章 黎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嚴繩孫傷今懷古詞探析
章 黎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嚴繩孫是清初詩人、詞人、文學家、畫家,與朱彝尊、姜宸英并稱為“江南三布衣”,與秦松齡、顧岱等都為梁溪詞人,是梁溪詞人群的代表人物。嚴繩孫由明入清后應詔出仕,漂泊中寫下許多感嘆人生、懷念故國的詞篇。詞篇中既有詞人對過去的追念,也飽含著作者嘗盡人生甜苦后的感懷,其詞作大體可分為感嘆人生、追思過去、懷念故國三類。
嚴繩孫;感嘆人生;追思過去;懷念故國
嚴繩孫,字蓀友,一字冬蓀,號藕漁,自稱勾吳嚴四,生于明天啟三年,無錫縣膠山(今屬東北塘鄉)嚴埭人,以詩詞書畫聞名。作為一個由明入清后又仕清的名士,其不拘的性格、清新的詩詞無不是特定時期某類人群的個性體現。
出門在外的文人墨客,常常會因為某處景物、某個場景引發內心的共鳴而寫下華章,或是為想念家鄉,或是悲今嘆昔,或是為自己的人生發出慨嘆。唐代張繼便是聽到寒山寺的鐘聲而引起內心的迸發,寫下《楓橋夜泊》詩,寒山寺也由此聞名;杜甫《登高》中的詩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既是寫景也契合了當時的心情,傳達了韶光易逝、壯志難酬的感慨。嚴繩孫詞中也多有此種抒發,沿途記下景與情的互訴。
一、感嘆人生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人生本就一場夢,韶華易逝,歲月匆匆,盡情縱樂之時能有幾何。“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王國維《蝶戀花》),留不住的又豈止容顏。“細雨濕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馮延巳《南鄉子》),細雨打濕了芳草,映出點點光芒,別樣的春光引人無限遐想,而各種感情隨著時間沉淀,也愈來愈深。
嚴繩孫《浣溪沙》詞曰:
膩粉無端退蝶翎。赤僧偷眼是蜻蜓。春光先過短長亭。
安得手持修月斧,愿將身作護花鈴。不堪風雨腳丹青。
首句就點出這是一篇惜春之詞,化用溫庭筠“蝶翎朝粉盡”(《春日野行》)句,寫蝴蝶漸漸褪去蝶粉。上片寫蝴蝶、蜻蜓,都是春的告知者,與短長亭形成一幅遠近交匯圖。下片抒懷,甘心做春的保衛者,手持修月斧守衛美景,化身為懸玲保護百花。然而,即便是丹青也難免褪色,何況是易逝的春光,又如何禁受得住風雨的摧殘?作者由春色感嘆人生,世間萬物終難逃繁華與落寞的輪回,凡是美的事物終將凋零,花開必有花落時;而人生亦如是,成功伴隨著失敗,得意伴隨著失意,命運往往如此。
唐以來很多詞人借用《浣溪沙》的曲調來感嘆春色易換、時間難留,最著名的當如晏殊的“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花落、燕歸,又一番輪回,似曾相識的場景,難以掌控的變化。李清照也有一首:“小院閑窗春已深,重簾未卷影沉沉,倚樓無語理瑤琴。遠岫出山催薄暮,細風吹雨弄輕陰,梨花欲謝恐難禁。”仍是惜春詞,末句顯出對春的眷戀以及難留的無奈,比之晏殊詞則感情上更深至。蘇軾作為豪放派的代表,其所作《浣溪沙》亦有不一樣的豪情:“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門前流水尚能往西奔流,人又怎能輕易悲嘆白發暮年呢!
嚴繩孫此類感嘆人生的詞還有很多,如 《念奴嬌》中:
浮生夢里,更能得、幾度人間今夕。西子湖頭秋已半,清景似曾相識。銀渚云開,珠胎月滿,一片傷心碧。姮娥知否,照人如此清切。
試望蘇小西陵,如今松柏盡,難尋油壁。星火樓臺永夜舟,不是舊游蹤跡。病憶愁吟,有荷花笑,我百端交集。數聲何處,夜分猶自吹笛。
“悲秋”是中國古典詩詞的一大傷感主題,具有哀傷的美感特征,這首詞也不例外。秋已過半,詞人夜游西子湖畔,舉頭望銀漢迢迢、月明星稀,此情此景似曾相識。聯想月宮清冷寂寞,人間亦如是,人生如夢,短短幾個秋,如今“松柏盡,難尋油壁”、“不是舊游蹤跡”,之前的景象無法復制。秋本身沒有傷意,然而草木凋零、萬物蕭條的秋景,總惹人與世事相聯,那經由春夏的生機轉入衰敗的恍然,與人從生到死的過程迸發出了悲劇般的崇高之美,使得詞人百感交集。
這一惜春一悲秋,都是對人生匆匆難復返的惋惜,還有《滿江紅》中:“生老樊川,水嬉不盡當年興。問十里湖光何處,畫橈相并。金管風多聽又失,珠簾雨細看難定。算陳思、著眼不曾多,驚鴻影。憑舷意,應誰省。拋醉纈,朱榴④。盡繁華都付,藕絲風領。一簇愁紅空極浦,半湖柔綠浮歸艇。正高樓、人在柳陰中,煙光暝。”這首詞中有兩類關鍵詞,第一種與時間有關:“生老”、“當年”、“陳思”、“不曾”、“驚鴻”、“盡”、“付”; 第二類與水有關:“樊川”、“水嬉”、“湖光”、“橈”、“雨”、“舷”、“藕”、“浦”、“湖”、“艇”。顯然,作者意取時間與水之流逝,表達“逝者如斯”之情,在時光流影中反觀人生。《水龍吟·端州五日》:“淹冉年華,禁他揉弄,這般狼籍……清尊空滿,朱顏難駐,浮名何益。”年華褪卻后,所謂功臣浮名又有多少價值呢?這該是作者年老時對過去人生的回顧與感慨。
歸燕、流水、花落花開、春去秋來這些景象都容易引起文人的情思,一般人可能無意身邊之景,文人卻會因此動心觸筆寫情,所謂“花開有落時,人生容易老”(陶淵明《為學》),時間飛躍,昨日對酒當歌,明日還剩幾何,若人生真只如初見,倒也省去不少煩惱。
二、追思懷古
借古喻今,與古人對話,這在詞中并不鮮見,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古、今有太多可比的東西,通過古今對照,能夠領悟很多東西。這類詩詞一般以歷史人物、陳跡為題材,借嘆史實、詠故人來感慨當今盛衰,托古諷今,寄托哀思。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在登臨建康賞心亭時便寫下傳誦千古的 《水龍吟》,劉過為悼念岳飛唱出一曲《六州歌頭》,都是借古嘆今,表達對南宋政權的不滿。
嚴繩孫的《桂枝香·胥江懷古》:
吳城東畔。早一抹秋容,驟雨初歇。試問忠魂何處,依稀未遠。六千君子凌波起,便江頭、水犀朝偃。傷心此際,驚濤濺血,臣言真踐。
歡千古、興亡滿眼。更白馬從游,此恨誰見。贏得神鴉社鼓,麗譙荒甸。西風誰把英雄淚,灑東流、一時吹轉。始應消得,簫聲吳市,那些幽怨。胥江乃春秋時吳國名將伍子胥率眾開挖而成,因以為名。想當年,勾踐部下六千貴族,浩浩湯湯,氣蓋當時;伍子胥文韜武略,功績垂青,最終卻受誣致死。《史記》載曰:“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吳城霸業,最終應了伍子胥臨終之言,氣數盡銷,不久而亡。詞人漫步吳城東畔,不禁產生諸多遐想,“歡千古,興亡滿眼”便是回顧歷史興亡后的感嘆。“西風誰把英雄淚,灑東流、一時吹轉”,“忠魂”、“英雄”往往比常人肩負更多辛酸與責任,然所有的功過得失、恩怨對錯,終究付諸歷史長河而東流不復,只是留給后來人嗟傷。
嚴詞中感嘆歷史交替的還有《臨江仙》:
試問吳公人去后,綺羅多少星霜。一聲漁笛散橫塘。虎邱今夜月,猶為照真娘。
記得霓裳花底見,春風幾度思量。生公石上舊年芳。夜寒蓮漏永,清影在回廊。
作者本是無錫人,因此對江南的描寫頗多,吳地虎邱也是作者常常吊唁之地,如《青玉案》中“虎邱山下傷心路。直不放、游人去”也是。《臨江仙》寫作者到吳地虎邱,想到吳王早已不在,不知又輾轉了多少年頭。真娘墓頭,衰草蔓延,倩影而今已不知何處。作者運用了諸多表示時間之詞,如 “去后”、“星霜”、“今夜”、“幾度”、“舊年”等,感嘆時間的流轉,末尾寫“蓮漏”計時,更表達出時光一去不復返之意,流露對時間的無法挽留之嘆。“吳公”、“真娘”、“生公”所在的虎邱,本是極輝煌之地,現已然冷落千秋、繁華不再。作者通過這一系列的對比,完成了今昔兩個時間維度上的連接。
通過時間比照完成古今對話,是中國古典詩詞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它不單是文學層面的情感寄托,更是哲學層面上對人生意義的反思,最著名的當如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是詩人在報國受挫后登上幽州臺的慷慨悲歌,表達了懷才不遇、寂寞無聊的情緒,感嘆宇宙的無垠和人生的短暫,引起后世許多共鳴,堪稱一部吊古傷今的生命之作。
三、悼念故國
嚴繩孫作為遺民,由明入清后又仕清的經歷給了他太多的壓力和無奈。面對清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思想、言語的強力鎮壓,很多文人均由反抗走向妥協,對故國的思念也只能埋藏心底,時而借筆端婉轉訴出,較少有“夢里相思,故國王孫路”(陳子龍《點絳唇·春日風雨有感》)的直呼。
嚴繩孫詞中有很多描寫了對故國的懷念,但較為隱晦,如《醉公子》:
郊外青驄馬。躞蹀垂楊下。悵望碧云重。夕陽蓮葉東。
最是銷魂處。禾黍離披去。遠客易驚秋。風多莫上樓。
全詞淡筆著調,上片寫詞人騎馬跑至郊外,徘徊在垂落的楊柳枝里,看著遠方的天空,莫名惆悵,不覺夕陽已悄然落下,是場景呈現。下片描繪心情,眼見原本繁華之地,現被禾黍覆蓋,茫茫然而歡騰不再,舊事如夢,不堪回首。詞人冷秋時候遠行到此地,今昔對比,越發覺得秋之悲涼。甚至不敢攀上高樓,站得越高,望得越遠,心底的悲情就會越發濃烈,恐承不住這風的吹徹,更覺寒冷。“禾黍”取自《詩經》,《黍離》篇《序》中說西周之后,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彷徨不忍去,乃作此詩。“遠客”則是化用李煜的“夢里不知身是客”(《浪淘沙》),均是感慨亡國之詞,平淡筆調的背后隱藏的是深深的哀悼。
又如《南鄉子》:
日永枕空支。漫折榴花綴五絲。渡口寂寥歌鼓斷,尋思。病也何曾似舊時。
懶自醉芳卮。剪取清光寫楚詞。此會明年何處所,差池。似客心情燕子知。
上片看似寫一個夏日午后,詞人一副閑散模樣,只在結尾點出對舊時的回首。下片借醉酒口吻道出懷念故國之意,“剪取清光寫楚詞”借用屈原懷念故國的方式,表明雖是清朝天下,但也妨礙不了對舊朝的念想,“似客心情燕子知”更是道出身不由己的無奈。
德國漢學家顧彬在《中國文人的自然觀》里總結了唐代懷古詩固定標記的六點:1.登高;2.望遠并追想過去;3.江山依舊而人生易老;4.歷史人物及過去時代的遺跡;5.眼前的真實自然;6.涕淚。嚴詞中的感傷念古大多也是緣于這些因素,周邊環境因時間轉換,徒留下物是人非的滄桑。
Analysis of the Yan Shengsun’s Compassion and Reminiscence over the Past and Today
ZHANG 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Jiangsu,China)
Yan Shengsun was a Qing Dynasty poet,writer and painter,and Zhu Yizun,Jiang Chenying and known as‘Jiangnan Three Citizens’,and Qin Songling,Gu Dai were famous poets,wer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Liangxi.By the Ming Qing Dynasty strictly Shengsun after drifting call of the government,drew many paintings of real life,nostalgia for the old poems.Words of both poets of past memories,but also full author tasted the bitter sweet life after about,need careful interpretation.
Yan Shengsun;feelings of life;reminisce;nostalgia for the old
I207.23
1007-5348(2013)01-0034-03
2012-11-30
章黎(1988-),女,江蘇南京人,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生,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責任編輯:吳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