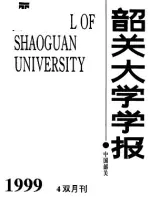環境侵權損害社會化救濟方式的比較分析
(浙江農林大學 環境法治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浙江 臨安311300)
一、環境侵權損害社會化救濟的實現方式
侵權責任法在賠償問題上的局限是制度性的,其根本在于侵權責任本身是一種追究個人責任的機制,使受害人的補償要受制于加害人的賠償能力。為了向事故受害人提供救濟,各國都在逐步建立一個由侵權責任法與社會保障法、保險法以及公益救助基金等共同發揮作用的損害救濟制度。
環境侵權作為極特殊的一類侵權,由于其不確定性、潛伏性、復雜性、廣泛性和科技性等特點,傳統的損害救濟方式在現實中遭遇各種障礙。通常認為,環境侵權民事責任除了個別化的損害賠償制度,還應輔之以提存金、企業互助基金、環境責任保險、政府救濟基金等多種制度相互配合與協調,有效地實現環境侵權責任的社會化。
(一)環境責任保險
責任保險是被保險人根據保險合同約定向保險公司交納保險費,當被保險人依法對第三人負有賠償責任時,由保險公司對第三人支付保險金之保險。其一方面可以免去被保險人支付巨額賠償金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無辜的受害者及時獲得損害賠償。而保險人則通過收取和經營保險費而獲得利益。責任保險制度將不同類型的無形風險外化為市場價格——即保險費,并通過保險費的集中,實現其風險在社會范圍內的轉移[1]。
環境責任保險既是一種風險分散和防范機制,亦是侵權責任法對現代社會侵權行為多樣化、侵權損害救濟途徑和責任形式多樣化、社會化的積極回應。因環境侵權而導致賠償責任時,被保險人可通過保險的渠道將巨額的賠償金外化為一定的保險價格,在具有同類危險的共同體,即眾多的投保人中得以分散,從而實現損害救濟的社會化。
(二)環境損害救濟基金
環境損害救濟基金是通過行政權力介入或社會組織自發形成基金,在特定情形下為了對受害人予以有效救濟而設立的一種社會化制度。根據基金的資金來源及基金運作特點,可將基金分為民間性質的環境損害救濟基金(又稱企業互助基金)和行政介入性質的環境損害救濟基金 (也稱其為環境政府救助基金)。
1.企業互助基金
企業互助基金,是由危險相近的企業或同行業的潛在污染者通過繳納基金份額的形式形成風險基金,當企業造成污染損害時,由該基金對受害人進行賠付的制度。在該制度中,環境損害的風險實際上是由繳納基金份額的責任共同體來承擔的,即將個體的風險分散于同一行業所有潛在的污染者中。企業互助基金又分為通過法律規定授權成立的賠償基金和完全由潛在污染企業自發建立的賠償基金。
前者最典型的是美國的舒坡兒基金。舒坡兒基金的資金來自于風險性比較大的同行業的潛在污染企業。盡管是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規定,但它的運作主要是靠民間團體。這種方式的優點是使基金賠償有法可依,賠償范圍、賠償數額明確。但是該基金是假設同類企業實施同一水平的環境保護措施,然后對其所要承擔的責任風險進行分化。但是如果有些企業在進行生產的同時能夠自覺投入較多人力、資金進行環境管理,那么強制其交納資金來充實環境損害賠償基金,則顯得未必合理[2]。
后者是企業從稅后利潤的法定公積金中提取,形成各個企業合力組成的基金庫。一旦某企業發生污染賠償問題,賠償金就從基金庫中出。這種方式是完全的民間方式,不具有任何的官方或強制性質,同時也減輕了政府的負擔。而且該基金的建立完全出于自愿,往往能達到很好的預防污染的效果。但是,環境侵權案件的涉及范圍十分廣泛,企業自發設立的賠償基金難以覆蓋該行業內所有的潛在污染企業,無法做到肇事企業間的侵權責任公平分擔。而且環境侵權伴隨著巨額的索賠,該基金的規模小、數量少,就不足以全額、及時賠償受害人的損失[3]。
2.政府救助基金
政府救助基金是政府制定專門的法令和規則,以征收環境費稅(包括排污費、碳稅)等作為籌資方式而設立的對環境受害人予以補償的基金。也有學者稱之為行政補償。行政補償強調原因行為的合法性,是行政主體合法行使公權力的行為造成相對人損害,由國家財政對受害人的補償。政府救助基金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體現了現代“福利國家”國家權力介入社會生活的特征。在無法確定加害人和加害人沒有賠償能力的情況下,國家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救濟受害人的職責。而企業常常缺乏經濟動力主動成立賠償基金,需要國家公權介入才能征收、管理和運用救助基金,如我國的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就是法律強制規定成立的。從這一點上來講,該制度具有一定的福利行政和社會保障的性質,使“轉移”損失的傳統損害賠償責任在相當程度上轉化為“分擔”損失的損害補償責任。另一方面,政府救助基金制度又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安全體制。從根本上說,該制度仍以“污染者付費原則”和民事賠償責任作為征收、設立和支出救助基金的基礎,仍屬于民事損害賠償理論和制度的調整、修正和補充,是民事損害賠償的一個特殊環節。因此,該制度保留規定了對侵權損害責任人的追償權,反映了現代社會“私法公法化”的趨勢。
(三)提存金
環境侵權損害賠償一般都是事后補償性的救濟,常常因為企業沒有足夠的資產來賠償,致使受害人陷入困境之中。所以,在損害發生前儲存一定的賠償資金是非常必要的。
葉曉華學者認為“寄存擔保基金”是在危險企業開工之前,由企業預先寄存一定的擔保金,以備損害賠償之用[4]。而王明遠教授則稱為“提存金”,并將其定義為:污染性危險企業在開工之前,依照有關法令向提存機關預先繳存一定的保證金、擔保金,或者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依照有關法令按期繳存一定金額,以備損害賠償之用[5]。竺效博士認為,提存金制度并非社會化的環境損害賠償方式,但是可以設計一種類似的事先專項存款制度,即要求從事生態環境危害行為的行為人事先向指定銀行開設的生態損害填補專用賬戶存款,以擔保存款人有一定的賠償能力……一旦存款人構成生態損害填補法律責任,銀行就可以根據有關司法文書直接將該存款人賬戶內的款項劃轉給有關實施生態損害防范、清除、修復措施的主體[6]292。
寄存擔保基金、事先專項存款和提存金在本質上都是提高環境危險企業賠償能力的事先的財務擔保制度。為了與普遍采用的概念相一致,這里依然稱為提存金制度。
二、環境侵權損害社會化救濟方式的比較
不論哪種社會救濟途徑,其實質都在于將環境風險分散化,便于受害者權益的及時救濟。但同時,又各具特色、各有優勢。
第一,從強制性上看。提存金是污染性危險企業依據法律法規按期繳納的保證金、擔保金,對拒不履行者,有關機構將對其科以一定的行政處罰,從而形成強制履行提存義務的機制。企業互助基金屬于企業間的互助合作組織,具有自愿性和互助性;但沒有國家公權力的參與,就容易導致因基金有限而不能充分救濟受害人的情況。政府救助基金制度由于公共權力的適當介入則恰恰彌補了這種不足。而根據環境責任保險關系的建立是否取決于投保人的意志,又可分為強制責任保險和自愿責任保險。
第二,從資金來源看。提存金制度只是將責任主體需要一次性支付的巨額損害賠償金在時間上予以分散,因而其僅對受害人有利而不能減輕加害人的經濟負擔。互助基金制度是由企業聯合體在一個封閉的范圍內對損害進行分擔,資金來源于各個具有同樣危險的企業按照預先約定比例繳納而形成的基金,資金來源較單一。環境責任保險中,保險公司向受害人支付的保險賠償金來自于眾多可能產生污染損害的投保人繳納的保險費,資金來源相對較單一。政府救助基金的資金是多方籌集的,來源渠道廣泛。依次是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資、由環境法規定之特別稅費(如碳稅、垃圾稅、排污費等)、向污染源關系人追索所得款項、基金孳息收入和社會捐助等。
第三,從社會化程度看。提存金制度僅是一種提高加害人賠付能力的事先預防制度,屬于事先的自我擔保。其責任最終仍由加害人自己承擔,并未進行任何社會化的分擔,不能作為“環境侵權損害的社會化賠償”的一種方案。企業互助基金是由具有同樣污染危險的企業共同出資設立的,在行業共同體之間實現了環境污染損害賠償風險的分散。環境責任保險中是由保險公司對受害人給予賠償,而保險公司再將損失轉嫁給成千上萬的投保人,從而實現損害的社會承擔。政府救助基金則屬于以社會性集團責任為基礎的損害補償制度,責任的社會化是通過補償資金籌集的多樣化來實現的。因此,提存金是社會化程度最低的一種救濟方式,其次是企業互助基金,再次是環境責任保險,社會化程度最高的是政府救助基金。
第四,從適用條件看。提存金和互助基金適用于民事責任歸屬和加害人明確、但支付能力恐有不足的情況。在通過基金獲得賠償后,加害人最終要按照約定的比例將互助基金墊付的賠償金予以一定的補充,因此加害人自己也承擔一定的責任。環境責任保險要求加害人明確,而且主要適用于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在實際發生環境損害時,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實際上每個投保人只是承擔了一小部分的賠償責任,即向保險公司支付的保險費用。政府救助基金不局限于對突發性環境損害的救濟,且針對的是加害人償付能力不足、根本不具備償付能力、有免責事由、污染源不明且無法確認加害人等情況,從而彌補了民事責任解決特殊環境侵害問題的局限。基金在補償后,如果加害人確定,再向加害人追償。
三、我國環境侵權損害社會化救濟方式的選擇
對于一個現代社會的損害填補制度的選擇,不僅應研究各種填補制度本身,還應該參照社會、經濟之發展。在我國,對于環境責任保險、環境救助基金的立法,目前局限于《海洋環境保護法》所規定的船舶油污責任保險與船舶油污基金、《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所規定的海洋石油勘探環境責任保險和《道路運輸條例》所規定的危險物品運輸責任保險四類。對于其他形式的經濟保障措施,如救濟準備金、公積金、擔保物權等,尚沒有充分的法律根據。
提存金和企業互助基金的適用需要滿足 “有明確的環境侵權加害人、環境侵權賠償責任成立”兩個條件。其中的提存金制度只是延緩了承擔責任的時間,沒有將損害賠償轉嫁給社會,加害人的賠償負擔并沒有減輕,仍然是在個別地解決問題。責任保險制度可以將環境風險轉移給眾多的投保人分擔,以達損害賠償的社會化。我國應建立環境損害賠償的責任保險機制,對從事高度危險、易于發生環境污染的行業或廢棄物處置的企業強制其繳納保險費投保。對于非高度危險性的行業和一般性事故所引起的環境損害采取自愿投保的原則,而政府予以積極引導與鼓勵。
除責任保險外,環境損害賠償基金制度可以作為社會化填補的另一種方式。我國可以采取“行業性企業互助基金”與“綜合性政府救助基金”相結合的較完整的基金制度。
就環境損害危險性行業而言,可以建立行業性企業互助基金。在必要時,企業互助基金可以對環境責任保險無法完全救濟的部分損害予以一定補充救濟。企業互助基金制度實質上是集中某個行業或集團的整體實力提高這個行業或集團內成員負擔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能力[6]286。該制度的社會化程度遠不如責任保險,且必須以侵權責任的成立為前提,故不利于對受害人權益的保護和損失填補,而只適宜作為侵權損害賠償制度下一位階的損失承擔方式,供企業自愿采用[7]。
責任保險和企業互助基金制度都是在加害人確定的情形下適用的,由于科學技術手段的有限性和環境污染損害原因的復雜性,有時難以找到造成污染的根本原因和直接的加害人。因此,無論是環境危險性行業還是非危險性行業,都應建立全國性的綜合性的政府救助基金。在必要時,其可以對環境責任保險和企業互助基金無法完全救濟的部分損害予以一定的補充;企業互助基金如果停辦,可以通過簽訂協議,將其并入綜合性環境損害政府救助基金的范圍,并繼受權利義務。此外,當加害人難以確定或加害人未投保或保險合同因故失效以及加害人因賠償數額巨大而破產或者因違法行為被撤銷主體資格,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應通過政府救助基金制度給受害人以有效的救濟。因此,企業互助基金和政府救助基金有機地構成了完整的環境損害社會化救濟的基金制度。
綜上,我國應將責任保險前置于企業互助基金和政府救助基金,構建一個完整的環境損害社會化救濟制度,建立多重主體救濟機制,藉以保護受害人權益,減輕加害人之負擔,達成“雙贏”[8]。
[1]游春,何方,堯金仁.綠色保險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9:88.
[2]論環境損害賠償中的基金制度[EB/OL].[2012-06-15].http://whhsq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03.
[3]胡震宇.大規模侵權損害賠償基金制度設計的思考[J].理論界,2011(8):69-70.
[4]葉曉華.環境侵害賠償制度基本問題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1998.
[5]王明遠.環境侵權救濟法律制度[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145.
[6]竺效.生態損害的社會化填補法理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292.
[7]周珂,楊子蛟.論環境侵權損害填補綜合協調機制[J].法學評論,2003(6):113-123.
[8]王堃.試論我國環境侵權損害的社會化賠償機制[J].現代商貿工業,2007(1):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