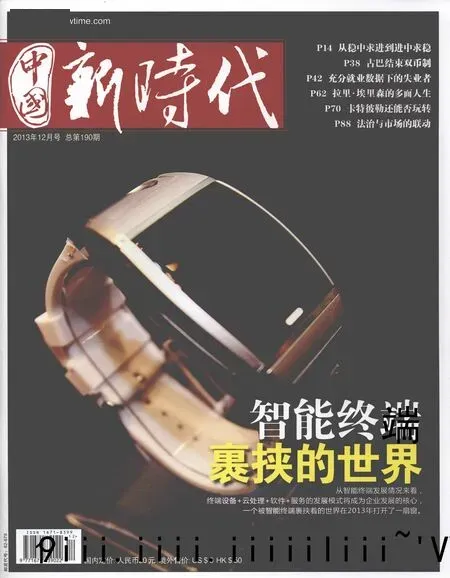魏瑪蝸牛殼里的世界
|| 文 圖· 鄭實
魏瑪成為德國古典主義的搖籃,甚至被稱為歐洲的文化中心,純屬偶然。它并沒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圖林根和附近地區,并不缺乏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重鎮:埃爾福特、耶拿、哥廷根、萊比錫、哈雷、哥達等。但為什么魏瑪在這一片群星中成為最耀眼的一顆?
一個小公國的繼承人邀請一位作家到他的小王國做客,兩人相見恨晚、相談甚歡。短暫的停留變成永久地居住,歌德于1775年定居于魏瑪,讓德國人無比自豪的“黃金時代”由此徐徐拉開帷幕。今天到魏瑪一游的人都是被這一佳話吸引而來。即便沒有認真讀過歌德的小說和詩歌、席勒的戲劇,對魏瑪共和國、包豪斯只是影影綽綽地聽說過,到達這個小小的城也會被融化到一種氣氛中,典雅、寧靜、散發著書香和莊重與理性的氣息。從城中的車站出來,走在碎石小路上,不知不覺,人們就會放輕聲音、放慢腳步、放下庸人自擾的煩惱,成為一個步入古典時空的探索者、尋覓者、崇敬者。
如果你也像歌德當年一樣,只打算短暫拜訪,走到市中心,突然地,腳步又會急切起來。因為每一幢靜默的建筑里,每一扇木門后面都深不可測地藏著好多寶藏,你會發現這里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要多,路邊一個不起眼的小胸像或墻上一塊落了塵土的小牌子都代表了一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和他們在此留下的歲月痕跡。你原來以為德國的人和事離我們很遠,但忽然發現他們的一個想法改變過世界,甚至余波也傳到遙遠的中國:包豪斯的設計讓我們如此眼熟,是因為早已進入尋常百姓家。
故事應當從一個女人說起。安娜·阿米莉亞公主16歲時從普魯士嫁到魏瑪。很不幸,兩年后,丈夫便去世了,留下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卡爾·奧古斯特。于是安娜代表兒子執掌公國,直到她確認16歲的兒子已經可以獨自處理政務,便“退居二線”,致力于推進文化和藝術的發展。魏瑪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才識和遠見。
不管你打算在魏瑪呆多長時間,我的建議是進城一定要先奔安娜·阿米莉亞公爵夫人圖書館的古典分部。因為它坐落于一幢古典建筑,空間有限,2004年的大火之后,著名的洛可可大廳每天最多只能容許290人參觀。因為當天的票常常早就被售光了,因此必須提前買票。當然也可以在網上預約。
如果沒有洛可可大廳,這座圖書館不會吸引這么多參觀者。它太炫目了,看過圖片,就一定想來。僅從視覺角度來說,洛可可大廳是魏瑪除藝術品之外最搶眼的一頓盛宴。其他的景點都或多或少依仗其包含的歷史文化內涵,而這個大廳本身,即便是沒有實用價值,也特別值得親眼一睹芳容,何況還有4萬冊圖書環繞四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爵夫人捐獻的私人藏書。正因為如此,在1991年圖書館建館300周年的活動中,這座圖書館被命名為安娜·阿米莉亞公爵夫人圖書館。
卡爾·奧古斯特公爵長大成人后,沒有辜負母親的信任,依然不遺余力地建設他們的這個小都城。他把歌德吸引到魏瑪,不僅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也給予歌德高度的信任,不顧幕僚的反對,委任歌德參與魏瑪市政和文化設施的建設。
公爵為歌德在城中心購買了一處住房。除了短期旅行,歌德一直住在里面,直到去世。這就是現在的歌德故居。這座典雅的小樓,每個房間都裝飾著雕像和繪畫,體現了主人對意大利古典藝術和文藝復興的向往。
歌德和席勒,是德國版子期伯牙的故事,只是沒有那么悲慘。他們的相遇開啟了古典黃金時代,不僅是魏瑪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是德國文化復興的重要標志。當然兩人并非“一見鐘情”,而是“好事多磨”。在歌德的舉薦下,席勒在魏瑪雖獲得了一個職位,但薪水比較微薄。他初來魏瑪時,很驚訝,覺得魏瑪是個蝸牛殼里的世界,不僅和外界的交通極不方便,而且城市自身的布局也很局促,文化氣氛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濃厚。幸而德國好多大城市的劇院都愿意上演席勒的劇作,他可以用稿費支付大部分購房款。可惜席勒和家人只在這里享受了不到3年平靜的時光就去世了。1847年,魏瑪政府購買了這個房子,在席勒的書房開辦了德國第一個文學博物館。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的反差會讓人對命運有更深切的認識。從建筑的外表看來,兩個故居的區別只是空間大小不同。但進入室內,就會感受到強烈的反差。歌德的房子很氣派,每個房間都像貴族的宮殿一樣裝飾精美,總是處于等待人欣賞的狀態。而席勒房子裝飾很簡單,家具更實用,更像是一個家。這當然是因為席勒的收入情況遠不及歌德,更重要的是席勒是個居家男人,他對夏洛特很忠誠,兩人生有4個孩子,因此家中必然是以養孩子、過日子為重心。
在魏瑪的人物長廊中,還有一長串令人驚喜的名字:克拉納赫、巴赫、叔本華、李斯特、尼采、格羅皮烏斯、保羅·克利、康定斯基、費寧格……他們和席勒一樣行色匆匆,并非對這里情有獨鐘,而是被命運的風偶然刮到魏瑪。其中好幾位離去時都是抱恨而別。
1919年德國第一個共和國將魏瑪定位為政治中心,但卻很難把共和國總統和部長們的名字加入魏瑪引以為榮的長廊。文化無疑比政治權力有更持久的影響力。公爵和夫人們顯然對此心知肚明。誰會記住一個小國的掌權者?他們只是歷史天空中的流星。但是當他們的名字和文化巨匠聯系到一起,就成為襯托恒星的星云,可以憑借他們的光芒一起閃爍。
格羅皮烏斯、保羅·克利、康定斯基、費寧格出生在4個不同的國家:德國、瑞士、俄國和美國。能匯集到魏瑪,是因為他們都是具有挑戰意識的藝術家,都堅信自己具有卓越的創造力,因而被包豪斯的理念吸引而來。
首先到來的是格羅皮烏斯。費爾德向魏瑪大公推薦格羅皮烏斯接管學校。雄心勃勃的格羅皮烏斯雖然正在戰壕中忍受煎熬,卻同時著手設計未來的包豪斯。他的干練作風、社交周旋能力以及堅定不移的意志是包豪斯得以誕生的重要條件。保羅·克利、康定斯基、費寧格受邀到包豪斯任教,把他們的現代主義藝術觀念帶到了魏瑪。然而幾年中,魏瑪當地居民對于學校過于開放的思想和學生們過度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直很不滿,終于在6年后取得議會的支持,將學校關閉。包豪斯被迫遷到德紹。
為了紀念學校在魏瑪的成就,現在這里有一所包豪斯魏瑪博物館。其中最重要的展品是受聘于學校的這幾位已具有一些國際聲譽的藝術家的作品。還有后來被大眾熟知的包豪斯設計的用具。K.J.朱克爾和W.瓦根費爾德設計的臺燈最初受到嘲笑,后來卻成為包豪斯最成功、最受歡迎的實用物品。
從克拉納赫到魏瑪,經過歌德時期,以及之后的幾代公爵都致力于藝術品收藏投資,魏瑪積攢了數量可觀的繪畫、雕塑和中世紀宗教藝術品。現在主要展示在宮殿博物館。它是魏瑪最宏大的一幢建筑。其中的4個房間以魏瑪4位詩人命名:歌德、席勒、維蘭德、赫爾德。
1925年之后,小城再沒有德國文化的大師級人物居住于此。但是建筑仍在,作品永存。曾經流動在其間的氣息是魏瑪最寶貴的財富。舊城很小,如果是散步,一個上午就能轉兩圈。如果你是想來充充電、養養眼,城中心和附近地區值得一看的地方簡直逛不完。
如今魏瑪有64,000常駐居民,是歌德席勒時代的十倍。每年還有5千到6千學生在包豪斯大學和李斯特音樂學院學習。1999年,魏瑪以“歐洲文化之城”的名義高調舉辦了慶祝活動。回歸古典的魏瑪變成了一個博物館之城,所有可能保存下來的遺跡都被精心愛護,甚至包括在歌德主持下鋪設的石子路和他在伊姆河公園花園房設計的小徑都顯得彌足珍貴。二戰空襲的破壞已被小心修復,看不出一點痕跡。2004年一場大火使安娜·阿米莉亞公爵夫人圖書館損失慘重,5萬本沒有復件的古籍永遠消失了。這場令人痛心的災難使魏瑪一下子警醒起來,全方位的護衛措施立刻著手進行。更精密的電子防火設備已經被移植到古典建筑的肌理中,以便完好保存先輩的遺產,留給后人繼續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