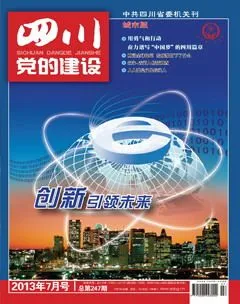創新撬動四川未來的杠桿
□ 本刊記者 鄧灼
創新撬動四川未來的杠桿
□ 本刊記者 鄧灼
自從美國的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宣稱有十種力量碾平了這個世界,我們才清晰地認識到:我們已經置身于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相同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因為信息化,已經由金字塔型變成了扁平型。
世界是平的了,要想不淪為世界的“打工者”,成為別人大腦的工具,你就必須學會創新。因為創新才有知識產權,才有新發明與創造,才能把產品做得一流。
世界變了,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中等收入陷阱與粗放發展的嚴峻考驗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2013成都財富全球論壇開幕晚宴上發表主旨演講: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既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是,中國也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化解長期粗放發展積累矛盾的嚴峻考驗。
四川是這一特征的濃縮。
2012年,我省人均GDP為29627.73元(4691.92美元),成功跨越“貧困陷阱”,躋身中等收入行列,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歷史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4000-5000美元后往往會成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分水嶺”,其經濟發展往往存在較大變數,處理得當,通常會出現一個較長的經濟高增長期,并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人均GDP的更高突破。反之,則可能出現經濟震蕩,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進而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四川正處在這樣一個重要轉折時期。
綜觀世界經濟,其發展階段分為要素驅動、要素驅動向投資驅動過渡、投資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過渡、創新驅動5個階段。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時,就必須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利用知識、技術、企業組織制度和商業模式等創新要素對現有的資本、勞動力、物質資源等有形要素進行重新組合,以創新驅動內生增長,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
從四川這一階段性特征看,近年來,勞動要素對我省經濟增長貢獻率持續下降,到2011年僅為13.8%;資本要素的貢獻率在2009年出現拐點后持續下降,2011年只有40.2%;科技進步貢獻率呈穩步上升趨勢,2011年達到45.9%,已超過資本貢獻率,成為推動四川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這一切表明,我省已進入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過渡的發展階段,只有改革創新才能破解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加快我省發展進入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軌道。
隨著省委十屆三次全會上“三大發展戰略”的提出,我省吹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號角。多點多極是總攬,“兩化”互動、城鄉統籌是路徑,創新驅動發展是動力,創新驅動將成為中國夢四川篇章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大不等于強,亟待打造激活創新增長極
作為西部經濟大省、科技大省和資源大省,四川科技研發機構和創新型企業總數長期保持西部第1位,2012年實施重大成果轉化項目241項,帶動產值2400億元,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產值8000億元,獲得國家科技獎勵29項。
但上述成績與我省定下的未來五年戰略目標——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2%,全省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總產值18000億元以上,戰略性新興產品總值超過8000億元,還有很大距離。
同時,大不等于強。作為衡量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我省科技成果轉化率依舊不高。“必須提高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地位,推動企業真正成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應用的主體。”這是業內人士的共識。
基于此,我省提出了“四大創新工程”—— 企業創新主體培育工程、產業創新牽引升級工程、區域創新發展示范工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工程。
圍繞“四大工程”,一系列的生動實踐隨即展開——國家技術創新工程試點的首批示范市縣的“先行先試”,正加快著推動區域內協同創新,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綿陽市先后組建“四川省軍轉民技術轉移產學研聯盟”等9個省級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成功培育軍民融合企業172家,軍民融合產值已達815億元;德陽市與四川大學成立產業技術研究院,計劃投資8.33億元,預期年產值超過100億元。在調研中,僅作為示范縣(區)的成都市武侯區,去年就實現技術交易額24.53億元,而涼山州會理縣更是通過實施135個技改項目,轉化應用8項國家專利,建成“四川省現代產業生產基地20強縣”……
實踐表明,越是經濟復雜困難,越應重視科技在調結構、穩增長、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依靠科技培育新產業、創造新需求、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我省正處于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過渡階段,創新能力居全國中上游水平,具有實施創新驅動的良好基礎。2012年我省知識創新能力、獲取能力和企業創新能力、創新環境4個主要指標分別排全國第9位、第8位、第16位和第11位。
把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創新發展上
“地奧心血康膠囊”成功獲準歐盟注冊上市,實現了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治療性藥品進入發達國家主流市場的零突破;50多家機構與四川有500多個合作項目,為川企新增收入207億元……6月16日,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和省委十屆三次全會精神讀書班上,中國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白春禮帶來一組與四川相關的案例。案例背后,共同直指一個主題:創新驅動的新機遇、新動力。
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唐橋從中讀出一個“道理”——企業應當是創新的主體。他認為,這種創新應該體現在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應用等全方位,“觀念要創新,以消費者、市場說了算;增長方式要創新,從過分依賴單一產品到打造全價位產品線;技術要創新,覆蓋口感、度數及風格;體制要創新,銷售要緊貼市場,減少中間環節。”
坦言正在“過冬”的攀鋼集團公司總經理張大德豁然開朗:“單純從鋼鐵產品找突破口,空間不足,但放寬視野,比如瞄準釩鈦資源綜合利用,我們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到世界頂尖,從而走出困境。”
區域創新、企業創新、科技創新,歸根結底,需要制度的保障。日前,我省研究制定了《四川省創新型省份建設試點方案(征求意見稿)》,從四川的特殊省情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入手,分析了四川加快發展、科學發展,面臨轉方式、調結構的迫切需求,以及環境資源壓力與日俱增的緊迫形勢,明確了四川創新型省份建設的思路,提出了創新型四川建設的組織保障。
這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組織保障。異曲同工,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最為關注的也是“保障”,他認為:從創新的層級來看,技術創新是最底層的,而體制機制和模式路徑的創新是更高層面的,轉方式、調結構屬于模式創新的范疇。一項新的技術順利轉化為產品,造福于人類,也必須有制度的保障。
白春禮也特別提到,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完全依賴市場之手不行,政府必須從產學研三個層面適當介入,對整個創新產業鏈施加必要的規劃、引導、組織、協調等影響。
其實我們看到,今年以來,全省各地都將科技創新作為了績效考核的長期固定指標,加大了考核權重,并且綜合運用財政引導、稅收政策、金融支持等多種手段,促進各類企業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