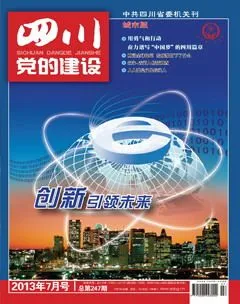當一座城市瀕臨資源枯竭
——是坐以待斃,還是絕地重生?
□ 本刊記者 雷怡安
當一座城市瀕臨資源枯竭
——是坐以待斃,還是絕地重生?
□ 本刊記者 雷怡安
輝煌
上個世紀60年代,全國各地的自然資源儲量豐富,如果哪個城市占有大量的自然資源,那么肯定是發展中的佼佼者。
“山上有森林,地下有煤礦”是華鎣市曾經的城市寫照。正因為有了得天獨厚的礦產資源,華鎣市相繼建起了華鎣山礦務局、華鎣煤礦等20多個以煤礦為主的資源型企業。至90年代末,國營、集體、個體煤礦達到102個,煤炭開采能力超過每年600萬噸,從業人員超過3萬人,煤炭業產值達到全市工業總產值70%以上,坐上了地方財政收入的頭把交椅。
享有中國天然氣化工發源地的瀘州更是了得,經過50年的天然氣開發,天然氣成為了瀘州發展的重要化工原料、城市及工業燃氣,并促使瀘州成為了全國18個化工基地之一和四川“西部化工城”。在上海交易所,瀘天化成為了瀘州僅有的兩個上市股票之一。
毋庸置疑,在以自然資源多少論發展前景好壞的日子,華鎣市和瀘州市占據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困境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部分依托自然資源發展的城市顯現出了發展的弊端。自然資源的過度采伐和粗放型生產導致的后果必定是資源數量的急劇減少,傳統發展的城市在此時遇到了發展的困境。
鄧正曾是華鎣當地很有名氣的煤老板。通過技改擴能,到2007年,彪水巖煤礦年產量達到5萬噸,實現純利400萬元。盡管這樣,鄧正卻整天提心吊膽。“壓力很大!”鄧正坦言:“煤礦面臨資源枯竭,再挖幾年,就沒有煤炭可挖了。”
長期偏重煤炭采掘粗放發展的華鎣在90年代遇到了發展的瓶頸。隨著廣安火電廠、成都金堂火電廠、重慶雙槐火電廠等電煤需求急增,煤炭企業長期飽和生產,剩余煤炭資源可采年限銳減。如今,華鎣市的煤炭資源可開采年限已不到3年。
和華鎣有著同樣困境的還有以天然氣為主要資源的瀘州。2009年的一組數據極具震撼力。瀘州市供氣量預計只有15.64 億m3,缺口達到7.34 億m3。民用用氣和工業用氣都經歷了嚴重的打擊。
這一切,讓本來輝煌的資源型城市瀕臨凋敝。
原因
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是一道“世界性難題”,而我國一個以資源豐富著稱的國家也在近幾十年里逐漸顯現出資源匱乏的困頓局面。
資源型城市在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矛盾,除了受資源開采的客觀規律作用之外,還存在諸多體制、機制上的成因。如計劃經濟思維下的直接調配與轉軌時期價格失衡,使一些資源型城市陷入了畸形發展的軌道。長期以來,不少資源型城市缺乏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他們采取“竭澤而漁”、“重開發輕建設”的發展思路,結果是,一旦資源沒了,“好日子”就到了頭。
現有的價格、財稅政策也很難保障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再加上現有政績考核體系對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缺乏科學的考評標準,導致一些地方領導片面地追求GDP增長,不注重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轉型
在與自然資源的對抗中,城市的命運大抵可以分為三種:城市衰敗、人去城空和涅槃重生。
“等到真正資源枯竭再轉型就晚了。”有專家提出自己的觀點。然而,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國外并不缺乏成功的案例。德國魯爾工業區以煤炭、鋼鐵開采為主,在20世紀50年代日漸衰敗,20世紀60年代德國政府對魯爾老工業基地進行改造,經過數十年持續不斷的發展,魯爾地區成功實現了經濟結構轉型。如今大部分礦山和鋼鐵廠關閉了,昔日濃煙蔽日、煤渣滿地,如今天空蔚藍、綠蔭環繞。在魯爾區穿行,如同行走在一個巨大的露天公園里。
前車之鑒,后人鑒之。2008年、2009年和2011年,我國國務院分三批界定了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其中四川的華鎣市和瀘州市上榜。2011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出臺,11月1日,資源稅改革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行。
中國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發展在此時顯得尤為矚目。
“我們將按照華鎣市轉型發展規劃要求,搶抓國家推動資源枯竭城市轉型等重大機遇,進一步加快轉型發展步伐。”華鎣市委充滿信心地定下目標:力爭到2020年非煤產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上升到80%以上,基本實現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
華鎣市借著西部大開發、成渝經濟區、東部產業轉移和國家的資金技術扶持等多項“東風”開始了轉型之路。
華鎣市確定把水泥產業作為過渡產業,將其升級,避免陷入產業斷檔的危機。建起慶華溪口機械加工園、廣華工業集中區機電產業園兩個機加工產業平臺,初步形成了汽摩配件、礦山機械、機械模具、農機制造等四大機械加工制造體系。
資源產業轉型發展,僅靠一兩個產業難以獨撐,必須構建起較為完善的產業體系。
在工業發展上,華鎣還依托華鎣山地產品資源,發展糧油、酒類、豆制品等農產品加工業。
在旅游開發上,依托華鎣山獨特的旅游資源,成功開發創建國家AAAA級旅游區、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省級風景名勝區、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小平故里行,華鎣山上游”,成為川渝旅游熱線,旅游業逐步成為華鎣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
面對資源的不可再生性和日益枯竭的現狀,瀘州市請來了中國科學院、四川省工程咨詢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的專家為瀘州出謀劃策,《如何改變對資源長期的依賴致使發展受限》是討論的中心議題。最終瀘州確定將經濟的構成從單一向多元發展轉變。
瀘州市在城市轉型發展中力爭在酒業發展上有新突破、在古敘礦區規模開發上有新突破、在加快化工產業轉型升級上有新突破、在加快長江機電綜合開發上有新突破。著力發展白酒千億產業:圍繞打造中國白酒金三角核心腹地的目標,全力促進白酒產業向集約化、品牌化方向轉變。做強做大瀘州老窖、郎酒集團兩大酒業龍頭,培育和壯大一批“小巨人”企業。加快推進“名酒名園名鎮名村”、“名酒名鎮”建設,積極發展倉儲物流、包裝、設計等白酒配套產業,構建以白酒生產為主、配套產業協調發展的白酒產業集群。
在全國69個資源枯竭城市轉型道路上,四川兩地的轉型之路是成功的,對轉型后的后續發展,我們還將拭目以待。
(責編:裴佩)
經驗與啟示(二)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模式——
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通過模仿創新模式實現了經濟的騰飛。我國武漢“光谷”則通過引進技術再自主創新,迅速成為湖北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國內外經驗表明,后發地區可以緊緊抓住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資本、技術溢出帶來的新機遇,把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作為主要模式,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后發地區必須通過局部突破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實踐證明,處于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過渡階段的地區應結合自身優勢資源進行產業布局,以高新區、經濟開發區作為科技創新驅動的重要載體,通過構建以城市和大區域為重點的多點多極支撐,以“點”、“線”、“面”等經濟增長極的先行先試,逐步實現整個區域的創新驅動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