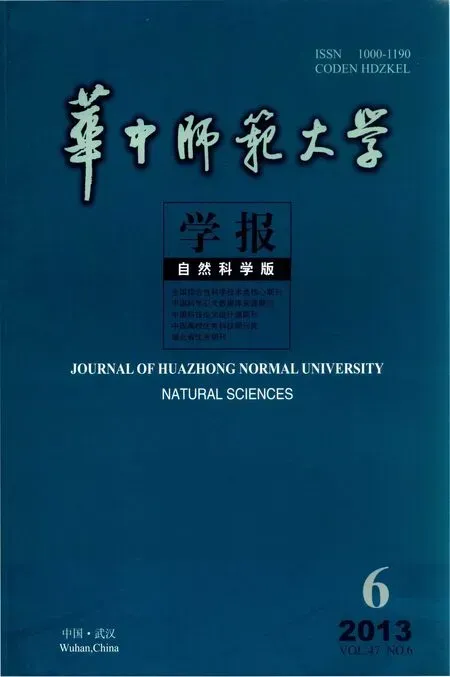江蘇省社會經濟發展的環境效應分析
李在軍,管衛華
(南京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南京 210023)
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各種環境問題日益彰顯,環境質量問題不僅影響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而且成為嚴重制約經濟進一步騰飛的瓶頸.有關社會經濟活動與環境變化關系的研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國外學者分析了經濟增長、人口變動、能源消耗、技術進步等社會經濟因素對環境的綜合影響[1-3].國內學者利用隨機回歸影響模型、向量自回歸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狀況的動態關系[4-6],三次產業與環境質量[7],外商投資對環境的影響[8],環境污染綜合指數與產業結構、環境政策、城市化水平與外商直接投資因素的作用機理[9],地區的貿易開放、政府規制、產業結構、資本、路徑依賴等因素對環境污染的影響[10],人口比重、人均GDP、工業能耗強度對環境負荷的影響[11]等,全面分析了社會經濟增長過程中環境污染狀況的時序動態變化特征.
大多數實證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國的范圍,缺少考察中國環境污染的地區特點,對省域的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作用關系研究更少,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完整的有關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相互作用的分析體系,因此,進行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相互作用機理的分析探究,對如何減輕環境壓力與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實現社會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江蘇省1990年~2010年間年均GDP 增長率為18.4%,在未來幾年間,社會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快速度發展,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省內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突出,基于此,本文利用江蘇省污染物排放量的數據,測度該時期內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并對環境污染指數的年際變化階段進行劃分,構建環境污染影響因素指標體系,分別對各階段內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與相關指標進行灰色關聯分析,從而對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各階段的特征進行闡釋,以期為未來社會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建議與對策.
1 研究方法
1.1 均方差決策
均方差決策法是一種根據信息熵原理設計的客觀賦權方法,通過指標信息量的測度,來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因此具有一定的準確性與客觀性.其基本思路是以各評價指標為隨機變量,各方案在指標下的無量綱化的屬性值為該隨機變量的取值.先求出隨機變量的均方差,將這些均方差歸一化,其結果即為各指標的權重系數.該方法已經在工程技術、社會經濟等領域被廣泛應用[12].
1.2 Mann-Kendall
Mann-Kendall法作為一種非參數統計檢驗方法,該方法不需要樣本遵從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數異常值的干擾,具有檢測范圍寬、人為影響小、定量化程度高的優點,該方法不僅能夠找出突變點,還能劃分突變區域[13].
1.3 主成分分析
基于本文所選相關環境污染影響因素的指標,采用主成分分析進行主因子確定.通過降維方法把多指標轉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即主成分)[4].本文對選取影響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相關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從而選定幾個主因子進行代替,然后求出各個主因子得分.
1.4 灰色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度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來判斷不同序列之間的聯系是否緊密[14-15].分別求出主成分因子得分值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絕對關聯度(ε)、相對關聯度(γ)及綜合關聯度(ρ)列,根據灰色綜合關聯序,判斷因子得分因素對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影響程度.
2 環境污染指標選取
環境污染水平的度量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總量與污染物排放強度(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量)兩類指標[9,16].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故選取污染物排放總量進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衡量.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當前的污染物排放主要由工業生產產生,因此本文選取了江蘇省1990年~2010年間工業廢水排放總量、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工業SO2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六項指標來進行江蘇省歷年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測度.以上數據來源于《江蘇統計年鑒》(1991年~2011)與《中國統計年鑒》(1995年~2010).
2.1 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計算
根據均方差決策計算得出各指標的權重分別為0.177 3、0.179 7、0.165 3、0.177 8、0.124 7、0.175 2.從圖1 可以看出,1990年~2010年來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變化起伏較不穩定,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變化態勢,這表明在經濟發展初始時期,江蘇省環境質量狀況較好,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狀況不斷惡化,整體來看江蘇省環境污染呈波動上升趨勢.為了更好的研究整個時期環境污染指數波動變化與經濟發展因素的影響關系,采用時間突變點進行研究階段的劃分.

圖1 1990年~2010年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變化趨勢Fig.1 Plo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from 1990to 2010in Jiangsu
2.2 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變動階段劃分
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在整個研究期間內波動變化較大,通過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時間突變階段來具體劃分其變化特點,以1990年~2010年間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值為時間序列,采用Mann-Kendall法來檢測1990年~2010年的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突變點,在給定顯著性水平0.05條件下,繪制出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Mann-Kendall統計量曲線(圖2).由圖2,可知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在2003年以后的擴大是一種突變現象,圖2中UF和UB的交點位置大致位于2003年,從而將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劃分為1990年~2003年和2004年~2010年兩個階段.

圖2 1990年~2010年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Mann-Kendall統計量曲線(置信線為α=0.05顯著性水平臨界值)Fig.2 Mann-Kendall statistic curv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from 1990to 2010
3 環境污染影響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1990年江蘇省城市化水平為22%,此后年均以1.86%的速度增長,2010年底達到60%左右,在此期間GDP以年均18.4%的增長率提升,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導致環境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增加,環境污染的破壞與壓力日益嚴重.經濟增長主要通過經濟發展規模因素、結構因素與技術水平因素等從不同程度、不同方向對環境污染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經濟發展初期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巨大的環境壓力,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破壞,而隨著社會技術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的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產業組織結構等的有序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而遏制了環境污染物的排放,減輕了環境污染壓力等問題.社會經濟發展不僅直接作用于環境質量,還可通過環境政策、社會生活以及對外貿易等因素的傳遞作用間接地對環境質量產生影響.本文根據已有研究對環境污染影響因素指標的選取并結合江蘇省經濟社會所處的階段[5,8-9,16-17],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與具有代表性原則,構建了影響環境污染的指標體系(表1),所有數據來源于《江蘇統計年鑒》(1991年~2010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1990年~2010年)與《中國統計年鑒》(1991年~2010年)[18-20].

表1 環境污染影響指標體系Tab.1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mpacts
3.1 1990年~2003年的相關指標的因子得分
對1990年~2003的規模因素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通過主成分分析提取一個主因子,其在各個指標上的載荷分別為0.993、0.994、0.994、0.967、0.991、0.993、0.752,故命名其為經濟發展規模;對1990年~2003的結構因素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兩個主因子,其中因子1在城鎮人口比重、第三產業結構、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費總量及人均汽車擁有量指標上的載荷系數為0.969、0.950、-0.959、0.874,命名其為經濟發展結構指標,因子2在第二產業結構與工業原煤產量指標上具有較高載荷分別為0.861、0.906,工業生產及原煤產量與地區能源存量密切相關,因此命名其為經濟能源結構;對1990年~2003年的技術因素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一個主因子,其在各指標上的載荷系數分別為0.981、0.813、0.898、-0.899、0.906,這些指標與經濟發展的技術條件密切相關,故命名其為經濟發展技術水平.
利用1990年~2003年環境污染影響指標的數據提取到4個主因子,各個主因子的年際得分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公共因子得分(1990年~2003年)Tab.2 Principal factors score(1990~2003)
3.2 2004年~2010年的相關指標的因子得分

表3 公共因子得分(2004年~2010年)Tab.3 Principal factors score(2004~2010)
對2004年~2010年間的經濟規模因素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的一個主因子在工業污染治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指標載荷系數較低為-0.391外,在其他指標上的載荷系數都在0.9以上,命名其為經濟發展規模;對2004年~2010年的經濟結構因素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一個主因子,主因子在各個指標上的載荷系數都在0.8以上,命名其為社會經濟發展結構;對2004年~2010年的技術因素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一個主因子,其解釋方差為75%以上,可以解釋技術因素的大多數數據,其在各指標上的載荷系數分別為0.965、-0.629、0.986、-0.975、0.828,命名其為經濟發展技術水平.
利用2004年~2010年環境污染影響指標的數據提取3個影響環境污染的主因子,各主因子的得分情況如表3所示.
4 環境污染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分析
分別根據1990年~2003年與2004年~2010年間的主因子得分,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對環境污染綜合指數與各主因子分別進行灰色關聯分析,結果如表4、表5所示.

表4 1990年~2003年環境污染綜合指數與各因子得分的灰色關聯度Tab.4 The gra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the factors from 1990to 2003
通過比較環境污染綜合指數與各主因子得分系數間的綜合關聯度,可以發現1990年~2003年間影響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因素主要是經濟能源結構與經濟發展技術水平,其次是經濟規模結構與經濟發展結構.可見,1990年~2003年間江蘇省環境整體污染的嚴重是由其能源消費利用結構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環境污染治理技術水平落后共同導致的.同時,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也對環境污染造成一定的影響.

表5 2004年~2010年環境污染綜合指數與各因子得分的灰色關聯度Tab.5 The gra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the factors from 2004to 2010
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在2004年~2010年間與社會經濟結構綜合關聯度最大,其次為經濟規模因素與經濟發展技術水平.表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科技的進步,環境污染的壓力雖然有所緩解,但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及煤炭為主的能源利用結構,伴隨著不斷擴張的經濟發展規模、人口增長與消費需求的壓力,帶來能源開發、利用與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從而導致環境污染狀況不斷惡化.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對1990年~2010年間江蘇省環境污染的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1990年~2010年間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變化起伏較不穩定,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變化態勢,這表明在經濟發展初始時期江蘇省環境污染狀況良好,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環境污染狀況不斷惡化,總體來看環境污染狀況呈不斷上升趨勢.
(2)江蘇省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在整個研究期間波動變化較不規律,通過時間突變點分析得知,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在2003年以后的擴大是一種突變現象,從而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年際變化劃分為1990年~2003年和2004年~2010年兩個階段.
(3)根據已有研究對環境污染影響因素指標的選取,嘗試構建了影響環境污染的指標體系,從社會經濟的發展規模、結構與技術水平等方面建立環境污染影響指標綜合指標評價體系,基本包含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多方面,但限于數據時序獲取的困難,所構建的指標體系并未全面.
(4)通過灰色關聯分析得出,1990年~2003年間造成江蘇省環境整體污染嚴重的原因在于其能源利用消費結構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環境污染治理技術水平落后.同時,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也對環境污染造成一定的影響;2004年~2010年間第二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及煤炭為主的能源利用結構,是導致環境污染狀況不斷惡化的重要原因.
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增長是短暫的,其動力很快會消失,而環境污染將長期反作用于經濟增長,制約經濟的長期發展.因此,江蘇省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要依靠集約型的增長方式,制定合理的經濟產業規模;依靠和使用科學技術,調整能源利用結構,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廣清潔燃料,采用清潔生產工藝;建立區域環境污染質量監測系統,強化區域環境監督管理和污染源的監控與治理,實施總量控制和達標排放;加強對環境造成污染的企業整治,建立科學、完善的資源、污染權市場和交易機制,形成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良好的反饋機制,實現二者長期、均衡與和諧發展;同時,城市作為人口、經濟、產業的集聚地,是環境污染治理的重點難點區域,今后應遵循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要求,制定科學的城市環境綜合治理規劃,制定有利于城市污水集中處理和生活垃圾安全處置的政策,加強城市綠化、美化及其保護工作.
[1]Grossman Gene M,Krueger Alan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353-37.
[2]David I Stern.Explaining changes in global sulfur emissions:an econometric decomposition approach[J].Ecological Economics,2002,42:201-220.
[3]Dinda S.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a survey[J].Ecological Economics,2004,49:431-455.
[4]郭 瑩.我國各地區環境狀況的主成分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10(21):105-106.
[5]楊 茜.我國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狀況的主成分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5(18):74-77.
[6]李慶華,鄧萍萍,宋 琴.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資源開發與市場,2011(2):131-134.
[7]王張成,馬海鋒.江蘇省產業發展的環境效應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0,29(10):96-100.
[8]章貴軍,付志剛,李妙萍.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的實證分析——基于福建省2000—2008年面板數據[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7(S3):108-110.
[9]楊福霞,聶華林,楊 冕.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效應分析——基于廣義脈沖響應函數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10,36(5):133-142.
[10]藍慶新,韓 晶.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效應研究——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130-137.
[11]羅 帥,李 磊.新疆社會經濟發展的環境效應分析[J].新疆財經,2011(6):5-10.
[12]徐明強,談 毅,等.基于屬性的技術評價方法匹配研究[J].中國管理科學,2005,13(1):48-52.
[13]管衛華,周 靜,陸玉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消費水平的區域格局變化[J].地理研究,2012,31(2):234-243.
[14]劉思峰,郭天榜,黨耀國.灰色系統理論及應用(第二版)[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59-63.
[15]李 健,周 慧.中國碳排放強度與產業結構的關聯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1):7-11.
[16]屈小娥.1990-2009年中國省際環境污染綜合評價[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5):158-161.
[17]趙海霞,曲福田,郭忠興.環境污染影響因素的經濟計量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環境保護,2006(4):43-49.
[18]江蘇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隊.江蘇統計年鑒[G].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2011年.
[19]國家統計局能源統計司.中國能源統計年鑒[G].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2011年.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G].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