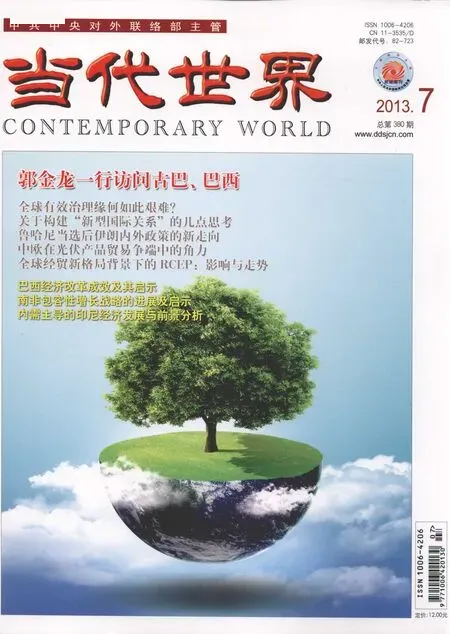巴西經濟改革成效及其啟示
■ 楊志敏/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回顧巴西近百年走過的發展道路,似乎繁榮和危機總是在交替出現,因此被形象地稱為“鐘擺型”發展道路:一場經濟繁榮之后迎來一次經濟危機;一次危機過后面臨發展道路的抉擇、經濟政策的調整。20世紀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開始,巴西開始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內容的經濟改革進程,而2003年盧拉領導的勞工黨上臺執政后,巴西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歷史欠賬
20世紀90年代巴西的經濟改革主要圍繞“三化”,即國有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進行的,旨在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在之后多數年份里巴西經濟保持了增長、嚴重通脹得到遏制、對外貿易實現增長、企業效益得到提高、政府財政負擔有所減少,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此階段的改革也出現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如私有化削弱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忽視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等。
其中,私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經濟控制力。20世紀80—90年代,巴西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政策取向下,實行了多輪國有企業私有化。當時,國企私有化政策似乎是全球趨勢。不過,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實行私有化是為了提高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而巴西則更多是為了緩解公共部門日益惡化的財政壓力。出售國有企業,不僅能快速增加政府收入、甩掉虧損企業、減少政府負擔,還能通過將國企轉變為盈利的私企,增加政府未來的稅收。
到20世紀90年代末,巴西大量的國企甚至包括具有戰略地位的國企均被私有化,其中最為著名的有科洛爾執政時期私有化的米納斯吉拉州鋼鐵公司、卡多佐執政時期私有化的淡水河谷公司等。而最大的國企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則因憲法限制僥幸不在其列。據稱,巴西的私有化計劃是世界上正在實行的最龐大的私有化計劃。20世紀90年代公共財政的一大收入就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據統計,1990—1999 年,巴西私有化收入高達717億美元,其中工業部門占巴西私有化總收入的四分之三。
但是,巴西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政策使公共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的同時,削弱了國家控制經濟的能力,因此在2002年大選時引發了國內的激烈爭辯。有分析認為正是私有化政策使巴西本國的研究開發機構被棄置, 取而代之的是從跨國公司進口技術。據統計,巴西資本貨物進口額由1994年的75億美元升至2001年的148億美元, 同期半成品的進口額從6億美元升至273億美元。盡管外資大量流入, 巴西的固定資本投資率較低,“在跨國公司領導下進行的巴西經濟現代化, 既沒有促進巴西資本積累率的提高, 也沒有促進巴西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巴西在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重增長、輕分配”的理念,結果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問題嚴重。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后期,巴西政府注意到了上述問題,開始發展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并制定減貧等措施。同時,進行了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來緩解社會矛盾、減輕民眾不滿情緒等。但是市場化的改革導向、政府財政控制力的下降等并沒有使上述社會問題得到有效解決。這使得社會公平和正義遭到嚴重忽視,成為20世紀90年代改革遺留的歷史欠賬之一。
勞工黨上臺的經濟改革:有的放矢
首先,巴西政府關注社會公平問題。政府相繼推出“零饑餓計劃”、養老金改革和稅收改革等多項再分配調整方案。其中,在推行“零饑餓計劃”時,新政府大量削減開支,并專門成立了社會發展和消除饑餓主管部門,實行多種社會資助計劃。同時,政府還通過采取分配未耕種土地、增加農作物種植資金支持、設立土著居住區、重新啟動東北部開發管理局、減少農村合作社稅額、鼓勵私人銀行向小農場和合作社借貸等措施進行扶貧。
2003 年盧拉政府繼續采取了“家庭救助金計劃”等擴大再分配的政策。經濟增長和成功的扶貧政策使得約3000 萬巴西人進入中產階層,社會不平等、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趨勢有所緩解。據統計,巴西中產階級人口比重由1992年的32.5%,提高到2003年的37.6%、2009年的50.5%。其中,農村中產階層人口比重,由1992年的13.6%提高到2003年的29.6%和2009年的35%。事實上,巴西已經通過“南南合作”計劃將其創新性的社會政策擴展應用到其他國家。巴西本身已經在國際發展援助方面成為“新興捐助國”。
正是由于巴西政府在社會問題上的成功關注,使得勞工黨政府的支持率節節攀升。據悉,其中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是重要的新生支持力量。據一項民調顯示,在羅塞芙總統就職15個月時,她的支持率高達77%,較2011年12月上升5個百分點,遠高于盧拉(54%)和卡多佐(57%)當政時的民調支持率。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羅塞芙不僅在較為貧窮的東北部地區具有高達82%的支持率,而且在反對黨支持率較高的東南部地區也贏得了75%的支持率。

從科爾科瓦多山俯瞰里約熱內盧。
其次,政府加強對經濟的控制力。
盧拉在競選時主張叫停私有化政策,并決定在不出售國企的情況下,改善公共財政赤字。但是,由于投資者對當時“左翼”勞工黨執政持懷疑態度導致外資大量出逃。因此,盧拉任職初期,巴西的經濟形勢依然嚴峻,他甚至不得不一改反對私有化的政策,繼續實施了一些企業的私有化。最終,其在位的八年時間里僅成立了五家國企。2013年羅塞芙總統在執政不到兩年時間里成立了五家國有企業。相比盧拉政府,本屆政府組建國企的步伐明顯加快,對國企的建設不斷加強。巴西此輪“新國企”風潮,應視為勞工黨自2003年執政以來的三屆政府在政策上一脈相承的結果。羅塞芙政府之所以加速組建新國企,一方面緣于勞工黨執政政策的延續;另一方面與國內外經濟大背景密切相關。羅塞芙上任之初,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各國普遍采取了加強政府干預的反危機措施: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增加對私有企業的股權收購;發展中國家,包括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等拉美國家在內,重現國有化浪潮。
從巴西國內情況看,2012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僅為0.9%,不僅低于2011年的水平,也低于拉美地區平均3.0%的增速。巴西經濟增速回落主要是受外部經濟環境持續惡化的影響,其中,不僅出口部門,而且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表現較差。對此,巴西希望通過振興工業來提升競爭力。此外,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因表現出色,被譽為21世紀國企的代表,這也一改人們對以往國企缺乏效率和浪費資源的看法。
再次,繼續推進貿易、金融和財政改革政策。2003年勞工黨執掌政府后,繼承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注重推進貿易自由化政策尤其是擴大在美國市場的份額;重視區域內經濟一體化建設,重點推動南共市與其他貿易集團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積極吸收南共市的新成員。盡管遇到一定的阻力,但巴西政府繼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時,著力在財政改革方面,推動增值稅改革、降低工資稅、調整對社會保障融資稅,以及減少稅種等措施。
巴西近十余年經濟改革成果:成績斐然
首先,中產階級隊伍在持續壯大,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有重要意義。
自2003年以來,巴西有了5000萬新消費者。2005年15%巴西人屬于“A階層”(家庭收入超過6745雷亞爾)和“B階層”(5174—6745雷亞爾);34%屬于“C階層”(1200—5174雷亞爾),而51%屬于“D階層”(751—1200雷亞爾)和“E階層”(少于751雷亞爾)。之后幾年,上述比例變化為人口的“A階層”和“B階層”占18%;“C階層”(即中產階級)上升至36%;“D階層”和“E階層”下降到46%。進而在2007年“C階層”即中產階級比例上升至46%;“D階層”和“E階層”下降到39%。最新統計顯示,中產階級比重達到了55.05%,而“D階層”和“E階層”進一步下降到33.2%。
其次,巴西投資安全評級獲史上新高,提振外資的信心。
2008年,標準普爾評級機構首次將巴西評為“可靠投資”級別。由此巴西進入了不存在拖欠風險的外資可靠國家行列。為此,外資繼續看好巴西的基本經濟面。據統計,2011年拉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額超過1530億美元,占當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10%,創下該地區該項紀錄的歷史新高。該地區絕大多數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分享了外資流入的一杯羹。其中,巴西成為最大的贏家,當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達660億美元,約占拉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44%。包括巴西在內的拉美在吸引外資方面表現不俗,主要得益于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動復蘇,二是拉美自身宏觀經濟基本面良好。外資流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地區,主要是“綠色投資”的增加,實際上該地區的企業并購活動是停滯不前的。同時,通過增加信貸和減稅等刺激辦法,使巴西更好地克服了金融危機。再次,巴西實現了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國向債權國的歷史性轉變。
2005 年,巴西停止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款,并在2006 年中實現了石油的自給自足。2009 年,巴西在經受全球危機的情況下,宣布將向IMF注資100億美元。由此成為47個能夠向IMF定期提供運轉資金的成員國家之一。這些資金主要用于幫助發展中國家。最后,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巴西躍居全球第六大經濟體。
2011年,巴西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位居美國、中國、日本、德國和法國之后。同年,巴西的外匯儲備有史以來首次超過3500億美元;巴西的國際貿易收支得到改善,出口額達到2560.4億美元。此外,巴西勞工部的數據顯示,2010年巴西正規就業崗位增加了280萬,致使正規就業的工人數量達到4400萬。但是巴西的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而有些挑戰是長期困擾巴西乃至整個拉美地區的痼疾。首先,收入分配不公、土地所有制難題可能成為巴西經濟改革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其次,減貧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任務艱巨。目前,巴西仍有4000 萬人生活在貧困中。與此同時,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據統計,2002—2010年,巴西北部地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4.7%提高到5.3%,東北部地區從13%提高到13.5%。東南部地區從56.7%下降到55.4%。再次,外需與內需對經濟增長的關系處理問題。外部經濟環境依然嚴峻。2012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僅為0.9%。主要是由于全球礦產品需求下降、價格下跌,巴西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和歐元區經濟形勢惡化等致使巴西的鐵礦石等礦產品的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不過,可以看到巴西GDP中,國內需求比重達到60%,而凈出口占比最高年份也不超過25%,平均只有10%。因此,發展內需是巴西經濟增長的關鍵。此外,運輸和電信基礎設施不足、稅制繁瑣而復雜、教育和衛生保健系統欠完善等瓶頸也限制著巴西的發展。
巴西經濟改革重要啟示:與時俱進
首先,一定要堅持經濟改革。
收入分配不公、土地所有制落后、地區發展失衡等阻礙巴西經濟發展的長期頑癥和根本性問題,因此也是經濟改革堅持的方向和長期任務。這種改革或許需要跨越數屆政府、數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為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西歷屆政府一直在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治理落后地區發展問題方面積累了經驗。巴西1988年的憲法闡述道:消除不平等問題是巴西聯邦政府的根本性目標之一。盧拉上臺后也重申了憲法的規定就是使消除地區發展不平衡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中心任務之一。其次,世易時移,變法亦矣
。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具體政策;二是發展模式。在具體政策方面,近20年的改革歷程中,巴西出臺的許多政策都有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但應當隨著條件的變化,適時調整政策,因為不可能存在跨越時空的經濟改革“萬靈藥”。以“雷亞爾計劃”為例,它在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條件下,對控制通脹、吸引外資、穩定經濟功不可沒,但堅挺的雷亞爾幣值不僅使巴西出口受損,而且該計劃吸引了投資資本的流入。因此,在其自身存在制度缺陷和外界環境的變化的情況下,應當及時調整政策。而在發展模式方面,要做到有所揚棄。巴西過去歷經初級產品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新自由主義以及如今的所謂“務實主義”的發展模式,每種發展模式的出現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更有其“生命周期”,因此要學會主動地調整發展模式,這樣才能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而不是像巴西發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僵化地、被動地靠外部或內部的經濟危機來顛覆發展進程,從而被迫轉換發展模式。再次,關注民生是永恒的主題。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忽視民生,小則可能出現社會動亂,大則影響國家政權穩定。這點在選舉中就體現在選民“用腳投票”上。哪個政黨能夠關注并改善民生、注重社會公平和正義、促進經濟發展,那么它就能夠贏得政權。2002年巴西勞工黨首次上臺,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忽視社會公平正義的弊端盡顯;到2010年勞工黨再次贏得大選,也在于民眾對巴西“左翼”政府過去
八年執政效果的認可;而再到2012年民意調查給予了現政府極高的支持率,也在于勞工黨進行的經濟改革有效繼續矯正了20世紀90年代改革的失誤,在減貧和促進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方面做出了成效。不過,巴西在改善民生方面仍任重道遠,例如,“令饑餓計劃”尚未實現讓每個巴西人吃上一日三餐的目標。今后,更多地關注民生問題、讓經濟改革成果惠及絕大多數民眾是巴西政府的努力方向。
[1] 阿德里亞娜·厄塞爾·阿勃德努爾.巴西經濟走出“失去的十年”陰影[J].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 ,12(5).
[2] 巴西政府網站:http://www.brasil.gov.br/
[3] 江時學.拉美發展前景預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4] 呂銀春.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5] Wilber Albert Chaffee, Desenvolvimento:Politics & Economy in Brazil,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8.
[6] Patricia Justino and Arnab Acharya,“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Processes and Inputs”, PRUS Working Paper No. 22,April 2003, Poverty Research Unit at Sussex,University of Sussex.
[1] EIU, Country Report—Brazil, May,2012.
[1] EIU, Lula Pushes Reform, Country Monitor, August 4th, 2003.
[7] Michael Reid, Brazil’s Unfinished Search for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Autumen 1998.
[8]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equality,“An Overview of the Brazilian Economy”. http://www.econ.fea.usp.br/nereus/eae0503_1_2006/hadch19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