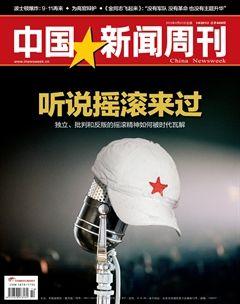江津“草根金融”之路
滑璇
李永祥從包里掏出兩根黑白相間、長約二十公分的硬刺。 “刺是豪豬身上的,這是我今天下鄉的收獲。”李永祥說。
李永祥是重慶市江津區綠豐農業信用擔保有限公司(下稱“綠豐擔保公司”)總經理,4月12日,他下鄉突擊檢查了一家豪豬養殖場。
“我們給這些企業在銀行做貸款擔保,貸款發下去后,就得及時掌握企業的經營情況。”李永祥說。
李永祥說的擔保源于,2011年重慶推行的“三權”抵押融資改革。為確保農民能夠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居民房屋和林權從銀行貸到資金,重慶市成立了一批國有融資擔保公司,綠豐是其中一家。
“農村有很多資源,但不能變成資產。‘三權抵押就是要盤活這些沉睡的資產,讓資金流動起來。”江津區金融辦綜合科科長廖章言說。作為重慶的農村金融服務改革創新示范區,江津區又在“三權”基礎上增加了農村塘庫堰承包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
2013年初,銀監會明確表示支持探索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農房等抵(質)押貸款業務。“在江津,類似的試驗已進行了近兩年。”廖章言說。
“三權”抵押
從豪豬養殖場回來,李永祥直奔下班前的最后一站——江津區五舉醬菜有限公司(下稱“五舉公司”)。在總經理楊培國的辦公室,李永祥一邊聊,一邊拿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不停地記著。
五舉公司成立于1998年。2002年開始,產品出口到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雖然發展勢頭迅猛,但一年要收上萬噸蔬菜原料,缺少流動資金成了公司的短板。
沒有流動資金,楊培國游說1萬多家蔬菜種植戶把菜“賒”給他,為此不僅提高了收購價格,還要支付賒欠期間的菜價利息。
“由于是農村廠房和土地,銀行不認,所以貸不出錢來”。楊培國說,有時候要找朋友東挪西借,還找過高利貸。
2009年,楊培國將資產抵押給重慶市農業擔保有限公司和綠豐,利用它們的擔保從銀行貸出數百萬。2011年“三權”抵押融資推開后,楊培國的醬菜存貨、廠房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都成為抵押資本,貸款數額逐年增加。
今年,五舉公司在綠豐抵押了部分醬菜存貨和近千畝土地承包經營權,也是綠豐為它作的擔保,一舉從重慶銀行拿到貸款450萬。
“其實這些抵押物評估下來至少值1200多萬,但是為了減少風險,只貸了不到一半的數額。”李永祥說。
江津區金融辦的廖章言解釋說,抵押物價值大、貸款額度小是“三權”抵押融資中的常規做法,“這樣可以減少銀行和擔保公司的風險,還能增加貸款成功率”。
其實,五舉公司2011年首次用土地承包經營權貸款時并不順利。從七八月開始申貸,到資金全部到手,歷經四個多月,差點錯過收購時間。“那時剛推廣‘三權抵押,銀行不理解。廠房在他們眼里都是‘看得見摸不著,更別說土地承包經營權了。”楊培國說。
綠豐的加入讓貸款順利了許多,通過實地考察生產經營狀況,組織農業專家進行專業評審,并依次向董事會、主管副區長報批,綠豐決定為五舉提供全權擔保。如果五舉還不上錢,綠豐將承擔100%的連帶責任。
作為江津區農委的下屬公司,綠豐的擔保,讓銀行放下了心,當年底,貨款發到了楊培國手上。
據江津區金融辦統計,截至2013年3月底,江津累計發放“三權”抵押融資貸款1936筆,總金額超過11億元。
資金互助社
“三權”抵押的試點同時,江津區還嘗試利用農村資金互助社為社員個人和微型農業企業發放小額貸款。白沙鎮的明星農村資金互助社(下稱“明星互助社”)便是一例。
50歲的楊永科是明星互助社的發起人和理事長。16年前,他靠著從農商行貸出的5萬塊錢起家,進行房地產投資。
農民出身的楊永科深知小額貸款對農民創業的重要性。2010年12月31日,楊永科開創明星互助社,注冊資金300萬。
兩月之后,黑石村椿桃農家樂的周萬平,成了互助社的第一個客戶。
與楊培國一樣,經營農家樂的周萬平也借過高利貸。在交納了100元的入股資金后,周萬平很快通過互助社的調查審核,用住宅面積128平米的農房進行抵押,一周內就拿到了10萬塊的貸款。如今,周萬平已連續貸了3年。
“我們的放貸速度比銀行快,一般5萬以下的,只要1~3天,10萬以上的也就一個星期。但是我們的手續和銀行一樣,非常齊全。”楊永科說。

放貸前,互助社要對借款人進行調研,借款人所在的村社、家族也要出具意見。
“其實,村民入股時交了多少錢和能從互助社貸出多少錢沒關系。能貸多少錢,主要看家庭實力和貸款用途,用我們農村的話說就是看這筆錢能不能雞生蛋、蛋生雞。”楊永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互助社是一個封閉的金融機構,只對入股社員提供貸款。由于社員彼此熟悉,本金又是大家共同出資,所以哪個借款戶家里有點風吹草動,互助社馬上就能聽到風聲。社員崔先敏曾從互助社借出2萬塊錢養豬,沒多久便轉變經營方向把豬全部賣光。當天晚上,崔先敏的擔保人、村支書一個電話打到互助社匯報情況,第二天互助社便與崔先敏取得聯系,提醒她還款。
截至目前,互助社放出的貸款尚未出現一筆不良記錄,沒有擔保人真正承擔過擔保責任。“因為有利息,農民自己就會控制貸款數額,”廖章言說,“而且農村的思想并不十分開放,一些人仍然守著‘借錢就是沒本事的老觀念。”
由于帶有內部互助性質,互助社的貸款用途五花八門,囊括了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為開展種植、養殖、手工業等經營活動貸款自是當仁不讓,而結婚、生子、蓋房子也都可以借錢。按照用途不同,貸款利率各不相同,讀書、治病年利率最低,只有6%;買車等奢侈性消費年利率最高,達18%。
貸款額度小、用途各異,加快了互助社的資金流動。黑石村一位社員貸款3萬,只用7天就全部還清。
由于大部分是小額貸款,互助社成了銀行的補充,那些尋求大額貸款的客戶直接被推薦給銀行。楊永科介紹,截至目前,互助社共有社員1530戶,累計為240戶農民放貸1905.64萬。其中涉及“三權”抵押的171戶,貸款1488.8萬。
風險隱憂
有了兩年實踐,楊培國對“三權”抵押融資的貸款套路開始駕輕就熟。每年重新申貸前的兩個月,便著手準備各種文件,保證12月蔬菜收購期開始前資金到位。
事實上,2005年底掛牌的綠豐,早在成立之初便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及地上附著物納入擔保業務范圍。當時的做法是,將土地租金和管理費投入算作抵押資本。但在同一年,當一家公司試圖以這樣的資本到工商部門注冊成立公司時,卻遭到拒絕。后經政府協調,方才成功。
2011年3月,重慶高院下發《關于為推進農村金融服務改革創新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其中規定: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居民房屋、林權抵押糾紛案件,當事人按照“三權”抵押登記時是細則設定的抵押權,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有效。
盡管有了司法上的肯定,以土地承包經營權設定抵押,在實踐中仍有法律瑕疵。李永祥介紹,涉及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銀行貸款,基本都須進行抵押擔保。“但是土地都是集體的,理論上說,你在抵押的時候就要征得每一個農戶的同意。”李永祥說,“這樣的操作非常麻煩,實踐中根本做不了,是一個空白地帶。擔保公司只能被動接受貸款戶的承諾,但法律上沒法確認。”
與此同時,一旦借款人無法還款,如何確保土地承包經營權等抵押物變現,也成為“三權”抵押融資的瓶頸。廖章言坦承,這是他眼中最大的發展障礙。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江津從去年起開始籌建農村產權綜合交易平臺。作為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的一個窗口,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在內的多種權利,將在此平臺流轉。貸款風險發生時,那些抵押給擔保公司的經營權,將被重新包裝,尋找下家。而權利流轉換來的資金,將被用于填補擔保公司的資金損失。
互助社下一步的發展也讓楊永科有些擔憂。“現在全鎮200多平方公里,只有一個工作點。很多農民要跑很遠才能找到我們。雖然市里、區里對我們都非常支持,但中央不發文,我們在金融機構中始終是個‘另類,拿不到支農再貸款,放貸資金就可能不夠。”楊永科說,僅2011年、2012年兩年,互助社的資金缺口就達到了3000多萬。
為了控制風險,銀監會對農村資金互助社設立了“對前十大戶貸款總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的規定。楊永科現在相當后悔當年沒有吃透這些規定,“否則我的注冊資金肯定上千萬”,而現在想要增資就變得非常困難。
“因為存在這些問題,江津的抵押融資還說不上有多大成功,但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金融行業的‘嫌貧愛富,”廖章言說,“我們依然在不斷嘗試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