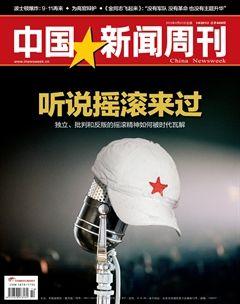比爾.蓋茨的水稻秘密
徐智慧
圍繞轉基因水稻進行的爭論,2013年春烽煙再起。
在比爾·蓋茨登上博鰲論壇的講臺前,國內“反轉(反對轉基因)派”科學家已經對他即將發表的演講進行了一輪“炮火準備”。當蓋茨在博鰲宣布“綠色超級稻”研發成功,馬上引起該品種是否為轉基因水稻的質疑。
“轉基因”標簽從何而來?
悄悄研發四年之久的“綠色超級稻”,在揭開神秘的面紗之前,早已被貼上了轉基因水稻的標簽。究其原委,皆因其與轉基因研究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去年轟動一時的“黃金大米”事件中,有媒體發現,現身衡陽小學食堂的轉基因“黃金大米”,得到蓋茨基金會的支持。據《每日經濟新聞》調查,“黃金大米”研究者、美國Tufts大學教授湯廣文曾在2009年5月向蓋茨基金會陳述“黃金大米”在中國的試驗情況,證明蓋茨基金會一直在為“黃金大米”試驗提供資金支持。
公開信息顯示,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進行的轉基因水稻研究,曾獲蓋茨基金會資助。綠色和平轉基因研究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蓋茨基金會目前正在資助國際水稻研究所及其合作伙伴共同研發“黃金大米”,是該項目的三個出資方之一。
而“綠色超級稻”的命名者,是轉基因農作物研究領域的“旗手”——中科院院士張啟發。
2005年,張啟發提出“綠色超級稻”概念。他希望借助這一計劃,搞清4萬個水稻基因的功能,進行基因重組和分子設計育種,培育出高產、抗病的超級水稻。2007年,美國科學院院刊介紹了張啟發的“綠色超級稻”計劃。同年,他和袁隆平一同入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眾所周知,張啟發是鐵桿“挺轉派”。他牽頭研發的轉基因水稻 “華恢1號”和“Bt汕優63”,于2009年8月獲得農業部頒發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獲得該證書后,只須通過農業部的審定,就可進行商業推廣。因此,在這兩種轉基因抗蟲水稻獲得安全證書前后,曾引起激烈爭論。
據綠色和平轉基因研究人員透露,轉基因水稻中的抗蟲基因Bt,這種蛋白來自于一種叫做“蘇云金芽孢桿菌”的菌類,而非來自水稻自身。某些害蟲吃了含有Bt蛋白的水稻之后,會被毒死。恰恰是這一點,引起“反轉派”的猛烈攻擊。
“昆蟲都無法下口的轉基因水稻,對人體就沒有害處嗎?”社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而張啟發所進行的安全性試驗,被質疑時間太短—一兩周的大鼠實驗,不足以證明其對哺乳動物健康沒有損害。
因為民間組織和“反轉派”科學家的反對,“華恢1號”和“Bt汕優63”獲得安全證書的時間至少推遲了兩年。這一點說明,中國反對主糧轉基因化的聲音并不微弱。
“解決窮人吃飯問題”
“‘綠色超級稻不是一個品種,而是一個方向。”該項目首席研究員、中國農科院黎志康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所謂方向,是指研發防病防蟲、節水抗旱、高產穩產的稻種。”
黎志康是“全球水稻分子育種計劃”的發起人。早在1998年,他在美國發起這一計劃,旨在為非洲、亞洲不發達地區解決糧食安全問題。黎志康歸國后,這一課題亦獲國家支持,列入“948”重大項目。
2008年,蓋茨基金會找到黎志康,洽談農作物品種改良方面的合作。在博鰲,蓋茨回顧了他的夫人梅琳達與黎志康初次會面的談話:“(黎博士)告訴我們,可以開發新的水稻品種,只須較少的肥料和水,在試驗階段的結果相當不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研究,可以開發出適合非洲貧窮國家的稻種。”在蓋茨看來,黎志康的研究與蓋茨基金會全球慈善的目標不謀而合。
2009年,“綠色超級稻”項目正式啟動,共獲得蓋茨基金會提供項目經費1800萬美元。目標是在3年內培育至少15個水稻新品種,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南亞和中國西南部進行示范和推廣。
蓋茨博鰲演講中亦著重強調“綠色超級稻”對貧窮國家和地區的意義。在題為《為窮人投資》的演講中,蓋茨表示,在今后20年,中國農業將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些經驗可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糧食危機。
圍繞這個終極目標,“綠色超級稻”必須實現增產。
在水稻增產方面,傳統科學家袁隆平已經樹立了業界標桿。但在黎志康看來,袁隆平創造的高產,是以高投入為前提的。也即在高產田上,投入足量肥料、農藥和人力,以確保高產。優良的稻種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而“綠色超級稻”的目標,則是“少投入,高產出”。中國18億畝耕地中,三分之二屬于中低產田,“綠色超級稻”的目標,是在中低產田上實現糧食增產。比起只能在高產田實現高產的稻種,“綠色超級稻”更有現實意義。
“中國西部和南部有很多‘靠天田,如果能在那些缺乏水源、耕種條件惡劣的農田上實現增產,才能真正幫助那里的農民解決吃飯問題。”黎志康說。
在育種方法上,黎志康也與袁隆平不同。
袁隆平已將水稻雜交技術幾乎窮盡。而在黎志康看來,水稻雜交的方法已落后于時代。他采用的技術,是全新的“分子標記育種”,即標記出水稻4萬個基因的不同功能,找出具有諸如抗旱、高產、防病、防蟲的基因,將這些基因整合起來,培育水稻良種。
“‘綠色超級稻未使用轉基因技術”
特殊的分子育種方法,需要一個強大的數據技術平臺。為此,黎志康和華大基因結成合作伙伴。這是一家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基因組學研究公司,1999年代表中國參與了“人類基因組計劃”,2002年獨家完成水稻全基因組測序。在“綠色超極稻”研究中,華大基因扮演了數據及標記技術平臺的角色。
然而,華大基因在生物基因領域的名聲,也讓“綠色超級稻”頭上的轉基因疑云更加濃重。當外界傳來非議時,華大基因和黎志康選擇向公眾坦白澄清。
“在‘綠色超級稻一期研究中,沒有使用轉基因技術。”黎志康表示,為實現低投入高產出的目標,“綠色超級稻”希望獲得少用肥料、農藥的性狀,在獲得這些性狀時,沒有用到轉基因技術。在抗病蟲害方面,也沒有使用張啟發院士研發的Bt轉基因方案。“其實,中國在水稻轉基因方面,可利用的技術亦十分有限。”黎志康說。
“比爾·蓋茨要解決窮人吃飯的問題,并不排斥轉基因。”華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長張耕耘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但隨著技術進步,相當一部分原來認為只有轉基因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完全可以用非轉基因的辦法來做。”
張耕耘介紹,“綠色超級稻”的研發中,運用了全新的“全基因組標記”手段,結合黎志康運用的“全基因組分子育種”,可令研發過程大大縮短。分子育種是個已提出20年的概念,但以前沒有實際用途。目前隨著基因技術的進步,用分子標記的方法,可以有目標地進行基因改良。
“比如小米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基因,事實上30年前就發現了,但一直無法改動它,現在用我們自己的技術,一年就搞定了,效率就是這么高。”張耕耘說。用傳統方法做基因組分子改良,至少要用七八年時間,現在一到兩年就能完成。
事實上,以“全基因組分子改良”技術的先進程度而言,其效率跟轉基因已經一墻之隔。如果單純追求某些特殊性狀,而該性狀卻不為某個物種擁有,那么,轉基因似乎就是一個必然的選擇。而“綠色超級稻”研究團隊并未承諾永遠放棄轉基因技術。
“‘綠色超級稻現在沒有使用轉基因技術,但我們并不排斥轉基因技術。”黎志康說。
支持研究,謹慎推廣
袁隆平院士早已表態,他并不反對轉基因研究,但在轉基因糧食對健康、環境造成的影響沒有定論之前,對稻谷、小麥、玉米等主糧的轉基因化須持謹慎態度。
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的薛博士,認為抗蟲轉基因植物的大面積種植,對田間害蟲有一定毒殺作用。但這種壓力會迫使害蟲“進化”,形成所謂的“超級害蟲”。同樣,抗除草劑轉基因植物的大范圍使用,亦會使得農民加大除草劑用量,結果形成“超級雜草”。這種“進化”,在美國的轉基因大田里已經出現。
而最讓“反轉派”擔憂的是,科學界對轉基因植物的各種影響還沒有完全認知。在薛的研究中發現,轉基因棉花葉片表面的一些結構和常規棉有些許不同,可能導致的后果不可預測。
轉基因生物的轉入基因可能會出現“逃逸”,也就是說通過一定途徑進入其它生物或者同種生物的常規個體中,給它們帶來新的性狀。這就是反轉派所擔心的“基因污染”。
而在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上,“挺轉派”“反轉派”各執一詞。但法國、土耳其對轉基因玉米、水稻的安全性試驗證實,轉基因食物對大鼠的健康造成損害。法國因此禁止了轉基因玉米的種植。
2009聯合國出版的一份研究報告,亦對轉基因主糧的商業化推廣持否定態度。這份題為《國際農業知識科學和技術發展評估》表明,轉基因農作物在政治、環境、生物的安全等方面表現出諸多不利影響。比如,轉基因農作物造成的基因流動,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同時,轉基因導致的糧食增產,在實踐中被證實與實驗室數據相差甚多。
該報告還指出,轉基因農作物的技術掌握在少數大公司手中,導致耕種收益更多地流向大型公司和少數富人,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國內外對轉基因食品的管理,根據立場和利益,可分為三種類型,即支持大力發展的美國,限制發展的歐盟,支持研究但限制應用的中國。”薛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美國最為寬松,只要是沒有明顯害處的轉基因食品,基本上都能夠順利推進,轉基因食品的標識也是自愿的。歐盟基本上是保守勢力,對于轉基因延續了一貫的態度:限制使用,盡量不生產。中國的轉基因研究力量很強,雖然目前是轉基因作物的進口國,但卻是潛在的出口國,所以中國對轉基因食品的管理介于美國和歐盟之間。
“我們傾向于大力發展轉基因作物,但是在應用上很慎重。這么多年,我國只批準了六種轉基因植物的商業化,其中三種是食品(甜椒、番茄和番木瓜),都沒有形成氣候或者只是在部分地區種植。”薛說。
“挺轉派”亦將中國對轉基因農作物的審定視為“嚴格”。
農業部的對轉基因農作物的審定程序長達數年。“光這個審定的時間,也足以把研究項目‘殺死。”黎志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