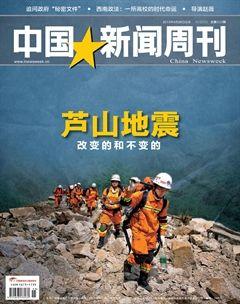災后心理干預一二三
上次汶川地震,震出個順口溜,說要防疫情、防記者和防心理治療師。新聞采訪報道中血腥的圖片,心理咨詢強賣強送,在當事人不愿意的情況下問詢悲傷,除經驗不足外,也說明了一些問題。我想,需要防范的其實是那些缺乏人道精神的“工作狂”“窺私癖”和“災難旅游家”。 4月20日蘆山地震,國務院提出為避免交通堵塞,無關車輛盡量不要占道,私自去往災區,這條原則也適用于心理援助。
汶川地震后的第四天,我去災區進行了心理干預,有些情形印象深刻。
在成都某大醫院,我見到一個12歲女孩,她因左腿被截肢而傷心不已,對醫生和護士、對心理援助者均抱以戒備和反抗的心態。
我的運氣好,到病房時,剛好她母親帶著她妹妹找到了這個女孩。她們抱頭痛哭,這女孩邊哭邊自言自語道:“你們到哪兒去了,怎么把我一個人丟下,我還以為再也見不到你們了。”媽媽說:“奶奶死了,爸爸還在救人,他也在找你,我和妹妹一直在找你,你都把我們給急死了。”我默默地坐在一邊,看著8歲的妹妹沒人顧得上,就拿出紙巾,讓妹妹給媽媽和姐姐遞過去,融入親情。一家人通過這種你來我往、互相不放棄的哭訴,補充了互相缺乏的歷史,從而完成了她們哀悼的儀式。僅僅數分鐘的工夫,這女孩就一反以往的刁蠻、任性的特點,變得安靜合作。
在災難發生之初(一周內),災民還未從“地震”“喪親”“受傷”的驚恐狀態中恢復過來,你問他們什么,他們都搖頭說“不、不、不”,此時既不適合采訪,也不適合任何心理干預。人類從宇宙洪荒中生存下來的一個技能就是“否認”,即暫時屏蔽任何信息,好像否認事件發生一樣。在短期內,這對個體具有保護作用,一般這個“休克”的不應期可持續數小時到數天。
那么,這段時間,該對他們做什么事呢?
首先,提供基本生理需要。人在極度驚恐時,大量耗能,所以提供具有能量的熱水、牛奶、點心對安撫他們的情緒非常有幫助。然后,引領并提供安全的居所。有些人在麻木狀態下不知道保護自己,有些人毫無目的地亂跑亂動,需要有人引領他們離開危險地方,到相對安全的地方。被子、毯子、衣物要供應充足,最好有很多抱枕,因為處于驚恐狀態下的人們情緒上如孩子一樣,懷里抱著東西使他們有安全感和連接感。
而最重要的,是親人的陪伴和聯系。熟悉的親人在身邊是最好的安撫,使得人們感到有支持、有連接和有希望。波士頓爆炸案后公布一個尋人軟件值得借鑒,軟件只提供兩個輸入選項:所尋人的特征、信息,找人的聯系方式和地址。知道親人活著的消息比任何干預都有效。
有些人會喋喋不休,反復述說當時發生事件的經過,這也是一種應對方式。他們能夠從危險中逃出來,需要自己反復確認自己的存在,所以聆聽是最好的干預態度。我認為,心理救援最重要的核心是提供支持、提供力量和提供希望!
在一次對消防隊員的干預中,一名新兵講了這樣的故事:一名老大娘在已經傾斜的樓房里死活不肯出來。沒轍,這位新兵戰戰兢兢地坐吊車上到五樓,給大娘做工作。余震不斷,樓房發顫,戰士頭腦一片空白,咕咚一下給這大娘跪了下去,說:老人家,您已經活了不少年頭啦,可我還沒活夠哇,求您讓我多活幾年吧!獲得“英雄”稱號的戰士,老為自己下跪的事感到丟臉,覺得自己不是英雄。
災區工作人員的心理狀況,同樣值得關注。他們除了工作緊張外,也會目睹和耳聞一些悲傷事件,甚至浸泡于其中。戰士、消防員、醫務工作者、新聞人士以及當地干部等,這些人員在心理學上有一種稱呼叫“無助的幫助者”,這里主要指他們的工作“耗竭”狀況,極度疲勞、覺得自己低價值、無能,不能做更多,不能幫到別人,一般這種狀況在連續工作一周后就可以發生,因此對這種人群應該注意更換工作人員和提供后續的心理咨詢。
特別需要關注的是,當救援者面對創傷,來自自身過去的創傷會被激發時,會出現“用力過度”的表現,如情緒反應也過度,行為反應過度,這時,他們不再適合去助人,他們也失去了工作的立場,他們應該從“幫助者”變成“被幫助者”!
總之,在災難發生之初(一周內),反復詢問災難及其后果本身就是一種災難。所有去現場的人,都應先學點心理危機干預知識,但近期內不宜做專業的心理干預,所謂需要治療的創傷后應急障礙在數月后才能確診。對于危機干預或心理援助,非專業心理人員還是遠離災區吧!
施琪嘉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武漢心理衛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