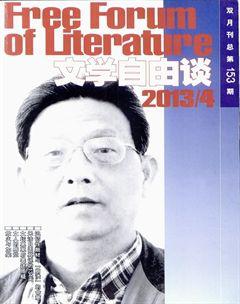文壇“某某后”表述質(zhì)疑
劉衛(wèi)東
“某某后”是當前文論中一個被默認為有效的關(guān)鍵詞,而且不斷膨脹發(fā)酵,似乎到目前已經(jīng)一統(tǒng)江湖了。打開報紙、刊物可以看到,“某某后”說法不絕于耳:“50后”佳作迭出,爐火純青;“60后”紅得發(fā)紫,神氣活現(xiàn);“70后”、“80后”話題頻出,喧囂不已;“90后”已經(jīng)毫不示弱,閃亮登場了。各種老少“某某后”濟濟一堂,顯得文壇興旺發(fā)達,讓人欣慰。每個“后”都是獨立的,每一代都有地盤,新世紀文學(xué)發(fā)展和研究的格局在“某某后”的引領(lǐng)下呼之欲出。真是開談不說“某某后”,讀盡詩書亦枉然。但是,面對此情此景,我卻有些疑問。
用“某某后”給作家“站隊”有效么?
查閱一下資料不難知道,“某某后”源于文化地震學(xué)理論,根據(jù)是,最近幾十年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迅速,日新月異,每一代成長的生活、文化資源都有巨大差異,因而,每一代都會跟上一代產(chǎn)生“代溝”。由于年齡差異造成閱歷不同,產(chǎn)生“代溝”是肯定的,即便是在外部環(huán)境相對固化的古代,孔子也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人生體驗。“代際差異”與其他理論一樣,是一個模型,并不是精確的判斷,正如孔子不是在四十歲生日當天感到“不惑”的,也沒人會這么認為。但是我們談代際的時候,就認真了,煞有介事,一定要看對方出生年月,然后認為“70后”肯定是一伙的,“80后”之間肯定聲息相通,其實都是捕風(fēng)捉影、望文生義。
從生活經(jīng)驗可以知道,個人心智的發(fā)育與年齡的增長并不是步調(diào)一致的。就文學(xué)成就來看,有的少年得志,有的大器晚成,這兩種情況都能找到相應(yīng)例子。就大家耳熟能詳?shù)摹?0后”作家而言,別說討論他們文學(xué)的共同特征,恐怕將他們并置在一起,我們自己都會覺得有點削足適履,亂點鴛鴦譜。按照年齡來說,最早的“80”后作家才三十出頭,可能剛窺文學(xué)堂奧;這還排除了那些尚未提筆的“潛在”的作家,四十以后才開始寫作,后來成為大師的也不乏其人。眾所周知,1918年,魯迅三十七歲,發(fā)表了他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當時魯迅不算年輕,但是“憂憤深廣”(茅盾語)的思想正是漫長積累的結(jié)果,沒有時間醞釀和歲月打熬是無法出爐的。人往往年少輕狂,為賦新詞強說愁,實際上不算數(shù),幾乎很難找到三十歲就思想成熟定型,然后一生一以貫之者,因此,自己三十歲時候說的話,別人三十歲時候說的話,當不得真。到了晚年,檢點經(jīng)驗、反躬自省、品評人物,有了閱歷的底子,此時的寫作才算金玉良言。“代際差異”在我看來僅算觀察當代社會分層的一個視角,其有效性連被拋棄的階級視角都不如,如今被拿來作為研究新世紀文學(xué)的一個標尺,實屬烏龍。就算強調(diào)代際,我認為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年齡作為標簽。丹納在《藝術(shù)哲學(xué)》中提出過影響文學(xué)的“種族、環(huán)境、時代”的三要素,其中的“時代”,跟代際略微沾邊。實際上,考慮到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情況非常復(fù)雜,東部“80后”和西部“80后”,城市“80后”和農(nóng)村“80后”千差萬別,“環(huán)境”因素才不能小覷。
在文論中強調(diào)“某某后”有什么問題?
我不反對“某某后”表述,但是建議限定在一定范圍內(nèi),現(xiàn)在的問題是動輒談代際,把年齡表征當做了創(chuàng)作本身。從文學(xué)史看,年齡表征與創(chuàng)作特色合一的情況有過巧合,“戰(zhàn)后的一代”或叫“垮掉的一代”就是例子。美國戰(zhàn)后出生的一代人在六十年代掀起了叛逆風(fēng)暴,毒品、搖滾樂以及“革命”燒紅了他們的神經(jīng),離經(jīng)叛道甚至反人類的花招層出不窮,但是歷史證明,很快他們就偃旗息鼓,穿上正裝進入寫字樓,變成了新一代知識精英,多年之后不出意外地成為新的非主流嗤之以鼻的對象。在我國,就“80后”而言,因為是“獨一代”,他們從出生就受到社會和大人的關(guān)注呵護,難免會有生活在鎂光燈下的感覺,但是就他們的文學(xué)追求而言,并不一致,按年齡將他們“一鍋燴”,無疑是不恰當?shù)摹R虼耍?0后”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學(xué)概念,而不應(yīng)該作為文學(xué)研究的切入點。看《歷史研究》可知,“80后”其實得名在先,至于接下來演繹出的“70后”、“90后”以及“某某后”,就是順道搭車了。
我感到擔心的,是過分強調(diào)“代際差異”后出現(xiàn)的畫地為牢、資源壟斷現(xiàn)象。目前情況是,很多“成果”先入為主地把代際差異作為談?wù)撟骷业钠瘘c,并衍生、引申出與此相關(guān)的下游產(chǎn)品,用“某某后”來給作家和批評家分門別類。2004年,滬上某人主編了《重金屬——80后實力派五虎將作品精選集》,推出了五位“80”后作家,開創(chuàng)了把“某某后”當做賣點的先河。“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80后”作家剛出道不久,就被幕后推手貼上了標簽?zāi)贸鰜矶凳郏噲D憑借新鮮面孔換個好價錢。其實操作者對此心知肚明,在序言中就連稱這幾位新秀“差異甚大”,但是依然如此這般,可見場外因素才是重點。我們今天來看這幾位作家,并未取得預(yù)期成就,不是他們成長得太慢,而是當年被過度消費,現(xiàn)在他們除了尷尬的于事無補的“虎將”之名外,仍然需要更有耐心和更有智慧的努力。目前打出“80后”旗號的各種文學(xué)活動如過江之鯽,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創(chuàng)意,顯而易見,這股風(fēng)潮很快就會被“90后”代替,而諸多如今的“80后”如果棲息在這個窠臼中,總有一天會被“新銳”奪走地盤,無家可歸。
更具有癥候意義的是所謂“80后”抱團取暖的觀點。有些批評者力主同代人互相關(guān)照,認為“80后”心靈相通,闡釋更容易“貼肉”和有效。猜都不用猜,這些人當屬“80后”,因為文章內(nèi)容表達出一種溢于言表的本位意識。“80后”其實不屬于弱勢群體,一直門庭若市,從來不乏關(guān)注,但是現(xiàn)在有人大聲疾呼,就擺明了要求資源重新分配的意愿。面對“80后”作家,同代的批評家并不是當前格局中的權(quán)威闡釋者,但是,在他們看來,自己才是理解本代人的最佳人選。如此特意強調(diào)代際差異,并且將其作為文學(xué)批評的理由,不僅荒謬,而且違背了基本的批評倫理。我不否認同一代的批評家和作家需要共同成長,但是前提不是相互“關(guān)注”,私相授受,結(jié)成圈子,而應(yīng)該強調(diào)人各有志,尋求個性。因此,這個話題的重點應(yīng)該倒轉(zhuǎn):“80后”批評家不應(yīng)該只關(guān)注同代作家。
“某某后”表述為什么大行其道?
新世紀以來,缺乏原創(chuàng)思想的文論界舉步維艱,飽受詬病。面對紛繁復(fù)雜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場,文論幾近植物人,失去了闡釋和判斷的能力;除了圍觀起哄和介入各種雞毛蒜皮,在重大問題上毫無建樹。此時,理論簡單明白,玩法老少咸宜的“某某后”及時趕到,單騎救主。按照年齡排列作家,后浪推前浪,倒也省時省力,其樂融融。文壇新人輩出,需要命名,這是批評家的必答題,但是,一番絞盡腦汁之后,他們拿出了“某某后”這樣不算答案的答案來勉強交差。盡管劃分“某某后”的方法缺乏創(chuàng)意,但是目前批評家也找不到更好的闡釋方法,這應(yīng)該算作是批評家的無能和恥辱。不知“某某后”的玩法還能使用多少次(已經(jīng)有人在說“00后”了),而批評家的顏面也不知何時能夠挽回。
但是,上述分析只是問題的表層。“某某后”能夠獲得媒體首肯,共同開發(fā),共享成果,恐怕僅僅說是思想?yún)T乏時代的權(quán)宜之計還不完全準確。“某某后”中其實隱含著進化論因素,這才是商家喜聞樂見的賣點。“五四”時期的先賢們,就玩過“新青年”的把戲,把年齡作為坐標,讓文壇遺老自感落伍,而青年們歡呼雀躍,以為自己才是進步力量的化身。青年文化即流行文化,把賭注押在青年的身上,永遠都不會錯。商家對“70后”和“90后”的炒作力度,明顯不如“80后”,就是因為后者目前是時尚主力人群,不過隨著“90后”的崛起,可以預(yù)見,商家很快就會向他們獻媚邀寵。放眼四望,以“80后”為名的文化產(chǎn)品層出不窮,實際是占風(fēng)氣之先的青年文化披了“80后”這件外衣;而對于“70后”,商家則大打溫情脈脈的復(fù)古牌。從目前文論看,用“某某后”的方式找出文學(xué)發(fā)展的“新的增長點”,明顯是商業(yè)操縱文化的表征。
就文學(xué)來說,“新”意味著作家與以往文學(xué)史對話后產(chǎn)生的原創(chuàng)質(zhì)素,是艱苦思考和探索后的結(jié)果,絕非與生俱來,因為人的面孔“新”,就認為文學(xué)也隨之而“新”,是進化論幻覺,根本是無稽之談。在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引入“某某后”,并且認為可以從中找到文學(xué)發(fā)展的線索是緣木求魚。不少學(xué)者在“某某后”問題上申請了課題,生產(chǎn)了論文,成為了權(quán)威,因此即便其中有很多問題,他們也不愿放棄自己的象征資本,況且有商業(yè)文化從旁邊策應(yīng)慫恿,他們更是騎虎難下。
“某某后”表述的危害
在當前文學(xué)研究格局中,“某某后”成為劃分學(xué)術(shù)領(lǐng)地不言而喻的依據(jù),也成為缺乏原創(chuàng)理論的學(xué)界聊以自慰的“創(chuàng)新點”。所謂研究者根本無須動腦,查下作者的履歷表就可以“某某后”地發(fā)表一番看法,實際上,他們的參照物就是“80后”,而結(jié)論還是根據(jù)多年前《萌芽》雜志居心叵測的比賽得出的。如果跟蹤幾位有影響的“80后”,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除了年齡相似,創(chuàng)作旨趣迥然不同,完全無法相提并論。然而,研究者仍然死抱代際不放,言之鑿鑿,除了懶惰無能,似乎沒有別的解釋。如果任由現(xiàn)狀發(fā)展,不但無法取得真正有價值的學(xué)術(shù)成果,還會因為人為制造藩籬而誤導(dǎo)、挫傷具有獨立探索意識的作家。
當“某某后”成為座談會、組稿和發(fā)表論文的必要條件時,文學(xué)生態(tài)和學(xué)術(shù)生態(tài)的平衡被打破了。原本自然競爭的格局,被年齡劃分成了多個互不聯(lián)系的條塊,并且有各立山頭,不相往來之勢。我們看到,1989年12月出生的作家,被強行綁定在“80后”集團中,而1990年1月出生的作家,理所當然被視為“90后”(參見陳平編選的《80后作家訪談錄》及陳文伍編選的《90后獲獎作家中學(xué)校園佳作》)。心理認同和排斥,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作家的心態(tài),而代際霸權(quán)一旦被放大,會使作家寫作時陷入“年齡焦慮”。
作家只分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不分“某某后”作家。目前“某某后”表述變成了一個黑洞,每個進入研究者視野的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都會被用年齡的眼光審視一番,然后再談創(chuàng)作的特點、突破和貢獻,似乎沒有這個程序,就無法為該作家定位。每個雄心勃勃開始做文學(xué)夢的年輕人沒有想到,自由自在天馬行空的寫作,也像論資排輩的辦公室的格局一樣,每個新入職者,都會被引導(dǎo)到放著自己名牌的格子間。這樣的文學(xué)格局,幾近不斷“推陳出新”的工業(yè)流水線,而充滿靈性的寫作,變成了打著出廠日期的超市中的貨品。文論界不應(yīng)繼續(xù)依賴“代際差異”模式,按照慣性“某某后”下去,而應(yīng)當把握住時代和作家作品的脈搏,做出令人信服的、無愧于文學(xué)發(fā)展現(xiàn)狀的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