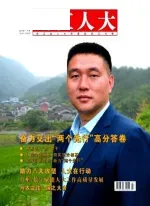我們圓桌會:共話城市治理
/朱狄敏 謝金金
我們圓桌會:共話城市治理
/朱狄敏 謝金金

圍坐在圓桌前,“我們”是平等的個體,有著相同的話語權,討論同一藍天下的城市治理。張林攝
從兩年前的默默無聞到今天成為杭州城市治理實踐上的一個標志性品牌,《我們圓桌會》在城市的公共治理領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平等、公開、多元的“圓桌”形式,一幅城市治理主體的“我們”圖譜漸漸呈現。
小圓桌討論大問題
解說:《杭州市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筑保護條例(草案)》提交人大討論。
應敏(市住保房管局):2007年擱置下來以后,我們沒有停下來。
解說:城市里的老建筑對于杭州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潘一禾(浙江大學):自己的根。
魏英杰(評論員):把這個城市、把文化都能夠串聯起來了。
解說:現存老建筑的狀況又是如何?
劉曉東(市規劃局):我都有一種救火的感覺。
…………
“關注我們的生活,關注我們的城市,‘讓我們生活得更好’!”2012年11月7日,《我們圓桌會》節目如期播出,話題是杭州市民十分關注的“保護老建筑究竟難在哪里?”
據悉,《我們圓桌會》是杭州電視臺綜合頻道的一檔互動交流談話類節目,于2010年12月20日首播,每期時長30分鐘,每周一至周五20∶00—20∶30播出。該欄目秉承“民主促民生”的理念,就城市共同關注的話題,邀請專家、政府工作人員、市民等各界人士共聚一“桌”,對話、溝通、交流,達到理解與共贏。在話題上,注重新聞事件切入與社會現象分析相結合,注重把輿論熱點中社會心理分析、情緒疏導與專家學者所關注的深層次思考和背景相結合。
截至2013年1月30日,《我們圓桌會》已播出500多期,涉及260多個城市公共話題的討論,先后有3500多人次嘉賓走進演播室,成為杭州城市治理實踐上的一個標志性品牌。
“創新執政,務實傳播,公民參與,只要有心,大有可為。《我們圓桌會》搭建政府、媒體與公民平等溝通的平臺,省會城市臺成為理性傳播的領跑者,接地氣、有膽識、有誠意。媒體一小步,民主一大步。”2012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主辦的“2012中國年度電視掌聲·噓聲”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陽光大廳隆重舉行,杭州臺《我們圓桌會》獲得了“年度掌聲”。
近年來,杭州市政府積極改良民眾參與的渠道與方式,擴大協商民主,推行“讓民意領跑政府”的開放式決策。《我們圓桌會》這個談話類節目正是這樣一個民主民生互動平臺。
“《我們圓桌會》通過城市治理理念的探討,聚焦于城市共同體的精神塑造,注重城市在治理中的職能轉型”,這是復旦大學副校長林尚立教授對《我們圓桌會》定位的評價。浙江大學教授潘一禾表示,《我們圓桌會》搭建了政府與民眾交流和溝通的公共平臺,通過這一節目可以對社會生活、城市建設增進認識,增強對社會的責任感。
可見,把“圓桌會”開到電視上,千家萬戶都來看,還能通過電話、網絡發表意見,小圓桌變成了“一張城市治理的大圓桌”。
“我們”的角色定位
目前,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比較集中,各個人群都迫切希望將自己的意志公開表達出來,互聯網便成為了民意表達最方便的渠道,于是無數單個網民所發出的成千上萬種聲音導致參與的爆炸,由此造成了諸多誤解的產生,問題的積累,分歧的形成。如何讓民眾有序、理性地表達,如何讓政府與民眾良性的互動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政府如何構建制度性民主協商對話的平臺?如何在這個平臺上推進政府行政的公開透明?政府決策過程如何向老百姓開放、讓老百姓參與?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圓桌會》是政府開放式決策的延伸,是開放式決策的常態化。堅持以知識與價值引領社會發展,以‘民主促民生’,體現了人文關懷和城市情懷。而它平等的交流、民主的對話本身就是正確價值的體現。”欄目總策劃、杭州市政府研究室原主任王平說。
杭州市清晰地意識到,現代城市治理必須從城市共同體的價值觀念出發,塑造一種現代的群體認同觀念——“我們”,才能真正樹立城市良性發展的社會基礎。
那么“我們”又包括哪些人呢?從官方文件《關于創辦交流談話類電視欄目“我們圓桌會”實施方案》中似乎可以找到“我們”的表述:“我們圓桌會”體現黨政、市民、媒體“三位一體”和黨政、院校、行業企業、媒體“四界聯動”的理念。因此,“我們”就是杭州這一城市共同體的代名詞,不管是官員、老百姓還是專家,都是“我們”中的一員,對解決城市問題、促進城市發展負有共同的責任。圍坐在圓桌前,只有職業的區別,沒有身份標簽、沒有高低順序、沒有等級高下,“我們”的人格是平等的,有著相同的話語權。
復旦大學城市治理比較研究中心在對該欄目分析報告中指出,《我們圓桌會》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都是對“協商治理”理念的一次有益嘗試,它是一種具體的問題解決載體和意見溝通模式,同時又是一種哲學層面的城市理念,是城市治理理念與城市問題的解決途徑的有機結合,體現了“桌面上的平等溝通”與“桌面下的有效治理”兩個層面的復合。

媒體一小步,民主一大步。《我們圓桌會》榮獲2012“年度掌聲”。項 輝 俞春江 攝

《我們圓桌會》已成為杭州“民主促民生”工程的一個標志性品牌。
實際上,欄目的定位從創立之初到現在也經歷了多番調整。如改進市民代表的產生機制以保障參與的多元性,不斷為欄目挖掘現行制度資源等,尤其是2012年開始,欄目中逐漸出現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身影。
“這不僅開辟了一條人大代表聯系選民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創新實踐在力求與現有體制接軌”,王平對此做出了積極評價。其實,“圓桌會上的‘我們’只是這個城市共同體的一個縮影,杭州市的社會建設還需要更多的‘我們’。這要求政府搭建更多的互動平臺,創造條件培育市民的公共精神與政治參與意識,從而形成具有獨立性和差異性又擁有平等對話權的‘我們’。”王平說。
“城市公共事務治理中,市民的參與既是民主的體現,又是政府優化治理的一個很好的資源。通過城市治理過程中所有層面的公民的有序參與,最終形成城市對人生活本身的回歸。”復旦大學城市治理比較研究中心主任韓福國在欄目的分析報告中寫下了這番評語。
對話的力量
圓桌會作為黨政機關借助媒體開展民主民生互動的平臺,給予了“我們”圍繞城市治理議題進行平等、理性對話和交流的渠道,成為黨政機關決策的重要參照,其成效逐漸顯現。
——對話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效能。杭州市積極創設各種平臺讓杭州市民參與對話,在圓桌會上,民眾可以就衣食住行等民生問題直接對話職能部門領導,同時通過討論和互動,專家、行業企業和市民關于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發展等方面的意見得以匯集。
“過去由于城市公共治理上缺乏良好順暢的溝通渠道,一些誤解與分歧難以消弭。現在,利用‘圓桌’溝通打破了隔膜”,王平認為,“圓桌”的積極影響已經顯現。圓桌會上提到的“蔬菜直通車”、“公交車接駁地鐵方案”、“交通擁堵治理”等建議已被相關職能部門接受并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措施。
——對話有利于培養公共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追求“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人們的主動參與性非常弱,缺乏“公共性”的價值訴求。《我們圓桌會》作為公民參與政治的一環,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培養,而這也正是評價政府治理良莠的標準之一。浙江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余遜達教授認為,“最好的治理必須是最有助于培育市民精神,最有助于提升公民參與能力的,杭州人民的公共精神的培育是否達到最佳的狀態,杭州人民的知識、認知水平是否得到最有效的提升是杭州市是否得到最好治理的兩個尺度”。
潘一禾教授則寄希望于圓桌會“形成一股正面的引導力量,以我們的主動意愿喚醒那些沉默者”。如今圓桌會正成為民眾對話黨政機關、實現民主權利的平臺,民眾的聲音開始變得強有力,積極性也得到極大的提升,每個人都平等的以主人翁的姿態出現。
——對話有利于民眾情緒的釋放。對話對于任何一種政治形態來說都是必須的。“哲學最高的水平就是一種有意義的商談”,當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認為該欄目很重要的價值就是對話。缺乏對話,民眾與政府之間就容易形成誤解。圓桌會的目的也是為引導公眾相互理解出發,就社會熱點問題進行建設性的交流互動,關注訴求,反映民意,疏導情緒、引導情緒、凝聚人心,達到城市各個生活群體之間,尤其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行為互動和信息交流,達成一些基本共識,即便達不 成共識,也要相互的理解或者相互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較為有效地釋放民眾的情緒。
對話背后的社會力量
“杭州很多經驗的推動力量都來自于社會,治理的動力也來自于社會”,林尚立評價,正是社會力量的推進促使杭州市政府加快了調整角色和定位。
經驗表明,公眾參與程度的高低與該地區的工業化、城市化、財富等有著很強的正關聯性。杭州市的經濟發展一直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經濟總量和產值也一直處于增長狀態,民營企業發展勢頭良好,高新技術發展迅速。福布斯在發布“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時以這樣的口吻報道杭州,“讓杭州進入世界視線的不僅僅是西湖,更多的時候是民營企業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民眾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其開始注重對個人及納稅人利益的維護以及對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渴求。物質上的富裕有利于民眾積累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經驗。正如浙江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副教授葉國文所指出的,“杭州市的民主實踐,運用了復合民主這一實踐形態,以民主形式創造發展,同時又以發展促進民主建設。而這種模式與杭州市的經濟條件、民眾文化、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不無關聯。”
政府和民眾的互動方式,體現了社會文明的程度。政府與民眾的互動越廣泛、越平等、越具有相互約束力,民主的理念才能在社會的方方面面體現出來。這些特征在杭州社會參與進程中得以證實。杭州市黨委政府在實踐中提煉了三點工作方針“要不要干由百姓定,怎么干由百姓選,干的好壞由百姓評”,從而讓民眾有序參與城市公共治理。
“今天,幾乎每一件關系市民社會生活的重大事項,杭州市民都有民主選擇的權利”。據悉,杭州開放式決策的深化,市民參與、選擇城市發展的熱情得到激發,政府決策更加科學、人性化,市民當家做主已成為杭州市民的一種生活文明。
“這些都是在缺乏現成經驗、缺乏參照的條件下取得的進展”,王平認為,“凡是創新和探索,其實都是不完善的,還需要回到進一步的實踐中去”。所以我們還需清醒地認識到,落實具有持續可行性并非單靠民眾的參與熱情,還需更為細致的民主政治理論建設以及悉心推進公眾參與實踐的智慧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