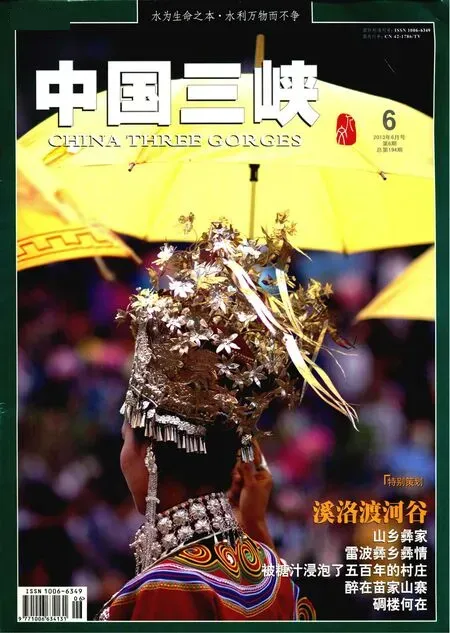生命之水
文/凌寒獨開 圖/黎 明 編輯/羅婧奇

清江。
一
時光漫溯至記憶的上游。
1968年夏日的某個黃昏,天邊涌來滾滾烏云,隨之而來的是雷鳴電閃,狂風大作。雨,瞬時就踩著雷聲的鼓點驟降下來,打在急奔的人身上,皮膚生疼,打在待收的莊稼上,莊稼流淚。兩天兩夜的雨啊,怕是驚散了多少悠閑從容的夢境。
山坡邊的一間茅草屋里,一位中年女人看著屋頂上的茅草縫隙里不斷滴落下來的水滴,聽著不遠處的清江河邊不斷傳來的河水怒吼聲,一邊在嘴里念叨著“這老天怕是要發狂了”,一邊果斷地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出門去看河里的水漲了有多高。漆黑的夜色里,偶爾一個驚雷,閃電劃過,就能清晰地看到河里不斷翻滾的浪頭,那發黃渾沌的污濁毀了原本純清的一江水,她的內心是無可名狀的擔憂。
又是一陣浪頭打來,河水眼看著漫過了田埂。驚恐的她想到了家里的孩子,迅速朝家的方向跑去,可是發狂的河水瘋了一樣朝前趕去,堵住了她回家的路。她連滾帶爬跑上一個高大的土丘,才躲過了浪濤的追趕。天色微明,她的視線里早已一片汪洋,那承載了夫妻倆幾多艱辛和希望的茅草屋已蹤影全無,耳邊隱約傳來的是幾個孩子撕扯著喉嚨在呼喚母親。
天亮了,雨停了,風住了,人們卻哭了。那一場大水,給村里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村民死傷無數,一半的房子沒入水中,有的人家甚至全部死于那場大水的魔手,成了絕戶。飽滿待割的莊稼顆粒無收,大地一片渾黃滄桑。原本靈動清秀的水之神,一瞬變臉就撕裂了人們膜拜的心。
……
2008年夏日的一個黃昏,我和外婆并排坐在清江河邊的石階上,聽外婆蒼老的聲音從容地講述著一個關于水的故事,那個在大水里抱著一根圓木漂了兩天兩夜被她救起的孤兒,時間的雙手讓他從一個失家的孩子變成了臉上滿是皺紋的中年漢子。此時他松開了牛繩,讓牛兒散淡地吃草,聽著述說,他不時凝重地點頭與補白。我知道,他,她,心底的那份蒼涼與無奈凌越四十年光陰仍然能夠清晰觸及。
追溯這份記憶的根源,無疑是植于自己內心最深處對水最原始的渴望與感知。現在看來,這種記憶是長久的,是永恒的,是將會伴隨著事件親歷者一生的記憶。
我相信,關于水的命題,從此將從這里發源,穿越人長長的一生。
二
水,井水,清江水,在我心里,是故鄉的眼,是童年的夢。
記憶中那汪深井,方圓幾十戶人家,吃、喝、洗、漱所用的水全靠從這口井里提取,每家每戶清晨所做的第一份功課就是去水井挑水。都說早上的新水最養人,最甘甜。薄霧輕啟中,村民們相繼打開家門,挑著水桶晃悠著踏上了去一里外的水井的路。哼個小曲,吹聲哨子,彼此間打個招呼,美好的一天便拉開了序幕。水桶伸進井口,井水不疾不徐地蕩開幾圈水波,井水澄澈,不摻半點雜質,無須過濾,裝了就走。踢踢踏踏的腳步聲中,夾雜著幾只狗狗歡快的吠叫,那是它們在和自己鐘情的狗狗打著招呼。寒來暑往,善良的村民淳樸的意念里,知道是水養育了村民,相伴相攜著走過無數個春秋,井水便具有了物質之上深層次的意義,從此對這口井有了深深的尊重與感激之情。
大人對那一眼清泉,是敬重。孩子呢,則是向往。
7歲那年秋天,家里的大人都去了地里做農活,留下我和6歲的華表弟在家里。那個年代的貧乏與單調,永遠是下一代人無法想像的沙漠斷層。不知是誰首先提議,去那個井邊玩吧,那水好清好涼,喝了生水肚子也不疼。于是,我牽著表弟一路飛奔到了井邊,先是扯拉著井邊的那些不知名的野草,小手弄臟了,就慢慢挪到井邊,想把小手洗干凈。不想,瘦小的表弟一個趔趄,一下子就栽進了井里。嚇傻了的我都忘記了要伸出手去把他拉上來,只是圓瞪著雙眼,大張著嘴看他在井水里不停上下撲騰。等到高處田坎上的鄰家叔叔看見這一幕,把表弟救上來時,表弟已經凍得臉色青紫,趴在叔叔懷里昏了過去。而我受到的懲罰讓我這一輩子都不敢忘記。
多年以后,當我們長大成人,我問表弟,你還記得小時候關于水的那一幕么?表弟笑說當然記得,印象中全是關于水帶給我們童年的飛揚的快樂。想啊,一到夏天,河里漲滿了水,水又倒灌進稻田和溪溝,然后便有無數的小魚小蝦誤闖誤撞進我們設置好的那些機關里。整個漲水的季節,我們哪一天不是滿載而歸?

清江。

看看,他記憶里全然沒有我一廂情愿的那段懺悔式的回憶,有的,只是我們滿臉滿身的泥水,手里拿著大桶小盆,赤腳走在田堤上,然后下到水里捉魚撈蝦,毒辣的日頭將白皙的皮膚曬得漸成鍋底模樣。若是碰到河水漫過那道紅紅的杠杠,大人們便要日夜輪流到堤壩上,忙著疏通河道,加高河堤,生怕河神再次發威。
好在每次總是有驚無險,但大人們的心,每每到夏天,便是懸著的,一季的收成啊。莊稼被農人賦予了太多的生存意義。
就像一部老電影,吱吱嘎嘎地喘著氣走完幾圈,便再也無力挪動蹣跚的腳步。漸漸成長的視線里,故鄉山水依然,原始古樸的風景里,許多未解的公式呈現在我的面前。鄰居江小芳一家搬家去了相對繁華的古老背鎮上,故土盡管難離,淚水背后,卻仍走得決絕。坎下老屋里的謝叔叔東挪西借,在靠近公路邊的地方蓋起了新房,并成了賺大錢的手藝人,河邊的三四畝田里的荒草長得比他打醬油的兒子個兒都高,他卻一點都不急,說種了也是白種。
而在我被父親慫恿著挑了一擔水,不,準確地說是桶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的水,柔弱的肩膀被恪得生疼,憤怒地將扁擔甩向一邊的時候;在江小芳那故土難離的六十多歲的爺爺每挑一擔水要歇上五六次的時候;在那一季的莊稼被大水淹沒打亂了原來的賣糧計劃,母親憂心于無力給我們籌上足夠的借讀費的時候:我突然有些明白,似懂非懂中,我卻無力完美地詮釋自己的答案。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遷移,或者離開,有時候,是難舍,是憂傷,但更多的,是與生存現實的一場無奈對抗。
他們,是對的。
三
記憶有時候是有斷層的,也是允許有殘缺的。
長大后,離開家,讀書、工作、成家、生子,日子散淡而平實。那份踏實與真實讓我疏離了曾經關于故鄉的回憶與遐想。風中捎來的消息,一次次激活著思念家鄉的神經。具有反調節、發電、航運、水產、旅游等綜合效益的高壩洲水庫的建成,那些曾經飽經滄桑的村莊永遠的沉落水底,已成為一段來年需要某些介質才能激活的回憶。門前那一馬平川的稻田,每到夏季,便可昂首挺胸的瓜熟蒂落。而故鄉的人們,每到夏秋季節,再沒有漲水之虞,夏蟲鳴叫的夜晚,枕著河風,安然入夢,而這一夢,該是盼了多少年。
必須坦白我的自私與無奈。對于回家,我還是有畏懼的。
曾經無數次將孩子帶回老家,童年的快樂永遠是相似的,樹上可以逮知了,溝里可以撈魚蝦,田里可以捉蛐蛐,風里可以聽鳥鳴。白天的一方樂土,成就了孩子的一身泥水,面對那一盆滿滿的水,孩子不知祖輩的辛勞,總是洗了一盆再來一盆。我告訴孩子,要節約用水,瞧瞧外公挑得多辛苦,可是孩子一臉天真地問我:我不可以將自己洗干凈點么。
我無言以對。
說到底,還是不方便罷!
不知哪天下午,母親打來電話,隔著聽筒,我能聽見母親在電話那頭無法自抑的欣喜:家里裝上自來水了,水嘩嘩的,一直流到家里的水缸里,和水井里的水一樣好喝,甜著呢。以后,孩子來玩,想怎么洗就怎么洗。
母親的喜悅感染了我。一有時間,我就帶著孩子回家,故鄉在一天天的嬗變里漸改了容顏。美了,綠了,秀了。小時候經常光臨的那一大片養魚塘,昔日的污濁與不堪早已被修復重塑,筆直瀟灑的水泥路縱橫交錯在各個水塘之間,塘的四壁被水泥和卵石鑲嵌得美麗極了。而門口的一江清水,更是安靜恬然地流淌著,這一流淌會是經年。外婆口中那個河水發威的故事,將永遠沉落記憶的水底。
最喜還是那口井。
常常一個人悄悄遛到那口圓圓的井邊,依稀記得那踢踢拉拉的腳步聲,那晃蕩在扁擔兩頭的木桶,那一見傾心與一見鐘情的狗狗。只不過是一段時間的流逝,井口已仿佛遲暮美人,井邊長滿了青苔,光滑的石板路已滿是青草覆蓋。但歲月記住了她曾經的風華,記住了那段與村民休戚與共的光陰。這,就夠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物,即使荒廢,即使埋沒,只要能夠記住,只要有人愿意記住,便是美好。令人欣慰的是,在水利技術人員的幫助下,鄉親們在村頭建起了集中供水站,老家的人都跟城里人一樣吃上了健康衛生的自來水,古井與盛水的木桶已成為舊物。
有人曾說,水是生命的源泉,那么,記住那些流逝的光陰和風景,在一定意義上說,便是記住了一些人,一些事。
而記住水,原來,便是記住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