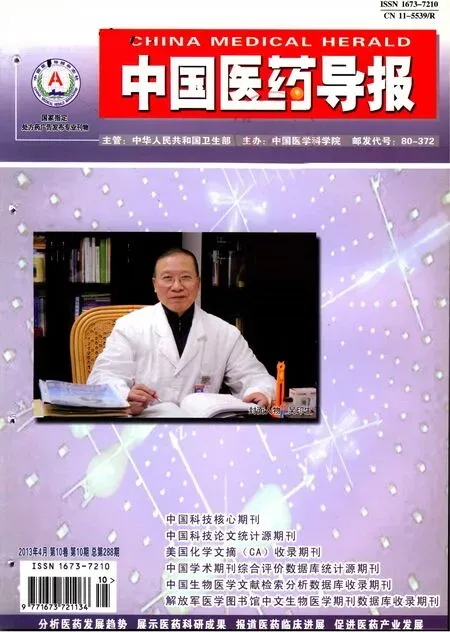團體心理輔導對交往焦慮新兵的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的影響
王 偉 徐維民 司亞東 賀 寧 李春波
1.武警河南總隊醫院心理科,河南鄭州 450052;2.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上海 004677
新兵在入伍初期,由于完全脫離熟悉的人際環境,遠離了原有的社會支持,常會發生交往焦慮。18~22歲是青年社交焦慮的多發期,根據王偉等[1]的研究表明,在新兵的入伍初期新兵的交往焦慮水平較高。因此,在入伍之初如何幫助那些有交往焦慮的新兵建立新的社會支持是他們適應部隊環境期間的重要問題。根據國內許多研究表明團體心理輔導對交往焦慮具有良好的效果[2-3],并有助于改善人際關系,提高適應能力[4]。本研究通過對新兵進行團體心理輔導的干預,探索對新兵應對方式、領悟社會支持、自尊的影響,以尋求改善武警新兵心理健康的途徑。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入伍2周后,于2012年1月8日筆者整體抽取某部武警新訓戰士進行交往焦慮問卷調查,根據王偉等[1]和黃慧蘭等[2]的調查結果,將交往焦慮劃界分定為49分。選擇交往焦慮評分>49分并自愿參加試驗的64人為研究對象,隨機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32人。兩組成員在年齡、民族、家庭經濟狀況、成長環境(城鄉)、是否獨生子女和單雙親家庭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評估工具 ①自編一般資料信息表:姓名、年齡、性別、婚姻、民族、家庭經濟情況、文化程度、居住地、獨生子女等項目。②交往焦慮量表(IAS)[5]包含15個自陳條目,由Leary編制,主要評定的主觀社交焦慮的體驗傾向。采用5級評分,分數范圍為15~75分,分數越高表明交往焦慮程度越高。③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CSQ)[5]包含20個自陳條目,由解亞寧編制,采用0~3級評分,通過評估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兩個因子了解應對方式。④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SSS)[5]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個分量表12個自陳條目組成,主要評定的主觀的社會支持感受,按1~5級評分,計算其社會支持總分,分數越高社會支持度越高。⑤自尊量表(SES)[5]包括10個自陳條目,由 Rosenbery編制,主要評定的主觀的自我評價,得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
1.2.2 評估方法 在團體心理輔導前、后,采用團體測試的方法,分別用同一問卷,對64名被試評估,采取統一的指導語,在同一地點,統一的問卷筆答。
1.2.3 團體心理輔導方法 實驗從2012年1月14日~2012年3月11日結束,兩組與其他戰士一樣參與正常的軍事訓練和心理訓練,并共同參加一次以人際交往為主題的心理健康教育課。實驗組的32人平均分為4組,每組8人。根據國內的相關文獻[6-8]設計團體咨詢計劃。共實施6周(春節期間休息1周),每周1次,每次2 h。每次輔導活動都完成明確的主題,從開始通過游戲建立溫暖、信任的關系,在保持積極、輕松、開放、支持的團體氛圍下,利用角色扮演、行為演練來鍛煉社交技巧,分組討論分享各自的感受,并積極完成每周家庭作業。團體發展經歷了信任接受、困惑探索、自我探索和變化成長四個階段。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組間對比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新訓前后評分的比較
新訓前實驗組與對照組間交往焦慮、應對方式、自尊、領悟社會支持相比較,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新訓后比新訓前的新兵交往焦慮得分降低、自尊水平升高,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1)。實驗組新訓后比新訓前的新兵交往焦慮得分亦降低、自尊水平、應對方式中積極應對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新訓后實驗組交往焦慮得分低于對照組(P<0.05),而應對方式中積極應對高于對照組(P<0.01)。見表1。
2.2 兩組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新訓前后差值的比較
將實驗組和對照組的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新訓前的得分減去新訓后的得分,得到新訓前后差值。實驗組中新兵的應對方式中積極應對提高大于對照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1)。實驗組中新兵交往焦慮、社會支持、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改善較對照組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自尊、應對方式中消極應對、其他支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 討論
社交焦慮是指對某一種或多種人際處境有強烈的憂慮、緊張不安或恐懼的情緒反應和回避行為。國外研究對社交焦慮的成因有多種理論,其中主要有社交技能缺乏模式和自我評價的認知模式。團體人際關系訓練可以通過社交技能的訓練和認知的改變,而改善社交焦慮。王冰等人的研究顯示交往焦慮與消極應對呈正相關與內外向、積極應對、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呈負相關[9]。為了有效地評估團體人際關系訓練對社交焦慮的干預效果,本研究從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等多方面來評估。
本研究結果表明干預前實驗組與對照組間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相比較,無明顯差異。干預后武警新兵的交往焦慮水平無論是實驗組還是對照組新訓前后都有了明顯的下降,但是實驗組下降幅度大于對照組,二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隨著新兵對部隊生活的適應以及同戰友的交往,他們交往焦慮的程度有明顯的下降。這是一個必然趨勢,這可以用Leary的社交焦慮自我展示理論來解釋,新兵來到部隊自我展示的動機過強反而會導致交往焦慮。團體心理輔導有助于促進交往焦慮狀況的改善。
在人際交往的沖突中和處理問題時,不同的人常習慣于不同的應對方式。積極應對者常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有效溝通、尋找解決途徑、尋求他人支持的方法,從而及時解決人際沖突和問題,避免交往焦慮。消極應對者常采取被動的等待、拖延、逃避、幻想等方式,因而使人際沖突和問題推遲或難于解決,導致交往焦慮。本研究表明對照組中應對方式新訓前后無明顯改變。新訓后實驗組的積極應對方式改善,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實驗組、對照組中消極應對方式新訓前后均無明顯改變。如何有效的改變交往焦慮新兵的消極應對方式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
表1 兩組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前后評分的比較(分,±s)

表1 兩組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前后評分的比較(分,±s)
注:與對照組新訓后比較,*P<0.05,**P<0.01
對照組(n=32)新訓前新訓后t 值 P值實驗組(n=32)新訓前新訓后t 值 P值54.03±4.37 47.63±7.45 4.20 0.00 54.00±3.78 42.66±10.02*6.00 0.00 21.69±2.87 28.56±3.45 8.66 0.00 21.65±2.88 28.84±3.70 8.60 0.00 16.69±2.58 16.69±2.12 0.00 1.00 15.68±2.65 17.00±3.26 1.76 0.08 15.72±3.22 15.562±2.862 0.21 0.84 14.90±2.75 16.06±2.92 1.63 0.11 14.63±3.09 14.34±2.91 0.38 0.71 13.75±2.33 14.84±2.52 1.81 0.08 47.03±7.41 46.59±5.96 0.26 0.80 44.39±6.74 47.91±7.77 1.92 0.06 1.17±0.54 1.05±0.52 0.92 0.36 1.40±0.56 1.24±0.67 1.02 0.31 1.58±0.585 1.43±0.47 1.08 0.28 1.51±0.50 1.79±0.56**2.15 0.035組別 交往焦慮 自尊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社會支持 消極應對 積極應對
表2 兩組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干預前后差值的比較(分,±s)

表2 兩組交往焦慮、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干預前后差值的比較(分,±s)
實驗組(n=32)對照組(n=32)t 值 P值11.34±10.45 6.40±7.24 0.06 0.042-7.26±3.71-6.88±3.85 0.42 0.690-1.32±2.80 0.00±2.13 2.12 0.038-1.16±2.48 0.16±2.02 2.32 0.023-1.09±2.83 0.28±2.95 1.90 0.062-3.58±6.87 0.44±5.05 2.65 0.010 0.16±0.83 0.12±0.52 0.21 0.840-0.29±0.66 0.14±0.45 0.35 0.003組別 交往焦慮 自尊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社會支持 消極應對 積極應對
對照組的領悟社會支持總分及各分量表分新訓前后無明顯改變。實驗組中新訓后新兵的領悟社會支持總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較新訓前改善,但是其他支持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領悟社會支持量表主要用于評估個體主觀上能夠感受到的社會支持程度。在本實驗組中,新兵現實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并沒有增加,但他們感受到的總社會支持、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提高了。其他支持包括了領導、親戚、同事的支持,而新兵入伍前幾乎沒有領導和同事的支持的體驗,因而其他支持前后變化無可比性。
交往焦慮狀況與自尊有密切關系,劉冉[10]的研究顯示自尊與社交焦慮存在顯著負相關。汪濤等[11]的研究顯示自尊是社交焦慮重要的預測因素。在本研究中,實驗組和對照組武警新兵新訓前后的自尊水平都有了明顯的升高,前后差異具有非常顯著統計學意義,但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培養自信心、提高自我評價本就是團體心理輔導的一個重要目標[12]。對照組自尊的提高的原因可能與新兵連本身就是一個同質的訓練團體有關。在新訓期間團體心理輔導不僅能夠有效降低新兵的交往焦慮而且能夠有效改善積極的應對方式、領悟社會支持和自尊。本研究由于持續時間相對較短,它對新兵的長期影響尚需進一步研究觀察。
[1]王偉,高平青,郭麗英,等.武警新兵交往焦慮狀況調查[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6,14(2):164-165.
[2]黃慧蘭,劉新民.團體人際心理干預與團體認知行為干預對社交焦慮的療效[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1,25(5):324-327.
[3]李丹.團體心理咨詢對提高醫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實證研究[J].右江民族醫學院學報,2010,32(2):260-262.
[4]楊茂鵬,袁維,張清媛,等.團體心理咨詢對醫學生心理適應能力評估的實驗研究[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0(4):46-48.
[5]旺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增訂版[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230-231.
[6]仝麗花,鄭曉邊.大學生人際關系團體心理輔導研究[J].中國學校衛生.2010,31(8):1019-1021.
[7]樊富珉.團體心理咨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5.
[8]鄧彩艷,段永.民辦高校大學生人際關系團體心理咨詢的效果研究[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2,20(3):472-475.
[9]王冰,才運江,王鑫龍,等.醫學生社交焦慮影響因素的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11,14(19):2213-2215.
[10]劉冉.大學生自尊與社交焦慮、人際信任的關系研究[J].淄博師專學報,2012,28(2):20-23.
[11]汪濤,譚靜,李敏,等.醫學生社交焦慮與自尊和人格特征的關系[J].第三軍醫大學學報,2009,31(11):1095-1097.
[12]李麗.大學生完美主義和自尊、懼怕否定的關系研究[J].中國醫學創新,2012,9(1):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