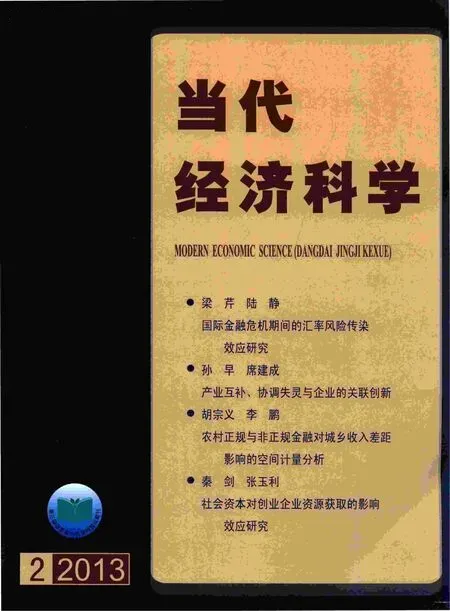中國是否存在住房泡沫的“避難所”
管 陵,葛 揚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江蘇南京 210093)
中國是否存在住房泡沫的“避難所”
管 陵,葛 揚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江蘇南京 210093)
本文從中國住房泡沫特征出發,構建“泡沫避難所”假說的理論框架,并在該框架中考慮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產生的影響。為檢驗該假說,本文利用動態面板模型對中國35個大中城市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1)中部城市具有“泡沫避難所”效應,即住房泡沫的增加使東部地區城市人口、人力資本、外來勞動力不斷向中部地區集中;(2)在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的增加造成東部地區城市人口規模的減少與人力資本流失的減緩,中、西部地區城市人口規模、人力資本與外來勞動力的增加。
住房泡沫;城市人口規模;人力資本;公共住房
一、引 言
自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房地產業投資規模逐年擴大,住房市場投機程度進一步加劇,部分城市出現了顯著的住房泡沫①呂江林認為,2006-2008年中國35個大中城市住房市場總體存在泡沫、部分城市泡沫較大,特別是部分一線城市泡沫驚人,蘊含巨大金融風險[1]。。由于住房市場發展關系到城市經濟結構與人口結構的優化,因此學術界對住房泡沫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格外關注。其中,“泡沫避難所”假說(“Bubbles Haven”Hypothesis)從城市經濟與社會福利角度較好地反映了住房泡沫變動與城市人口規模的負向關系,因而成為城市經濟學中的研究焦點。
“泡沫避難所”假說源于這樣一種現象。在發達城市,住房泡沫要比欠發達城市嚴重,對城市經濟與社會福利的負面影響也較大。此時,快速膨脹的住房泡沫會導致生活在發達城市的家庭根據城市經濟環境與福利現狀做出向欠發達城市遷移的決策,進而使得該城市人口規模逐漸減少。于是,與發達城市相比,欠發達城市可以憑借較低住房泡沫這種相對競爭優勢,吸引外來人口、積聚人力資本,并最終成為遷移人口的“避難所”。
圍繞這一假說,現有文獻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闡釋。一是基于住房泡沫的產業結構效應。管陵和葛揚認為,住房泡沫通過驅動資本增長率,調整產業間勞動力配置,間接使人口增長率隨資本增長率的增加而減少[2]。高波等人指出,城市間相對房價的升高會促使低端產業勞動力由房價較高的發達城市向房價較低的欠發達城市流動,誘發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3]。也就是說,大幅上漲的房價不僅有助于推動勞動力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升級,還可以優化城市區域間、產業間人力資本的配置。二是基于住房泡沫的財富效應。房地產業的高速發展在給地方政府帶來充足財政收入的同時,也促使政府加大城市公共產品投入力度,進而對人口流動產生正外部性效應。So et al.指出,由于公共交通設施的改善減少了城鄉通勤時間和流動成本,城鄉勞動力市場相同的工資增長率會鼓勵農村人口向城市積聚,而同比例增長的房價則會導致城市人口向農村流動[4]。三是住房政策在人口流動中所起的作用。Amundsen、Englund認為與住房市場相關的政策不僅對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潛在地改變著居民遷移行為[5-6]。Hardman 和 Ioannides采用住房市場代際交替模型分析了居民遷移與住房需求的關系,發現住房市場波動可以反映遷移的價格與頻率[7]。由于人口遷移過程伴隨著對住房存量的套利行為,所以較高套利成本和較低房價也決定了遷移成本。此時,政府可以通過對住房市場的干預來平滑人口流動。很明顯,“泡沫避難所”假說的內在邏輯錯綜復雜,而現有文獻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忽視了中國住房泡沫與西方發達國家住房泡沫的差異,沒有反映鮮明的中國特征;二是缺乏清晰的“泡沫避難所”假說理論框架;三是未考慮中國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在該假說中產生的影響;四是缺乏對“泡沫避難所”假說的實證檢驗。
為完善該假說,本文從中國住房泡沫特征出發,構建“泡沫避難所”假說的理論框架,并在該框架中考慮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產生的影響。同時,為檢驗該假說是否符合中國發展實際,我們利用動態面板模型對中國35個大中城市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的政策含義在于,政府在進行房地產政策調控的同時,應以人為本,充分考慮住房市場發展對城市人口規模、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外來勞動力造成的影響,并進一步探索可持續的公共住房保障機制,實現城市的包容性發展。
二、住房泡沫特征與“泡沫避難所”假說理論框架
(一)住房泡沫特征
什么是住房泡沫?它具有何種經濟特征?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相關解釋。對于泡沫的一般性而言,Kindleberger認為,泡沫是資產價格的特殊變化過程:最初表現為資產價格快速、持續上漲,并具有對未來價格進一步上漲預期;膨脹時期,泡沫可以吸引大量以獲取資產收益而并非使用資產為目的的投機者;泡沫破滅時,資產價格預期反轉,價格快速回落,資產市場交易萎縮,經濟衰退,最終造成金融危機[8]。而住房泡沫不僅具有泡沫的共性,還具有行業的特殊性。Arce和López-Salido考察了金融信貸約束在住房泡沫化過程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指出在過量貸款供給沖擊下,經濟會從資產低值穩態向高值穩態轉變,此時必定存在純泡沫(Pure Bubble),尤其是當住房投資的非套利條件得到滿足時,住房市場中存在的可貸資金的過量供給將產生靜態住房泡沫(Stationary Housing Bubble),其規模等同于投機性住房投資的總價值量[9]。就中國住房泡沫而言,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刻畫其特征。第一,消費者住房負擔加重。房價收入比不僅可以直接、準確的度量住房泡沫水平[1],還反映了消費者在自身預算約束下對房價的承受能力。當房價漲速超過消費者收入增速時,過高房價收入比意味著住房資產價格已與消費者實際購買力產生背離。此時,居住型消費者會被排斥在住房市場之外,而投資者則成為住房市場交易主體。第二,商品房投機性職能增強。當住房投資收益率超過市場平均收益率時,商品房將成為投資者的投資工具。房價的持續上漲不僅為投資者創造了獲取超額收益的理性預期,還在羊群效應的帶動下吸引更多投資者參與市場交易,助推住房泡沫膨脹。第三,地方政府對房地產業依賴性加大。房地產業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關系到地方財政收入總量。某些地方政府由于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方面缺乏實力,因而希望通過房地產業來帶動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增加。政府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和對土地財政的盲目追求造成了政府推動型住房泡沫。第四,住房泡沫受制于金融發展程度。寬松的金融信貸約束、普遍存在的金融摩擦、缺乏創新性的金融市場監管等,都會導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過度放大,推高實體經濟資產估值水平,進而加劇住房市場投機程度和潛在金融風險[2]。正是由于中國住房泡沫具有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復雜經濟特征,才使得其在城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和家庭遷移決策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調節著城市人口規模。
(二)“泡沫避難所”假說理論框架
“泡沫避難所”假說研究的是城市住房泡沫與適度人口規模之間的互動關系。這里的適度人口規模是指在最有利條件下達到最大經濟與社會福利的人口數量。簡單地說,由于住房為城市人口的生存與發展提供承載空間,這使得城市適度人口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住房市場滿足居住性需求的住房供給能力。而住房泡沫的動態演變過程通過扭曲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改變著住房市場供求關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福利損失,進而導致城市適度人口規模也隨之產生相應調整。在此期間,受泡沫影響的人口不僅包括擁有城市戶口的本地居民,還包括城市外來居民。因此,當城市間或城鄉間不存在嚴格人口流動障礙時,按照“泡沫避難所”假說的預測,隨著城市住房泡沫的增加,人們為了實現福利最大化,偏好于向住房泡沫較低的城市遷移,從而導致住房泡沫較高城市的適度人口規模逐漸減少。
理論上看,“泡沫避難所”假說包含三個基本假設。第一,各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的差異決定了其住房市場需求結構存在明顯不同。城市經濟增長取決于資金、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間的有效配置。當城市發展戰略引導過量資金進入房地產業后,資本市場上供大于求的資金會推動住房資產價格快速上漲,進而吸引更多投機性資金進入住房市場,放大投機性住房需求。第二,投機性住房需求在住房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住房泡沫與其他類型資產泡沫的區別在于,住房作為一種商品,除了具有投資價值以外,還具有滿足家庭居住性需求的使用價值。住房泡沫的形成意味著住房成為資本市場保值增值的投資工具,這勢必削弱其保障家庭居住的職能。投機性住房需求主導地位的確立不僅擠壓了滿足居住性需求的住房供給,還相應的增加了城市居住成本。第三,居住成本對人口自由流動有顯著影響。較高居住成本不但會減少外來人口的實際可支配收入,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生活,還會排斥城市內對居住成本較為敏感的中低收入人群,使他們更傾向于選擇具有較低生活成本的城市居住。
基于以上三個假設,我們可以厘清“泡沫避難所”假說的基本思路。
首先,住房泡沫會抑制城市居住性住房需求,壓縮城市人口生存空間,從總量上減少城市人口規模。假定存在一個發達城市和一個欠發達城市,發達城市在經濟增長率和投資收益率方面具有較大優勢,對欠發達城市的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有著強烈吸引力。隨著資金和勞動力的積聚,發達城市的經濟增長會進一步壯大住房市場發展規模。特別是資本推動型經濟增長,容易導致城市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當住房投資收益率超過社會平均收益率時,過量社會資金將涌入房地產業,加劇住房市場投機程度。隨著投機性住房需求在住房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住房泡沫出現。在此背景下,住房泡沫會從三個途徑減少城市人口規模。一是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勞動比的上升造成資本密集型產業繁榮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對萎縮。這不僅減少了城市勞動力市場需求,還減緩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二是居住性住房供給速度低于人口增長速度。這使得住房市場難以滿足城市人口的居住性需求,從而限制了人口規模擴張。三是住房泡沫引起的居住成本增長率超過了家庭收入增長率,即房價收入比增長速度過快。這會加重家庭撫養孩子的負擔,造成家庭在除住房以外的消費減少,降低家庭在發達城市生活的福利水平。因此,在同等條件下,家庭要么選擇降低凈撫養人口數或生育率,要么選擇能使家庭福利水平提高的城市居住。
其次,住房泡沫關系到經濟增長的質量與可持續性,會影響人力資本投資,長期來看不利于城市人力資本的積累。從房地產業非理性繁榮開始到住房泡沫破滅結束,整個周期不同程度地扭曲著資本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不僅導致全要素生產力(TFP)效率損失,還造成其他相對萎縮產業要素價格上升與升級成本增加,降低經濟增長的質量與可持續性。除此之外,經濟增長的質量還取決于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住房泡沫則分別從宏觀、產業、微觀層面阻礙城市人力資本積累。具體而言,一是由于住房與城市公共教育福利體系掛鉤,住房泡沫的增加會導致持有住房家庭與無住房家庭在享受公共教育投資方面存在明顯差別。長期來看,這種因住房所有權造成的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將減緩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人力資本的積累速度。二是住房泡沫在擠壓其他產業發展的同時,也減少了相關產業升級所必須的人才與技術需求,間接抑制了勞動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業對人力資本的有效投入。三是住房泡沫會產生不利于社會穩定發展的社會成本,比如由住房泡沫引起的通貨膨脹或是因房價上漲預期造成的金融動蕩。因為市場不具備控制與削弱泡沫的動機,所以城市居民必須自行承擔這種外部性成本。這無疑給想在城市生活卻無力購買住房的家庭增加了生存難度,壓制了這些家庭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投資支出,阻礙了家庭生活質量的提升與人力資本的積累。
第三,住房泡沫調節著勞動力流動規模與方向,并通過積聚住房泡沫風險來降低遷移者福利水平,形成針對城市外來人口流入的阻力。一般認為,城鄉收入差距和城市就業機會決定了城市人口流動的規模和方向。然而,從中國實際情況看,盡管房地產業具有較強產業帶動效應,可以增加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是包括居住成本在內的遷移成本和與住房綁定的戶籍限制政策不同程度地減少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生活的預期效用水平,抵消了其向城市遷移的動機。另外,隨著住房泡沫風險的積累,風險偏好型家庭對住房風險的主觀預期效用判斷在改變家庭正常消費行為的同時,還激勵其參與資產市場運作,促使其通過住房資產買賣來實現家庭投資行為最優化。這雖然可以起到防范家庭資產風險的作用,但卻增加了住房市場投機程度,加劇了住房價格波動和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這明顯不利于在該城市居住的風險厭惡型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而對于外來居民而言,不論是買房居住,還是租房,都必須額外購買住房泡沫這種風險產品。如果把“安居樂業”作為遷移者追求的效用函數,那么包含住房泡沫風險在內的住房均衡價格與均衡租金和勞動力市場的預期工資水平將直接減少遷移者的福利。因此,住房泡沫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原有居民和外來居民兩種不同類型居民群體福利水平的差異,從而降低了外來人口移居該城市的動機。這也意味著在不考慮城市管理者政策干預的情況下,住房市場、金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相互作用可以共同決定與住房泡沫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城市最優人口規模。
綜上所述,我們將其歸納為“泡沫避難所”假說一:住房泡沫的增加會導致發達地區城市人口規模減少、人力資本流失以及外來勞動力減少,但會促進欠發達地區城市人口增長、人力資本積累和外來勞動力增加。
(三)公共住房與“泡沫避難所”假說
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是由非商業化機構(政府或非盈利性社會機構等)主導、體現社會保障職能、采用非市場化方式運作、按特殊分配規則提供給特定人群居住的公共產品。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住房不僅是調節住房需求、完善住房供應結構、促進住房市場發展的一種手段[10],也是政府治理住房泡沫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面對著住房泡沫引起的社會問題,地方政府既有為中低收入階層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責任,也有化解住房泡沫風險、防范金融危機的義務。然而,公共住房與住房泡沫之間的復雜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泡沫避難所”假說。
一般認為,政府建設公共住房的目的是通過滿足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居住性需求,來抑制住房泡沫中的投機性住房需求,減緩住房市場投機氛圍,但是住房泡沫所具有的特性從多個層面抵消了公共住房保障性功能的發揮。一是當公共住房滿足市民居住性需求的速度遠遠落后于投機性住房需求增長速度時,投機性預期難以消除。尤其是當市民預期到公共住房供給與實際住房需求存在較大缺口時,無法享受公共住房的潛在需求者會被迫進入商品房市場。這將推動房價上揚,使住房投資者預期收益增加,從而加劇投機性行為。二是有限的城市建設用地在公共住房與商品房之間的配置會影響到住房泡沫膨脹程度。因為土地資源稀缺性是住房泡沫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所以公共住房過多占用城市建設用地不僅會突出土地資源稀缺性,抬高住房建設成本,還將造成商品房市場供給減少與均衡房價上升。三是地方政府在公共住房建設與財政收入之間存在激勵不相容,容易形成由政府失靈引起的住房泡沫。中國地方政府長期以來以財政收入作為政績考核的首要指標,而土地出讓金則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強行給住房市場降溫不僅會大幅減少地方財政收入,使地方政府面臨債務償還風險,還關系到地方主政官員的個人升遷。因此,這種利益沖突抑制了地方政府消除住房泡沫的動機。可以說,公共住房建設與住房泡沫的內在沖突強化了“泡沫避難所”假說的三個基本假設,導致城市公共住房建設不僅無法徹底消除住房泡沫,反而會在一定條件下使其繼續膨脹,并且按照住房泡沫原有影響路徑使發達城市人口向欠發達城市轉移。
在住房泡沫膨脹的同時,加大公共住房建設力度會進一步壓縮政府對教育、醫療以及產業創新的財政投入,長期來看不利于城市人力資本積累。尤其是對于欠發達地區,經濟上的落后不僅反映出創新要素的缺失與創新能力的不足,還暴露出其在人力資本投入方面存在著資金缺口。如果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于建設公共住房,那么城市短期內將無法積累產業升級所需的人力資本,長期則難以積聚創新要素。這無疑將影響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發達地區在財政收入總量方面要優于欠發達地區,可以憑借其較高金融發展程度,通過多種渠道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滿足城市公共住房建設資金需求。也就是說,由于發達地區具有獨特融資優勢,面對著相同程度住房泡沫,其進行同等規模公共住房建設所造成的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負向影響要弱于欠發達地區。因此,隨著住房泡沫的增加,城市住房保障體系的完善將有助于減緩發達地區人力資本下降,但會加速欠發達地區人力資本流失。
現有城市公共住房保障體系具有二元結構特征,即保障對象僅針對擁有城市戶籍的特定人群,不考慮外來人口住房需求。在此制度背景下,城市外來勞動力會遭受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與住房泡沫帶來的雙重負外部性影響。一方面,享受住房保障的中低收入家庭可以獲得政府給予的住房福利,在勞動力市場上形成與此相關的競爭優勢,使外來人口在就業方面處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政府在應對住房泡沫時采取的“限購”、“限貸”、“限戶口”等政策措施存在盲目排外的意圖。這無形中給外來人口在城市生活設置了重重障礙,增加了其居住成本,抑制了相應的居住需求。因此,外來人口在無法獲得住房保障情況下,要想長期在該城市生活,就必須考慮房價收入比或房租收入比是否在自身可承受范圍內。特別是在住房成本較高的發達城市,公共住房保障政策的執行力度一般要強于欠發達城市,其產生的負外部性影響也較大。這將導致外來人口的住房成本增長率要高于收入的增長率,從而激勵其向欠發達城市流動。
在此,我們獲得“泡沫避難所”假說二:在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的增加會造成發達地區城市人口規模與外來勞動力的減少,以及欠發達地區城市人口規模與外來勞動力的增加,但會減緩發達地區人力資本的下降和加速欠發達地區人力資本的流失。
三、計量理論模型
(一)模型設定
我們采用動態面板模型來驗證上述理論假說。該模型的優點在于,不僅考慮住房泡沫對本期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還重點關注內生被解釋變量滯后項對本期的影響,即城市人口變量在時間上的延續。模型具體設定如下:

式中,yit表示i城市t時期的人口變量,即城市人口總數、城市人力資本、城鎮外來勞動力這三個變量。yit-1用于捕獲城市人口變量的持續性,反映人口變動趨勢對人口變量均衡值的動態影響。主要解釋變量bubbleit為i城市t時期住房泡沫,我們分別用消費者住房負擔程度、投機程度、房地產業比重、房地產金融虛擬化水平來衡量該特征。系數ξ用于反映住房泡沫對人口變量的影響。Xit表示其他潛在影響因素,用于體現城市經濟與社會特征。μt為時間固定效應,δi為城市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本文在式(2)中加入公共住房保障政策(ZPHit)與住房泡沫的交互項。φ用于考察在宏觀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對城市人口變量的影響,并以此檢驗“泡沫避難所”假說二。
(二)估計方法
標準的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要求解釋變量與隨機誤差項之間不相關,即 Cov(bubbleit,εit)=Cov(Xit,εit)=0,但由于我們的模型涉及到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和人口變量對住房泡沫的反向因果關系,存在 Cov(yit-1,εit)≠0、Cov(bubbleit,εit)≠0 問題,所以會造成固定效應估計量有偏。同時,我們的動態模型還可能存在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聯立性問題,比如房地產業比重或金融虛擬化水平的變動會影響到人口規模的變動,但人口規模的變化同時也會決定著房地產業比重或金融虛擬化水平。因此,為了解決這些內生性問題和多重共線性問題,Arellano和Bond提出了差分廣義距估計(Difference GMM)方法,采用內生變量滯后項的差分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并假定隨機誤差項不存在自相關[11]。但當自回歸系數較高或面板效應的方差與隨機誤差項的方差比很高時,該方法會表現出不穩定。Blundell和Bond利用其他距條件推出系統廣義距估計(System GMM)估計量,并額外假定工具變量的一階差分與固定效應不相關[12]。該方法可以同時使用變量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信息,極大地提高了估計效率。以上兩種估計方法都具有一步估計和兩步估計。兩步估計的優點在于,可以基于第一步估計的殘差計算協方差矩陣,進行White異方差修正,但會低估標準差,降低估計效率。本文將同時采用差分GMM和系統GMM進行一步和兩步估計,并在差分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正交離差方程和水平方程提供的信息來加強估計效率。
(三)變量選擇和數據說明
本文重點研究中國35個大中城市①35個大中城市包括東部16個城市(北京、天津、石家莊、沈陽、大連、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福州、廈門、濟南、青島、廣州、深圳、海口),中部8個城市(太原、長春、哈爾濱、合肥、南昌、鄭州、武漢、長沙),西部11個城市(呼和浩特、南寧、重慶、成都、貴陽、昆明、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2002-2009年的數據。被解釋變量分別采用市轄區年末總人口數、人力資本水平、城鎮單位使用的農村勞動力來度量城市人口總數、城市人力資本、城鎮外來勞動力。由于住房泡沫主要出現在城市土地市場與房地產業較為發達的區域,而城市管轄的縣鄉在土地利用方面存在制度性障礙,難以形成有效的住房產權交易市場,因此本文將研究范圍縮小到城市轄區。城市人力資本由于沒有各市統計數據,本文采用各省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大專以上比例度量。城鎮外來勞動力用各省城鎮單位從農村招收的就業人員乘以市轄區總人口數占省總人口數的比重度量。
主要解釋變量包括:消費者住房負擔程度(AF)用房價收入比度量,投機程度(SP)用住房投資超額收益率度量,房地產業比重(HI)用住宅本年完成投資額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度量,房地產金融虛擬化水平(FL)用房地產資金來源中的國內貸款占住宅本年完成投資額比重度量。公共住房保障水平(ZPH)用經濟適用房本年完成投資額占住宅本年完成投資額比重度量,反映住房供給結構中政府發揮的作用。
其中,根據呂江林[1]的研究②呂江林[1]在計算房價收入比過程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采用全國水平戶均人口數作為各城市戶均人口數,與實際不符;二是2008年的住宅竣工套數數據缺失,是由2006年與2007年的算術平均值代替。以上兩個問題使計算結果與實際結果存在一定偏差。,本文的房價收入比計算公式為:
房價收入比=住宅平均單套價格/城鎮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住宅平均銷售價格×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家庭戶均人口數)。由于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無法準確獲得,本文用住宅平均單套竣工面積(即住宅竣工面積除以商品住宅套數)進行替代。通過計算,可以獲得2005-2009年住宅平均單套竣工面積,但2002年到2004年住宅竣工套數缺少統計數據,由于住宅竣工面積與住宅竣工套數高度相關,因此本文利用公式(本年住宅平均單套竣工面積=下一年住宅平均單套竣工面積×本年竣工面積/下一年竣工面積)來填補2002-2004年住宅平均單套竣工面積。由于各市城鎮家庭戶均人口數難以獲得,本文用各省城市平均家庭戶規模替代。
其他解釋變量還有,市轄區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市轄區人口自然增長率。以上變量2002-2009年數據均來自各年度《中國房地產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和中經網。除市轄區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外,對所有變量取對數形式。
四、計量結果分析
(一)住房泡沫對城市人口變量的影響
表1給出的估計結果都通過二階序列相關檢驗和Hansen過度識別檢驗。除第(8)列外,其余列人口變量滯后項高度顯著。這表明人口變量具有持久性和延續性。具體而言,住房泡沫對不同地區城市人口總數的影響存在差異。在東部地區,投機程度對人口增長率的負向效應明顯大于消費者住房負擔的正向效應。在中部地區,由于其住房金融發展程度在廣度和深度上遠不如東部地區發達,因而虛擬化程度的提高會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對于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消費者住房負擔每增加1%,會使人口增長率減少0.03%,而房地產業比重每增加1%,卻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促進人口增長率增加0.03%。
住房泡沫對不同地區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也具有差異。在中部地區,住房泡沫促進了當地人力資本的積累,其中投機程度起正向主導作用。而在東部地區,盡管金融虛擬化程度的提高對中高端人才有吸引作用,但住房市場的過度投機卻抑制了該作用的發揮,整體上加速了人力資本的流失。同樣,西部地區也存在著類似的中高端人才外流。
對于城鎮外來勞動力而言,由房地產業比重增加引起的產業結構變動對所有地區都有顯著的負向效應。這表明住房泡沫會導致資本密集型產業上升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下降,從而抑制了中低端勞動力向城市流入。但金融虛擬化水平對所有地區都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中低端勞動力收入水平較低、住房金融參與程度不高所致。另外,住房市場中投機因素所發揮的作用使中部地區外來勞動力增長較快,而西部地區則進一步萎縮。
總之,中部城市具有明顯的“泡沫避難所”效應,即住房泡沫的增加使東部地區城市人口、人力資本、外來勞動力不斷向中部地區集中。這反映出房地產金融的深化與住房市場體系的完善不僅為中部地區產業升級創造了條件,也為人力資本積累與人口流動提供契機。同時,這也意味著中部地區正利用較低住房泡沫這一相對競爭優勢,加快實施“中部崛起”經濟發展戰略、推動產業從東部向中部的梯次轉移。因此,“泡沫避難所”假說一符合中國東、中部地區發展的實際。
(二)在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對城市人口變量的影響

表1 住房泡沫對城市人口變量的影響
加入保障政策與住房泡沫的交互項后,表2估計的結果相對于表1發生了較大變化。具體而言,保障政策有助于促進中、西部地區城市人口的增長。其中,房地產業比重發揮的正向效應最為明顯。這表明公共住房投資的加大,不僅可以帶動房地產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增加城市就業機會,還可以抑制住房泡沫的膨脹,減緩消費者住房負擔。這對住房市場自身的健康發展和住房資源與城市人口的協調發展意義重大。然而,保障政策并沒有有效阻止東部地區人口增長率的減少,反而在投機因素的刺激下,加劇了住房泡沫對城市人口的負向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保障政策具有二元結構特征,無法使非戶籍人口的住房有效需求得到合理滿足。另一方面,有限的土地資源在向公共住房政策傾斜的同時,會進一步加劇城市土地資源的稀缺性,減少市場上商品住房供給量,從而造成土地市場結構扭曲和商品住房市場均衡價格上漲。這也為投機性住房泡沫的膨脹創造了條件。另外,東部地區投機性住房泡沫與保障政策的交互項存在臨界點——經濟適用房投資占住宅投資比重為 1.23%(e-0.44/0.1),即當政府保障政策超過該臨界點后,投機性住房泡沫對城市人口增長率的負向效應便會逐步減緩,反之,則進一步加深。

表2 在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對城市人口變量的影響
在保障政策背景下,房地產業比重變動對東部地區的人力資本具有負向效應,但由于東部地區具有較高的金融虛擬化水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人力資本下降。特別是當保障政策超過臨界點(6.9%)后,東部地區房地產業比重對人力資本的負向影響會隨保障政策力度的加大而逐步減弱。與此相反,住房泡沫對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積累存在加速作用。在中部地區,保障政策不僅減輕了中高端人才的住房負擔,還通過房地產投資結構的調整帶動了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集聚。而西部地區則在投機性資金的驅動下,不斷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并且當保障政策超過臨界點(5.13%)后,投機性住房泡沫對人力資本的正向效應會隨保障政策力度的加大而進一步增強。
由于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很少考慮外來勞動者的權益,所以外來的中低端勞動力更容易遭受住房泡沫與保障政策疊加所形成的外部性影響。盡管東部地區住房泡沫變量對外來勞動力的估計結果全都不顯著,但中部和西部地區的保障政策卻為中低端外來勞動力創造了轉移的“避難所”,產生了住房泡沫的正外部性效應。尤其是當中部地區保障政策分別突破臨界點0.123%、2.26%、8.5%之后,該地區消費者住房負擔、投機程度和金融虛擬化水平對外來勞動力的吸引力度將逐步疊加,不斷增強。
總體而言,在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除了對外來勞動力影響不顯著外,其余的計量結果與假說二基本一致;而作為欠發達的中部和西部地區,住房泡沫加快了該地區城市人口總數的增長、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外來勞動力的吸收。這與假說二的前半部分一致,但與其后半部分相矛盾。因此,“泡沫避難所”假說二并不完全符合中國實際。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分析住房泡沫與城市人口規模的關系,構建了“泡沫避難所”假說的理論框架,并在該框架中考慮城市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產生的影響。為驗證該假說,我們利用動態面板模型對2002-2009年中國35個大中城市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1)中部城市具有“泡沫避難所”效應,即住房泡沫的增加使東部地區城市人口、人力資本、外來勞動力不斷向中部地區集中,這基本符合“泡沫避難所”假說一。(2)在二元公共住房保障政策背景下,住房泡沫的增加造成東部地區城市人口規模的減少與人力資本流失的減緩,中、西部地區城市人口規模、人力資本與外來勞動力的增加,這不完全符合“泡沫避難所”假說二。
本文的研究對城市發展有重要啟示意義。城市作為創造財富的經濟體,應盡最大可能消除由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引起的投機性泡沫、金融摩擦與人口流動障礙,并充分利用住房市場、金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三者間的動態平衡關系,來擴展城市可承載空間、提高金融效率、加快人力資本保值增殖;同時,城市作為謀求人類福祉的載體,要努力實現城市公共福利體系的同步增進與包容性發展,即以人為本,用開放、平等、可持續的姿態,建立可持續的公共住房保障機制,變革由戶籍制度造成的二元福利體制,進而確保每一個市民享有均等的發展機會、獲得公平的發展成果。
[1]呂江林.我國城市住房市場泡沫水平的度量[J].經濟研究,2010(6):28-41.
[2]管陵,葛揚.住房泡沫與城市人口增長[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2(12):42-50.
[3]高波,陳健,鄒琳華.區域房價差異、勞動力流動與產業升級[J].經濟研究,2012(1):66-79.
[4]So K S,Orazem P F,Otto D M.The effects of housing prices,wages,and commuting time on joint residential and job location choices[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83(4):1036 -1048.
[5]Amundsen E S.Moving costs and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tra- urban mobility[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85,15(4):573 -583.
[6]Englund P.Taxation of capital gains on owner-occupied homes:Accrual vs realiz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85,27(3):311-334.
[7]Hardman A M,Ioannides Y M.Moving behavior and the housing market[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5,25(1):21-39.
[8]Kindleberger C P.Bubbles in history[EB/OL].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B000212,2011-10-1.
[9]Arce ?,López - Salido D.Housing bubbles[J].Macroeconomics,2011,3(1):212 -241.
[10]李克強.大規模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逐步完善住房政策和供應體系[J].求是,2011(8):3-8.
[11]Arellano M,Bond S.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277-297.
[12]Blundell R,Bond 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 -143.
Does China Have Housing Bubble“Haven”?
GUAN Ling,GE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Bubble Haven”Hypothesis(BHH)on the ba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housing bubble in China and analyses the impacts resulting from dualistic security policy of urban public housing in the framework.To verify the BHH,this paper conducts positive analysis to the data of 35 large-and middle-sized cities in China by using the dynamic panel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central cities have the effect of the“bubbles haven”,namely,an increase in housing bubble leads to the flow of urban population,human capital and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from the eastern cities to the western areas;(2)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istic security policy of public housing,an increase in housing bubble reduces urban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loss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astern cities and boosts urban population,human capital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Housing Bubble;Urban Population Size;Human Capital;Public Housing
A
1002-2848-2013(02)-0079-09
2012-11-21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房地產市場行為金融特征及其預期彈性管理機制研究”(12CJL018)。
管陵(1982-),江蘇省南京市人,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房地產經濟學;葛揚(1962-),江蘇省海安市人,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房地產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責任編輯、校對:李斌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