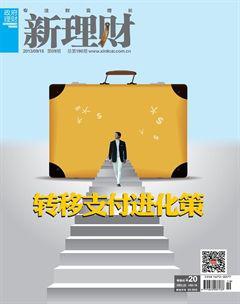從財稅體制看地方債務危機
方紹偉

中國是一個“集權型單一制”國家,不是一個“分權型單一制”國家,也不是一個“聯邦型復合制”或“邦聯型復合制”國家。這個簡單的政治事實,決定了中國的財稅體制不可能是“分權式”或“聯邦式”的。
可以說,“中央集權”、“分級代理”、“分稅限權”、“轉移支付”、“稅費最大化”、“預算軟約束”和“中央終極責任”是當代中國“財政集權體制”的七大基本特征。由于這些特征不完全符合“財政聯邦制”的一系列原則,故中國的“財政集權體制”也被稱為“財政準聯邦制”。本文將從從中國財稅體制的特征,分析地方債務危機的政治經濟邏輯。
財稅體制的內在困境
分析問題的第一步是看“宏觀稅負”,即稅收占GDP的情況。如果把各級政府在正式稅種之外的其他各項稅費加進去,中國的“宏觀稅負”會比這個比例高出很多。這個“隱性宏觀稅負”是個不可忽略的大問題。
分析問題的第二步是看“中央收入比”,即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從1990年到1993年,“中央收入比”從50%下降到35%,1994年因分稅制改革而上升為67%,此后逐步下降到50%左右。“中央支出比”的情況也類似。現在的問題是,全國總的稅收在增加,中央的收入總額也在增加,可中央除了國防保安、外交行政、文體交通、教育科研等支出外,其他的錢都到哪去了?這就是爭議較大的中央給地方的補貼或“轉移支付”問題。
轉移支付之所以爭議大,要害在于“地區平衡的再分配原則”往往被“討價還價機制”和“跑部錢進機制”所取代,結果轉移支付本身不僅變得毫無原則,還起到了“鞭打快牛”和“激勵腐敗”的負效應。轉移支付中的一般支付和專項支付往往各占一半,專項支付的審批權掌握在中央各個部委手中,各地的“駐京辦”就擔負起了爭搶專款的“跑部錢進”任務。好好的稅錢,有很大的比例就燒在了“扯皮”、“尋租”和“回扣”上。大稅種如增值稅和所得稅的大頭都讓中央拿走了,地方還哪來的錢去辦那么多的事?“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標還如何可能持續實現?地方的積極性還能往哪調動?按照“財政聯邦制”的“對等原則”,稅收從哪來用到哪去效率最高,但如果中央財權太大、“地區平衡的再分配原則”太靈活,就會出現地方政府“從看納稅人的臉色變成看中央的臉色辦事”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的“財政集權體制”甚至不能叫“財政準聯邦制”,“分稅限權”取代了“分稅分權”,所以它似乎只能叫“財政偽聯邦制”。
80%的中央收入用于轉移支付,確實表明中央的財權太集中了。這也意味著說,看一個國家的財政分權程度,根本不能只看地方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中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也要看。大部分錢可能最后是地方在花,可其中很大的比例,需要地方從中央的控制權上“哭鬧出來”(轉移支付統計上算中央支出)。同樣重要的是,既然從中央那“哭鬧出來”的是錢而不是中央的稅權,地方還不夠花的話,也就只能從中央那“哭鬧出來”非正式稅種之外的其他稅權和債權。
這就到了分析問題的第三步:既然中央搞“財權最大化”,包括被鞭打快牛的各省區就只好搞“稅費最大化”,這可以被稱為中國特色的“地方隱性財權定律”:一旦“法定財力”無法應付日益增加的“事權責任”,“法定財權”就必然尋求突破自己而獲得非正式的“隱性財權”(包括“隱性稅權”和“隱性債權”),以解決“法定財力”與“事權責任”的不對稱困境。
地方“隱性稅權”
在理解地方“隱性稅權”和“隱性債權”的問題上,中國“財政集權體制”的“分級代理”、“稅費最大化”、“預算軟約束”和“中央終極責任”這四個特征尤其重要。簡單地說,地方及地方部門要在盡可能保證自己福利(包括政績和升遷)的情況下辦好代理的事務,而保證自己福利的兩大辦法是“部門最大化”和“責任代際化”,“稅費最大化”和“債務遠期化”就是這兩個辦法的財政體現。
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一直包括預算內、預算外、非預算三大部分。2011 年起,預算外收入(教育收費除外)納入預算管理,因此,2011 年財政統計中的非稅收入規模開始增大。非稅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對政府收入進行的分類;預算外資金則是按照“資金管理方式”進行的分類。非稅收入概念在2003年明確后,預算外概念逐漸淡化。目前,非稅收入的主體還是預算外資金,非稅收入已經被逐步納入預算內管理。
在改革過程中,還存在大量的既非預算內也非預算外、并且未納入“非稅收入”的“制度外收入”或“非預算收入”。不少省市的非稅收入在一般預算收入的占比高達30%以上,加上非預算部分則可能超過50%。非預算收入具有非規范性、隨機性、低透明性,是轉軌過程中逐步擴張的“小金庫”。
非預算收入主要由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直接支配,既可能被用于經濟建設,也可能被用于事業發展、社會保障和公職人員的津貼。其中,無償的非預算收入是指政府部門以及依托政府的社會團體,憑借自己特定的權威向社會募集的臨時性收入。有償的非預算收入是指政府部門直接運作或委托企業運作、并以政府名義向社會各界的借入資金。有償的非預算收入實質上是政府信用資金,中國的地方政府無權發放債券,但這種收入本質上是地方公債。
地方“隱性債權”
不理解中國地方財政的政治邏輯,就不可能理解當代中國經濟的發展邏輯。而由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門只是中央的代理,“稅費最大化”和“債務遠期化”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必然結果。
按照1994年出臺的《預算法》,中國的地方政府無權發行債券。“正式債權”沒有,“隱性債權”卻普遍存在的。地方的“隱性債權”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是向中央“哭鬧出來”的由財政部代理發行的地方債(列入省級預算管理) 。
第二是所謂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即地方政府組建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城投公司)、城建開發公司或城建資產經營公司,這些公司通過地方政府劃撥的土地、股權等資產,加上財政擔保、補貼等還款承諾,建成了資產和現金流達到銀行、承銷券商或理財產品融資標準的公司,然后將融資款項用于市政公用事業等項目中。城投債券或市政債券一般都需要上報省發改委、國家發改委審批。在監管收緊時,不少地方通過信托貸款、融資租賃、售后回租、墊資施工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
“地方政府公司化”導致出現超前的基礎設施投資或加劇產能過剩的投資。到2013年3月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9.59萬億元。地方投融資平臺推進的各種項目普遍資本金不足、回收期長、收益率低,出具虛假注冊資金證明、以流動資金或搭橋貸款充作資本金、高估實物出資、以貸款抽回資本金、政府擔保過多、虛假抵押、以新債還舊債等“飲鳩止渴”現象普遍存在。
第三是地方企業發放的債務、地方政府補助事業單位所借的債務。這三個方面意味著地方的債務包括:負有償還責任的直接債務,負有擔保責任或連帶償還責任的間接債務,負有沒提供擔保、但承擔救助責任的其他債務。
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債務最終將以稅費的形式落到地方老百姓的頭上。現行稅制表面上是對地方政府不利,實際上卻是對納稅者不利。問題不在于地方政府要分清該不該干什么,問題在于制度邏輯規定了地方政府必然干什么。地方政府“代理權”的邏輯,使地方政府經常埋怨中央“要讓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是,代理中的“財力不對稱”、“責任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決定了地方政府把治理任務和經濟發展往“財務困境”甚至“債務危機”上滑行。
分析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不能簡單的運用“自中央而下”,或者“自百姓而上”,或者“從地方政府看上下”的思維,必須確立的是一種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百姓與地方或中央之間的“多重博弈”的思維。現有體制下的地方債務危機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行為能力,地方債務危機必然因此轉化為中央稅制危機、高房價危機、民生支出危機、環境污染危機甚至社會公德危機。
(作者系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