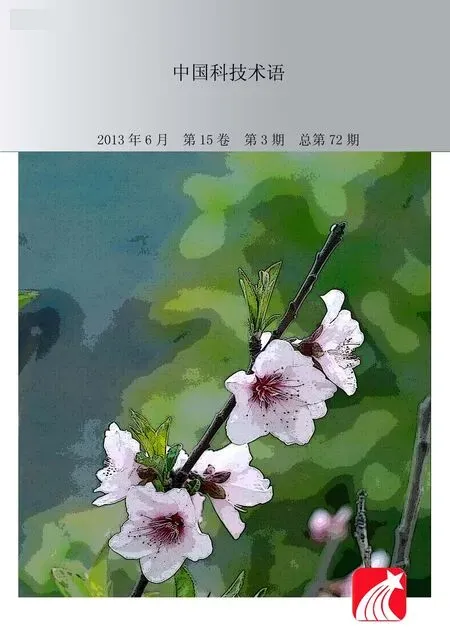“媒介”概念的演變
梁之磊 孟慶春
(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北京 102600)
一 “媒介”詞源分析

以上是“媒”和“介”各自的詞源追溯,那么作為一個詞組使用的“媒介”始于什么時候,又是有何種含義呢?目前出版的傳播學基礎理論圖書,對“媒介”進行概念界定時,很多都只是直接引用了西方的現代定義,對其漢語詞源談及很少。雖然“媒介”從字面理解看似簡單,但是從字面上的理解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它在漢語中意義變遷的復雜歷程。所以,考究“媒介”的詞源非常有必要。
筆者通過檢索發現,西晉學者杜預(222—285)在注解《左傳·桓公三年》“會于嬴,成昏于齊也”時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1]就目前查閱的古籍而言,這是“媒介”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最早出處。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媒介”一詞最早出自五代劉徇(887—946)編撰的《舊唐書·張行成傳》:“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此處所提的“媒介”則是推舉人、介紹人的意思。而在此之前,除杜預提到“媒介”外,東晉常璩在《華陽國志》中有“和養姑守義,蜀郡何玉因媒介求之”的用法,這說明在唐代以前“媒介”就已經是一個固定搭配了。
二 “媒介”詞義的演變
從杜預的兩句話中可以看出,杜預認為:魯桓公沒有通過媒人而直接與齊僖公會見并訂下婚約,這是不符合正統禮儀的。在第二段話中,杜預對“言己”解釋到:讓人推薦自己,就要通過“介”來實現,這個“介”就是“媒介”(引薦人),也就是(能夠被推薦的)原因。“媒介”最早的詞義就是介紹婚姻對象的媒人和為上層介紹人才的引薦者,也是其從西晉一直延續到晚清的兩種最主要詞義。
作為媒人、引薦者的“媒介”詞義,在此后歷朝的文獻中多次出現過,可見該詞義在歷史上是貫穿始終的。從文化角度看,這體現出“媒介”在中國傳統婚姻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古代中國人的人際傳播的方式。
到晚清,“媒介”概念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詞性上由原來單純的名詞變為名詞或者動詞,“媒介”從原來的“媒人”“引薦者”釋義擴展為“其他起聯絡和介紹作用的人”;二是指代對象上的變化,由“人”的范疇延伸到“物”的范疇,指代那些起介紹、聯系作用的物。至此,“媒介”的意義變化接近了現代的意義,即人們用來傳遞、交流信息的工具。清代黃遵憲撰寫的《日本國志》中寫道:“關家資分散之罪家資分散之際,有藏匿脫漏其財產,……或為其媒介者,減一等。”此處“媒介”的詞性由名詞變成了動詞,詞義也由傳統的“媒人、引薦者”變成了“介紹、聯系”。這一用法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媒介的行為主體與對象都變成了“物”,其詞義也拓展為實在之物(而非人際關系)的交流傳遞,這種新用法對于“媒介”的意義變遷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只有當“媒介”概念從人際傳播的范疇中解放出來,它才有可能向更豐富的所指和更高層次的抽象發展,進而演變為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媒介概念。
在民國的雜志上,“媒介”繼承和創新了之前的用法,用“媒介”指代“媒人、引薦者”的用法依然存在,另一些文章中所使用的“媒介”概念則越來越接近其現代詞義,例如,“舊書為傳染病之媒介”“昆蟲為傳布種子之媒介”,將“媒介”視為一種起到連接、傳播作用或使雙方發生關系的事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紙——文化的媒介》一文,里面寫道:“紙,文化的媒介,精神的食糧,這大家都同意了。”即將紙張視為可以承載和傳播文化信息的媒介,已經完全屬于傳播學對于“媒介”的認識范疇了。
三 “媒介”的當代釋義
英語中的“媒介”一詞(medium),大約在20 世紀30年代開始應用,其主要含義指使事物之間發生關系的中介體、手段、工具等。日常生活中,“媒介”又有不同的指代對象,可以是物理意義的“介質”,也可以是文化現象,如漢字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媒介。媒介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就用“泛媒介”的概念來解釋這種現象,他認為人類任何技術進步、任何工具的發展都是媒介的發展,都是人體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石斧是手的延伸,車是腳的延伸,電話是聲音和耳朵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耳朵的延伸,電視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總之,人與周圍環境發生關系,必定通過媒介。約翰·費斯克等編撰的《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中定義媒介:一般來說,媒介是一種能使傳播活動得以發生的中介性公共機構。具體說,媒介就是拓展傳播渠道、擴大傳播范圍或提高傳播速度的一項科技發展。廣義上講說話、寫作、姿態、表情、服飾、表演等,都可以被視為傳播媒介。每一種媒介都能通過一條信道或各種信道傳送符碼。這一術語的這種用法正在淡化,如今它越來越被定義為技術性媒介,特別是大眾媒介。有時它用來指傳播方式,但更常用于指涉使這些方式成為現實的技術形式,如報紙、收音機、電視、書籍、照片等[2]。
國內學者也對“媒介”概念有不同的界定。李勇、李嬌在《“媒介”考辯》中闡釋“媒介”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他們認為從廣義的角度看,媒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事物之間發生、確立關系的中介,而媒介充當的中介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工具,二是介質、媒質。他們認為狹義的“媒介”是指建構人與人信息溝通關系的介質,主要有三種形態:一是作為傳播工具的人,如媒人;二是作為傳播工具的物,如烽火、軍號;三是技術性傳播工具,如報紙、廣播。
楊鵬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理解媒介,“傳播媒介處于信息傳送者(簡稱傳者)和信息接受者(簡稱受者)之間,是用以承載、運輸信息的工具,如信函、報刊、電話、電視等。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是為信息傳播服務而存在的,首先必須有信息的產生、有傳播的需求,然后才談得上媒介的選擇和使用。”[3]他在《厘清“媒介”概念 規范學術用語》中認為我們現在說的“媒介”其實是狹義的媒介概念,即大眾傳播媒介,在現代社會中最常用的義項特指書籍、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等。并且,他還從三個不同角度分析了大眾傳播媒介的概念。其一,比較狹義的意思是僅指傳播的渠道工具,即具體的電視播出設備、報紙的物質形態等。其二,指媒介機構,尤其特指人員組織。其三,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傳播機構和傳播渠道工具的總和,更多的是指傳播者,又包含了傳播渠道工具[3]。
參照約翰·費斯克的定義,雷建軍把媒介指涉為傳播方式的技術實現形式,其主要形態有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話、手機與電腦等[4]。
李瑋、謝娟在《“媒介”、“媒體”及其延伸概念的辨析與規范》中說,由于“媒介”所代表的對象是客觀的,獨立的,因而大眾傳播學視野下的“媒介”之內涵,一方面可指傳遞信息的手段、方式,如語言、文字、聲音、圖像等,另一方面可指傳遞信息的載體和樣式,如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互聯網絡、手機等載體,以及博客、QQ 等樣式[5]。
從以上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學者對“媒介”概念的界定都帶有時代、知識背景等印記,參考古代社會對“媒介”的解釋,古代的“媒介”具有一定的傳播學意義,雖然還沒有真正演變到現在的傳播學中的“媒介”定義,但卻都有連接、交流的含義,都突出強調了媒介的功能性,結合目前學者普遍對“媒介”的定義,從功能上進行界定比較算是一個公認的闡釋。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邵培仁教授認為:媒介,就是指“介于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的用以負載、傳遞、延伸特定符號和信息的物質實體”[6]。它包括書籍、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及其生產、傳播機構。
四 結語
對于“媒介”概念的理解,反映出人們對其認識的不斷變化,內涵上從起介紹作用的人到傳遞信息的人、物或者介質,外延上從指代人到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甚至是虛擬的網絡。這也反映了人類的傳播活動越來越豐富和頻繁,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
隨著歷史文化的發展,因詞語的多義性,“媒介”所指涉的對象在不斷地變化、擴展,為了能對“媒介”有更直觀、深入的理解,我們不得不從某個角度對“媒介”進行界定,而它的外延是不斷變化的,只有在把握“媒介”內涵的基礎上才能對外延有更深入的了解。
[1]杜預.春秋左傳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79.
[2]約翰·費斯克.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161.
[3]楊鵬.厘清“媒介”概念 規范學術用語——兼及“媒體”“新聞媒介”等概念的辨析[J].當代傳播,2001(2):18-20.
[4]雷建軍.軟化的“媒介”——整合過程中的媒介內涵演變[J].現代傳播,2007(1):54-56.
[5]李瑋,謝娟.“媒介”、“媒體”及其延伸概念的辨析與規范[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11(24):694-699.
[6]邵培仁.傳播學導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