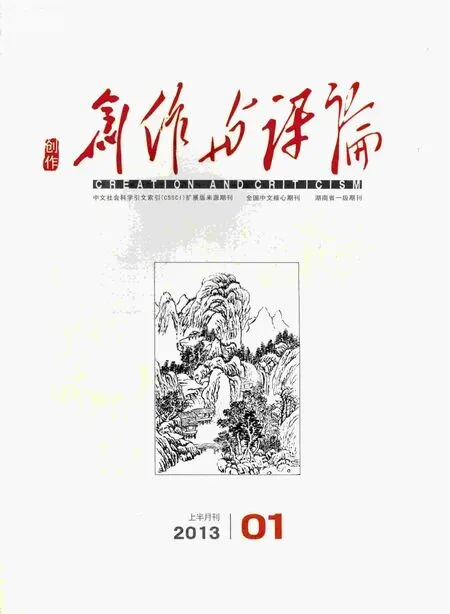小說三題(中篇小說)
○ 姜貽斌

大妹的鞋墊
大妹是想過我的。
大妹是隊長的大女。
隊長有高高矮矮四個女。
我插隊住在隊長的樓上,大妹常來樓上玩耍,這是自然不過的,不必擔心有什么閑言碎語。她每回來樓上,總是一個人來,從不帶妹妹們上樓。一上來就笑著說,小姜哎,你屋里像個牛欄屋哎。說罷,拿掃帚掃地,或是拿抹布這里抹抹,那里擦擦,好像她住在這樓上似的。有時候,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隊里的人都叫我老姜,包括隊長。
只有大妹叫我小姜,她說,哎呀,叫老姜難聽死了,十六七歲人,哪里就老了呢?
我也不清楚是從哪天開始的,大妹對我就有點那個意思了。平心而論,大妹對我的關心是無微不至的。除了打掃屋子,我每次換下的衣服,她就悄悄地拿去洗掉了。曬干之后,又疊得整整齊齊地送來,十分醒目地擺放在床鋪中央。
我的樓房從來不鎖門的,所以,她進進出出很方便。
我這個人沒有什么優點,弱點卻很多,尤其是沒有幾斤狗力氣,吃不得大苦,受不得大累。如果去河邊的船上挑肥料,大妹自己挑一程,然后,又返回來幫我挑,她幾乎是同時挑兩擔,工分卻記在我的賬上。望著她滿身大汗,我很不好意思,有時拒絕她幫我挑,我說我慢慢挑就是了。大妹搶過我手中的扁擔,直爽地說,你又挑不起,充什么卵狠呢?我來我來。挑起擔子,匆匆地走。望著她的背影,我不由涌起一陣感動。總而言之,她好像是我的保護神,不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勞動中,處處都幫著我,惟恐我吃不消。另外,我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最害怕螞蝗了,如果腿上沾一條肉肉的棕色螞蝗,我居然嚇得抖抖地指著腿上,戰戰兢兢地說,大妹,快來。大妹一看,急忙彎下腰,一邊說不要怕,一邊將螞蝗小心地從我腿上扯掉,扔得遠遠的,咬牙切齒地罵道,你這個該死的。
若是雙搶季節,大妹去山上采金銀花熬茶,然后,不厭其煩地將茶水送上樓來,灌入我的茶壺。我喜歡喝金銀花茶,涼沁沁的,我從來沒有發現過茶壺是空著的。大妹還不時地叮囑說,小姜,你要多喝茶嘞,鬼天氣也太熱了,容易發痧,茶水是解熱的嘞。也多虧了大妹,雙搶大忙,在火爐般的天氣里勞動,我居然一次痧也沒有發過。
有一回,隊長叫我和大妹去縣城買農藥。平時,去縣城買農藥派一個人就行了,隊長這次卻派兩個。當時,我還不明白為什么要派兩個,這不是浪費勞動力嗎?走到半路上,看著走在前面的大妹,我才忽然明白,哦,這是隊長故意安排的吧?他在利用手中小小的權力,為大妹和我制造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吧?
那天,大妹興奮極了,挑著空籮筐,一路上滔滔不絕,忽而說小姜嘞,你看那座山像不像個菩薩?忽而說小姜嘞,你看那條河像不像一條腰帶?忽而說小姜嘞,你看那片彩霞像不像一匹馬?忽而說小姜嘞,那一丘田像不像個斗笠?
她嘰嘰呱呱地說個不停,說實話,我心里并不是那么高興的,又不愿意讓她掃興,就附和道,像,像,像,像。
到了縣城,她并不急于買農藥,叫我帶著她到處看看。對于這個縣城,我簡直太熟悉了,我的家就在縣城。縣城其實很小,在大妹的眼里卻很大,簡直大得不可思議。為了滿足她的心愿,我帶著她去商店啦,電影院啦,造紙廠啦,磷肥廠啦。等等。其實,除了商店,其它的地方我們也沒有進去看,只是站在大門口看看而已。大妹呢,卻不時地發出驚嘆,哎呀,這么多的人呀?哎呀,廠子這么大呀?哎呀,商店這么多東西呀?
大妹就是這樣一路驚嘆,讓我感到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如果讓熟人碰見,肯定會嘲笑這個妹子也太鄉巴佬了。
幸虧沒有碰上熟人。
走走停停,看過一些地方之后,我以為也差不多了。大妹似乎仍不滿足,好像要把縣城的角角落落看個遍,過一回足癮。她不斷地轉過臉問我,反正時間還早,是不是還去哪里看看吧?
這時,我有些不耐煩了,看過這么多的地方可以了。所以,我覺得大妹今天格外纏人,難道要把縣城的每一寸地方都看到嗎?當然,我臉上沒有流露出來,擔心刺傷她的自尊心,所以,我漫不經心地敷衍說,哎呀,這個縣城太小,沒有什么地方好看的了。
她不相信,驚訝地說,難道沒有地方好看了嗎?難道就沒有了嗎?你再想想看?她張大眼睛望著我,提醒我。
我抓抓頭發,裝著絞盡腦汁的樣子,然后,很無奈地說,真的,我實在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好看的了。
大妹一聽,情緒顯得有些沮喪,不再說話了,極度的興奮似乎猛地降到了冰點。
她憂郁地說,那……那我們去……買農藥吧。
我帶著她大步地朝農資商店走去,剛走到農資商店大門口,她竟然又轉過臉問,小姜嘞,你再想想看,如果實在是沒有什么地方好看了,我們就買農藥好不?
我毫不猶豫地說,買吧,然后,回隊里吧,還有幾十里路呢。
大妹直直地望著我,好像一眼要將我的心臟穿透。她的嘴唇顫動著,欲言又止,似乎又不心甘,猶豫一下,最終還是說了出來,你……你難道不回家看看嗎?
我一怔,恍然大悟。
哦,大妹其實一直在暗示我,其目的是要去我家看看。而我根本沒有這個想法,我不想帶她去我家,即使我的父母沒有意見,那些街坊也會有看法的,他們一定會嘲笑我,說我帶一個鄉下妹子來了。再者,我也不能讓大妹去我家,這很容易讓她想入非非,以為我對她的態度很明朗了。
我腦殼一轉,趕緊撒個謊,說,哎呀,我爺娘上班去了,屋里沒有人,再說,我也沒有鑰匙,進不去。
大妹疑疑地看我一眼,徹底失望了,眼神暗淡,二話沒說,默默地走進農資商店,買了農藥,挑著擔子往回走。
在回去的路上,大妹不要我挑農藥,也不跟我說話,悶頭悶腦地走在前面,與來時的心態截然兩樣。我明白,她肯定是生氣了,我也終于明白,她來縣城的真實目的。她這次來縣城,并不是想看什么造紙廠磷肥廠,她說要看那些地方,只是她一個巧妙的幌子罷了。其實,她最想去的就是我家,這是她的最終目的。我卻像一桶冷水朝她潑去,殘酷地讓她的希望之火破滅,堅決地掐斷了回家之路。我甚至懷疑,這很可能是隊長夫婦與她共同醞釀的計謀,讓我不知不覺地走進他們精心設計的圈套。
看見她老是一個人挑著擔子,我也有些過意不去,這么遠的路途,哪能讓一個妹子老是挑著呢?再說,她平時都是幫我的。
所以,我試探地說,喂,大妹,我來挑一程吧?總是你一個人挑,要不得嘞。
她不理睬我,也不說話,仍然悶悶地走著。當然,讓我放心的是,大妹的力氣很大,絲毫也不比后生們差,這是有口皆碑的,她能夠挑一百多斤,這點農藥是不在話下的。也所以,我并不擔心她挑不動,只是讓路人看見,我的臉上有些不好意思罷了。
大妹與她來的時候截然相反,一個是興味盎然滔滔不絕,一個是郁郁不樂一言不發。
我默默地走在后面,心想,從現在起,她如果徹底地改變對我的態度,不理睬我了,那么,也是一件好事,這就怪不得我了,我也不必承擔什么責任。
而事情的進展,誰又料得到呢?
那天,大妹看來真的生氣了,一下都沒有讓我挑。當快走進村子時,聽得見雞叫狗吠了,大妹突然又興奮起來,滿臉笑容地說,小姜嘞,今晚你要來我家吃飯,我家還有一塊臘牛肉嘞,我要我娘老子放點紅辣椒粉,再放點大蒜,保證蠻好吃的。哎,你要陪我爺老倌喝一杯嘞。她悶悶不語的狀態居然一掃而光,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我不由愕然。
其實,你們也能夠看得出來,隊長也是有這個意思的,想把大妹許配給我。當然,他還是比較含蓄的,講究一些分寸。他肯定將我和大妹對比過的,覺得大妹比我差很多,如果萬一談不成,他這個做爺老倌的,還有一個體面的退路,不至于怎么尷尬。當然,他也清楚我家的情況不盡如人意,父母天天挨批斗,而我畢竟是縣城的人,只是虎落平川罷了。
隊長娘子的態度卻很明顯,絲毫也不掩飾對我的關心,一旦有了好菜,就派大妹叫我下樓來吃。這個時候,隊長客氣地說,你想喝酒,自己倒吧。隊長娘子卻不一樣,滿面春風,不僅親手給我倒酒,還不斷地叫我夾菜,甚至還親自給我夾,夾得我碗里一堆的菜。我看得出來,大妹也想給我夾菜的,又有些不好意思,有點差澀,只是飛快地看我一眼,好像是鼓勵我放肆吃。
有一天,我從家里回來,還沒有走進隊長家的門,在屋檐下,隱隱地聽到大妹在大聲罵人。我不明白她在罵誰,為什么罵人,大妹的脾氣歷來是很溫和的。我沒有立即走進去,趕緊剎住腳步,悄悄地站在門邊聽。
只聽見大妹說,舅舅,你不要再說那個什么姓王的了,好不好?我是不會答應的。
她舅舅苦口婆心地說,大妹,我也是為你著想嘞,你也找得婆家了,小王的姑父還是公社干部,家庭條件不錯的嘞。
大妹憤憤地說,他姑父哪怕是縣里省里的干部,我也不愿意。語氣十分的堅決,沒有絲毫的余地。
說完,大妹忽然哭了起來,嗚嗚的哭聲從屋里幽幽地傳出來,濕淋淋地灌進我的耳朵。
我想,隊長夫婦應該表態了吧?這是關系到大妹的終身大事。我卻始終沒有聽到隊長兩口子說話,也許是他們不便說吧?舅舅畢竟是一番好意,做父母的如果表示反對,肯定會掃了舅舅的面子。當然,是否也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他們已經在心里同意大妹跟我了吧?
此時,我倒是希望大妹能夠答應下來,然后,選個好日子,讓她舅舅帶著那個姓王的后生來相親,再然后,定親結婚。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心里就輕松得多了,不必在這件事情上有什么顧慮了。這個大妹卻非常固執,簡直是寸土不讓。她這種強硬的態度,很可能也惹火了她舅舅,后來,我很少看見她舅舅來了。
大妹不僅做得田土功夫,針線功夫也相當了得。像她這樣的妹子,在鄉村是很受男方歡迎的,如果嫁過去,肯定是個狠角色。平時,我的衣服破了,她就給我縫補。另外,她好像在不斷地給我做鞋墊,我雖然穿著她的鞋墊,也只是一年兩雙而已。而我不明白的是,她哪里要做這么多的鞋墊呢?我看到她平時空閑了就不停地做,做得專心致志的。對于這個問題,我沒有問過她,她想做就讓她做罷,也許,這是打發閑時的一種方式吧?大妹做的鞋墊,每一雙的花紋都不一樣,花樣在不斷地翻新,或是菱形的,或是波浪形的,或是長方形的,或是梅花,或是桃花,或是梨花,等等,可見她的手藝是相當不錯的。
曾經有許多次,在樓上只有我和大妹。我們坐得很近,我記不得當時說過些什么話了,反正說得很開心。說著說著,只見大妹微微地閉上了眼睛,那種狀態,很明顯是讓我在她的臉上打啵。當然,我很理智,不敢打啵,擔心這一啵,會啵出許多的麻煩來,以后肯定難以脫身的。所以,我敷衍地說,大妹以后吧啊?我看得出來,大妹雖然感到十分失望,卻也沒有勉強我,她似乎同意我的意見,把打啵的浪漫放到以后,放到水到渠成之時。當時,我的確很膽小,甚至連大妹的手都不敢去摸,擔心會摸出許多的麻煩來。
由此可見,我對大妹的態度是非常曖昧的,或者說,是很模糊的。其實,大妹并不明白我從心底里是不喜歡她的,對她沒有一點感覺,而我又不敢說出來,倒不是擔心說出來對于她來說過于殘酷,而是擔心我的態度如果過于明了——不論是迎合,還是拒絕——其結局都會令我不寒而栗。前者害怕到時甩不掉她,她會像螞蝗死死地沾著我,后者是擔心隊長肯定不高興,以后會想方設法地給我小鞋穿,更重要的是,他如果卡住我招工呢?
我不喜歡大妹的理由十分簡單,她實在太矮了,一米五都不到,而且胖,胖得又不勻稱。像這樣的妹子,哪里會引起我的興趣呢?我雖然是個知青,算個落難之人,而我的審美觀和擇偶標準,也不至于差到這種地步吧?其實,我喜歡的是另一個妹子,那個妹子叫李桃桃,李桃桃不僅讀了高中,而且長得苗條,五官又十分的清秀。而李桃桃又不愿意跟我談對象,她比大妹理性多了,她說我以后肯定會招工的,像我這種人是根本靠不住的,她說,她還是嫁給農村人比較現實。所以,李桃桃沒有給我一絲希望。
總之,我和大妹這種含含糊糊渾渾沌沌的狀態,保持了三年多,一直到我招工的那天。
招工對于每個知青來說,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不論是去什么廠礦,畢竟是希望終于到來了,其興奮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我到招工的那天,卻沒有絲毫的興奮和激動,我以為,隊長一定會強迫我確定了與大妹的關系,才會放我走的。所以,我忐忑不安,十分緊張,以至于無法預料這件事情的最終結局。
也就是那天,隊長突然叫住了我。
當時,他坐在灶火邊,火焰映在他的臉上,臉色很難看,似乎充滿著怨恨矛盾和冷漠。他不說話,悶悶地抽著煙,眼睛卻死死地盯著我,我嚇得渾身起泡,意識到大事不妙。我曉得,招工的手續已經開始辦理了,我這次能不能夠招工,就是隊長一句話,他如果不叫我去大隊辦手續,我又怎么敢去呢?我膽怯地坐在他的身邊,一句話也不敢說,雙手緊張地伸進大腿中間,不斷默默地數著數,我不曉得要數到哪位數時,他才會張開尊口。我更不敢看他那難看的臉色,我的心高高地懸在廣闊的天空上。
那是決定我命運的關鍵一刻,我卻顯得是那么的可憐和無奈。我默默地數著數,以此來分散自己緊張的心理。現在,我已經數到六千三百五十二了,隊長還是沒有表態,所以,我只好繼續往下數。
我想,只要他不說話,我就一直往下數。
終于,漫長而沉默的過程結束了——當時,我默默地數到了九千五百六十二——隊長終于說話了,他痛苦地咳了幾下,口氣非常冷漠,居然沒有一絲祝賀的意味,好像是極不情愿地很快地把要說的話說完,所以,是一字一句地說的,他說,去—大—隊—李—秘—書—那—里—辦—手—續—吧。
我一聽,趕緊站起來,壓抑著滿腔的喜悅,低聲哎哎地應著,態度極其謙卑。然后,我真誠地說了一聲謝謝,飛快地跑了出來。我似乎生怕隊長反悔,然后,像一只快樂的小鳥,飛舞在一條條狹窄的田基上。我明白,這句話能夠從隊長嘴里說出來,是多么的不容易,又是多么的艱難。
我走的頭天晚上,大妹來到樓上,什么話也不說,只是默默地流淚,一直流到深夜。如果不是我催她去睡覺,她一定會流到天亮的。她一定明白,我們的關系到此結束,再也沒有一絲希望了。望著大妹,當時,我是有一種沖動的,想在她的臉上啵一下,作為一個永久的紀念。而我又擔心惹事生非,終于打消了這個念頭。
第二天,我以為她會來送我的,等了許久,卻連她的人影子也沒有看見。
在我的樓房門口,不曉得什么時候擺著一迭厚厚的鞋墊,整整齊齊的,擺在最上面的那雙鞋墊,繡的是盛開的桃花。
默默地望著它們,我頓時明白了什么,也許,大妹早就預料到有這么一天了吧?
小英的婚事
小英這個妹子,性格非常固執,或者說非常要強。
下面順便舉兩個例子——
其一,那年雙搶,村里的幾個妹子斗狠,小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們商量說,今天每人插一丘田,誰先插完秧誰先回家。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只是想想,還是有問題的,那些水田大小不一,面積不可能是一樣的均勻,又不可能把那些水田用刀子劃得整整齊齊的,然后,再進行公平的比賽——那只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做法罷了。所以,她們采取了鄉村最常見的辦法——拈勾。誰拈到面積小的,就算她走運,誰拈到面積大的,只能說她背時。小英的手氣不好,居然拈到了一丘最大的。對此,小英也默認了。然后,妹子們各自馬不停蹄地插起秧來。她們的動作非常快迅,手像雞啄米似的,將一蔸蔸綠色的秧苗插進渾濁的水田。隔遠一看,那一行行綠色的秧苗,就像是從她們屁股里排出來的。她們爭先恐后,從早晨一直插到太陽落山,那幾個妹子的田都插滿了,小英的那丘田呢,還遠遠地沒有插完。其實,這個結局也完全在她們的意料之中的,小英插的那丘田面積大許多。別的妹子見天色不早了,終于心軟了,站在田基上勸小英,小英小英算了,你那丘田本來就大些,我們還是回家吧。小英根本不理睬,翹著屁股繼續插,一直插到午夜。
其二,隊長有次說,你們這些妹子如果誰掮起了水車,我就給她加一分。那天,隊長本來是嘴巴沒有味了,分明是開玩笑的,他能夠預料到,沒有哪個妹子能夠掮起水車的,掮水車的只有男勞力。那時,男勞力一天十分,女勞力一律六分。如果每天能夠加一分,一年下來就很可觀了。當時,小英認真地問隊長,哎,隊長你說話要算數嘞。隊長聽她一說,也認真起來,拍著汗毛胸部說,我幾十歲的人了,哪里還哄過人呢?小英指指身邊許多的人,說,這么多的人可以作證的,到時候,不要說沒有聽見隊長說的話。眾人說,這個我們能夠作證,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嘞。小英果然也當真了。從那天起,只要有了空閑就練習掮水車。掮水車,也不是說掮就能夠掮起來的,它不僅需要力氣,還需要技巧。就說我吧,插隊這么久了,也不敢掮水車,一是擔心摔壞水車賠不起,二是沒有力氣,害怕閃傷了腰子,害了一輩子。小英卻十分的要強,許多人勸她不要掮了,說如果摔壞了水車,或是傷了腰子,都是個大麻煩,再說,你屋里也不靠你加上那一分。她偏偏不聽別人的勸說,硬要學著掮水車。所以,在那段時間里,一旦有了空閑,小英就站在保管室的屋檐下,咬著牙齒掮水車,還虛心地向男勞力請教,一招一勢的,很有章法。其實,那些男勞力雖然也教她,心里卻抱著一種看把戲的態度,背地里還說,小英如果把水車掮起來了,那狗都不吃屎了。小英卻不服狠,還是咬緊牙關掮,后來,水車終于讓她掮了起來。那天,她掮著水車,穩穩當當地走到隊長的屋門前,大聲叫喊,隊長,你快出來看,我是不是把水車掮起來了?隊長走出來一看,嘆道,哎呀,你這個妹子真是的,太霸蠻了嘞。隊長終于認了輸,只好給她加了一分。
那年,小英已經不小了。
其實,鄉下人說的不小,也就是十八九歲。按說,妹子一般在十五六歲就找婆家了,定親了。家里人也先后給小英找了幾個,她卻一個都看不上,看不上也就不說了,甚至還沒有好臉色給別人看,瞟著兩道特務似的目光,冷冷地站著。為此,她娘老子只差點沒有給她下跪了,求她說,小英嘞,人家來相親,你要放客氣一點嘞,何況,你給人家篩茶,人家還要放茶錢給你的嘞,至于談不談得成氣,那是要看緣分的,而的你茶錢反正是到手了嘞。
小英卻跟別的妹子大不一樣,不想去貪人家的茶錢,她并不看重錢,而是看重人。如果相親的后生來了,她不是大方地笑著跟人家見個面,打個招呼,試探著說些閑話,相互摸摸底細,然后,再從長計議。她卻是躲在睡屋里面,偷偷地從門縫朝坐在堂屋的拘謹的后生看一眼,眉頭忽地一皺,就皺出許多的不滿意來,然后,干脆躲著不出來了。你說人家是來相親的,妹子如果不出來,這又是哪里的規矩呢?難道讓別人白走一趟嗎?她的父母顯然很尷尬,大聲叫她,小英小英,快出來嘞。心想,她如果不出來,就要拖她出來,不信她今天不亮相。然后走過去,嘴里還在叫小英。誰知推開門一看,睡屋里面卻是空空的,沒有人影子了。原來,小英早已從窗戶上逃走了。
對此,我疑惑不解,也曾經問過小英的。我說,你這個后生也不要,你那個后生也不要,你到底要嫁個什么樣的后生?
小英也很直爽,毫不隱瞞地說,起碼要嫁個吃國家糧的。
我覺得,小英是個心氣很高的妹子。
后來,固執的小英卻碰上了一個固執的后生。
那個后生是楊家坳上的,叫楊國生。楊家坳上離我們村子有八九里路,不遠也不近。那個姓楊的后生我也看到過。實話說,長得還是蠻不錯的,一頭黑長發,多少像個有文化的。人也很拘謹,顯得很忠厚,不像有些后生油腔滑調的,張揚得過分。當然,有句話我不便當著小英說,擔心傷了她的自尊心。如果依我之見,那個姓楊的后生比小英強多了,我指的是各方面。僅僅說長相吧,小英的長相其實并不怎么出眾,蒜頭鼻子,臉皮又黑,嘴巴皮還有點厚,根本談不上什么乖態。當時,我還懷疑,這個楊國生怎么這樣愚蠢呢?那么多乖態的妹子不去找,怎么偏偏看中了小英呢?其實,他是完全能夠找到比小英強兩倍或是強五六倍的妹子。
而對于這門親事,小英仍然不答應。
不答應的理由,居然是嫌姓楊的是農民。
這難道不是在說笑話嗎?你小英不也是農民嗎?你又有什么理由嫌棄人家呢?再說吧,找對象是要講緣分的,也是要講機會的,過了這座山,就沒有那道坳了,盛開的花朵就會凋謝了,如果沒有找到吃國家糧的,你小英是不是不嫁人了呢?
所以,我也十分著急,好像小英是我的親妹妹,眼看著這朵鮮花快要凋謝了,我就耐心地勸她。我說那姓楊的后生蠻不錯的嘞,又是一副通情達理的樣子,你如果嫁給他,肯定沒有虧吃的。我還說,姓楊的后生看來有點文化嘞。小英聽罷,仍然不愿意,耳朵根本不進油鹽,居然信誓旦旦地說,老姜,我已經下了決心,如果不找個吃國家糧的,我絕不罷休。
小英不愿意談這門親事,她的父母卻很愿意。她父母已經讓小英氣過許多回了,也難堪過許多回了,所以,這次也下了死決心,小英不愿意,他們做大人的愿意,如果繼續任著妹子的脾氣,一拖再拖,拖到年紀大了,拖到皮肉起霉了,那么,狗都不會來聞的。所以,她父母擅自做主,不管小英答不答應,楊國生他們是要定了的,甚至叫楊國生經常來走動,他們就不相信女兒永不回頭。楊國生也就聽了小英父母的話,雖然心里有點不舒服,大概覺得能夠找到小英這樣的妹子,也就很不錯了。她雖然現在還不答應,他相信這只是暫時的,人心是肉長的,他相信自己會慢慢地打動她。所以,楊國生經常來走動,并且使出了水滴石穿的功夫。
楊國生是很會做人的。
每次來,他要給小英家送些禮物,或是一條魚,或是一只雞,或是一刀肉,那些禮物上面還要貼上一小綹紅紙條,以示鄭重和客氣。后來,他聽小英的父母說過,說小英最喜歡吃蝦米了,楊國生就不辭辛苦地去河里撈蝦米,撈到蝦米,馬上提著籃子活蹦亂跳地送過來。
小英卻很倔,曉得蝦米是楊國生送來的,從來也不嘗一口,筷子根本不往那個碗里伸,好像桌子上沒有渾身通紅的辣椒炒蝦米。楊國生雖然愕然和尷尬,卻不吱聲,默默地忍受著,一口一口地吃飯。加之,有小英的父母在穩住他的心,他也就沒有把愕然和尷尬流露出來,更不是一氣之下走人。有小英的父母做他的堅強后盾,所以,他顯得很有底氣,竟然百折不撓,甚至一如既往地送蝦米來,也不管小英吃不吃,反正,他的心意算是徹底地到位了。
楊國生這個人真是蠻不錯的,不管小英松不松口,對他是什么態度,他甚至還不辭辛苦地幫著小英家做事,簡直像個上門女婿。每回來,楊國生也不歇口氣,進屋打個招呼,就扛起鋤頭,或是挑著糞水,去挖土,或淋肥,每回累得滿頭大汗。村里人誰不夸這個后生呢?他們都曉得,小英的態度沒有絲毫的改變,就紛紛說,像這樣的后生,真是太少了嘞。甚至還指責小英太不懂事了,說她的心比鐵還要硬。小英的父母親,當然是非常滿意楊國生的,每回看見他來了,就背著小英狠狠地惡罵小英,說她簡直是瞎了眼睛,脾氣像牛牯一樣犟。楊國生聽了,只是微笑,輕輕地說,不要罵她。好像心里早已有了底案,相信小英一定會慢慢地轉變過來的。當然,小英父母還勸楊國生不必性急,說這樣的事得慢慢來,性急吃不得熱豆腐,他們一定會叫小英回心轉意的。所以,楊國生也就鐵了心,堅定不移地來,十分勤快地來,提禮帶物地來,還笑著附和地說,對了,慢慢來吧。
小英好像有什么預感,因為楊國生每次來了,她基本上就不在屋里,也不回來。開始,她還在屋里吃飯睡覺,并不回避楊國生。現在呢,大約是看見楊國生的臉皮太厚了,他已經和自己父母串通一氣狼狽為奸了,所以,她也采取了更為斷然的措施。只要楊國生來了,小英就不再在屋里吃飯睡覺了,那到哪里吃呢?她不是在張家吃飯,就是在李家睡覺,總之,與楊國生避而不見,眼不見為凈。她不擔心沒有地方吃飯,也不擔心沒有地方睡覺,她有一伙蠻好的女伴,女伴們都曉得她的心氣很高,非一般人不嫁的,也就十分理解地接納了她。
我經常看到楊國生在小英家的菜地忙碌,像愚公般的揮汗如雨,所以,心里也隱隱地生出一絲憐憫和同情。像楊國生這樣提前為岳父母拼命賣力,真是可以作為一種典范的,難道小英的心是鐵打鋼鑄的嗎?看到楊國生這樣年輕的活愚公,難道絲毫也不為之動心嗎?當然,這本來也不關我的卵事,小英愿不愿意嫁人,需要她自己點頭才算數的。我這是咸籮卜操空心,實在是看不過眼了。后來,我對小英感嘆道,小英啊小英,像這樣的后生,真是打起燈籠也難找的嘞。
小英卻毫不領情,憤憤地說,累死活該。
當然,小英還算是不錯的,她一直對楊國生采取回避態度,并沒有直接跟楊國生發生過任何正面沖突,這就避免了許多的難堪,以及不必要的口舌。看起來沒有硝煙彌漫,沒有刀光劍影,雙方都在以婚姻的名義,默默地打著一場堅韌之戰。楊國生真是固執得可愛,仍然掉在未來婚姻的夢想之中不能自拔。他天真地以為,小英的腦子哪天一定會開竅的,就像陽光終會從層層烏云后面萬丈光芒地照射下來。所以,他仍然照來不誤,在那條八九里路的小道上來來回回,好像已經把這里當做第二個家了。
這一切,小英也隨他去了,并不干涉這個頑固不化的后生,任他馬不停蹄地走在鄉間的小路上,任他揮汗如雨地像個活愚公,任他不斷地來向自己的父母獻殷勤,反正只要自己不松口,把嘴巴緊緊地守住,這樁婚姻肯定就沒有戲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楊國生這個年輕的活愚公,在稱呼上居然也起了變化,喊小英的父母不再叫伯伯伯母了,已經改叫爺娘了,竟然叫得大大方方,自自然然,一點也不生澀,或者害羞。小英的父母倒沒有什么意見,咧開嘴巴,樂哈哈的,想來這種喊法,也只是遲早的事了,楊后生想喊,就讓他喊吧。所以,不論是喊的還是跟應的,雙方都高興。當小英曉得這事之后,氣憤極了,有一天等到楊國生走了,回來沖著父母大罵,是誰讓他這么喊的?他憑什么這樣喊?真是死不要臉,臉皮比牛皮還厚嘞。
罵得父母不敢做聲。
她的父母一想,也是覺得有點虧理,他們畢竟還沒有成親,甚至連訂婚也是遙遙無期,憑什么就喊爺娘呢?
那天晚上,小英罵過了,還砰地摔爛一個茶碗,粉碎的白瓷片綻放在地上,像一片雪花。
后來,小英終于忍無可忍了,不愿意讓這種似是而非的局面繼續下去了,也沒有耐心打堅韌戰了,她要采取更為果斷的措施了。當然,她做得很沉著,并沒有聲張,更沒有提前把這個消息發布出去。她悄悄地向那些女伴借了軍裝軍帽和皮帶,還借了一個紅袖筒,紅袖筒上印著紅農兵三個黃色的大字。當時,這些行頭并不難借,那個時候,每個村子都備有這些行頭,演樣板戲需要。女伴們問她借這些東西做什么,小英說,她要演一曲好戲。問她究竟要演一曲什么樣的好戲,她又不說。
沒過多久,楊國生又來了,汗水涔涔的,手里仍然提著鮮活的蝦米。那天,小英的父母走親戚去了,只有小英在屋里。楊國生哪里又曉得呢?一腳跨進門檻,就親切地喊爺娘。誰料沒有人應答,又高喊一句,小英的父母也沒有出現,卻把小英從睡屋里叫出來了。
楊國生抬頭一看,呆住了。
只見小英一身軍裝,頭上戴著軍帽,腰里束著寬大的皮帶,手臂上戴著紅袖筒,英姿颯爽,且雙眼怒瞪。她連招呼也沒打,大聲地喝道,姓楊的,你以后再也不要來我屋里了。
楊國生見小英這副嚴肅的打扮,又是這種憤怒的口氣,一時膽怯起來,困惑地問,為什么?
小英繼續憤怒著,說,你曉得你舅舅是什么人嗎?哼,你瞞得了別人,瞞不了我,你——她伸出一只手指向門外——現在,你趕快給我滾出去。聲音鏗鏘有力,像鐵錘一錘一錘地敲出來的,不容人有絲毫的遲疑。
這一番話,把楊國生嚇得說不出話來,呆呆地望著冷漠憤怒的小英,提著的蝦米叭地掉落在地,蝦米們卻全然不顧屋里緊張的氣氛,一只只活蹦亂跳的。楊國生終于明白了什么,怔了怔,趕緊灰溜溜地逃走了。
再也沒有來過。
小英的父母見未來的女婿沒有來了,覺得很是奇怪,楊后生是不是生病了呢?想托人去問問,又沒有人去楊家坳上,就很迷茫地問小英,國生怎么不來了?
小英心里很高興,他娘的腳,這場堅韌戰終于取得了最后的勝利。當然,她還是很沉得住氣的,沒有流露出一絲勝利的喜悅,只是不耐煩地說,我怎么曉得呢?
小英的父母覺得這件大事結束得有點奇怪,兩人就去了一趟楊家坳上。在楊家的菜地,他們見到了仍然很愚公的楊國生,心想,呃,這個后生沒有病么。然后,小英的父母擔憂地問他為什么不來了,楊后生的態度仍然是很不錯的,只是沒有喊爺娘了。他抹了一把汗水,就很慚愧也很老實地把原因說了出來。
小英的父母聽罷,也怔住了,半天沒有說話。
小英雖然終于痛逐了楊國生,而當她與我說起這件不了了之的事情時,眼睛居然濕紅了。她難過地說,老姜呀,其實呀,我也不是鐵板一塊呀,人心畢竟還是肉做的呀,對于他呀,我也不是沒有動過一點心的呀,我也想過的呀,只要他對我好呀,不吃國家糧就不吃國家糧呀,而你不曉得呀,他舅舅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呀。
我猛然一驚,心想,哎呀,原來如此呀,且不說他舅舅曾經是國民黨,就說我父親吧,他老人家年輕時曾經稀里糊涂地參加過三青團,現在已經搞得慘兮兮的了。
問,你怎么曉得的呢?
小英很自信,言之鑿鑿地說,我早就調查過了的呀。
噢。
小青的假期
在村里,我雖然十分孤寂,也不去滿五娘屋里,滿五娘是個孤寡老人,去她屋里玩耍又有什么味道呢?想必也是冷冷清清的,一點鬧熱也沒有。況且,我跟她年紀相差太大,幾乎無話可說。再者,聽說她的成分太高,過去是地主的三姨太,曾經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所以,我也不想跟這樣的人來往,以免引起別人不必要的猜疑。
那個年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后來,我竟然去她的屋里玩耍了,而且去得很勤快,像泥鰍斗水,斗一回,又斗一回,似乎沒有什么顧忌了。對于這個異常的情況,你一定會感到很奇怪吧?
其實,也沒有什么奇怪的,凡事都有它的起因。
滿五娘屋里忽然來了一個妹子,叫小青。
小青大約十五六歲,是滿五娘的小侄女,還在讀書。每次到了假期,小青就背著書包,提著綠色的網袋子,來滿五娘這里住個幾天。原因很簡單,小青的父母不想讓滿五娘太孤單,所以,叫小青來陪陪她。
小青看來是個心氣很高的妹子,來了之后,似乎看不起村里人,好像跟村里人有某種隔閡吧,反正是不怎么來往的。她如果不跟大人們來往,我還是能夠理解,一個小妹子,跟大人們又有什么話說呢?問題在于,她跟與年紀一般大的妹子也不來往,見面既不笑,也不打招呼,目不斜視,像一只高傲的天鵝,所以,對于那些雀鳥之類,就沒有放在眼里了。惟獨看見我,她的眼睛唰地亮了一下,像兩只在黑夜中突然亮起的電燈。我的眼睛也唰地亮了一下,也像兩只在黑夜中亮起的電燈。
那是在井邊挑水時,她挑著水剛好離開,我挑著水桶往井邊走。在狹窄的小路上,我們初次相見,所以,雙方的目光碰上了,突然唰地亮了一下。當這個陌生的妹子與我擦肩而過時,我轉過身子,望著她苗條的背影,很遺憾沒有及時地趕來,如果趕來了,我可以幫她打水,跟她說說話,還可以幫她挑水回家。
所以,我非常明白,自己失去了一個接近她的最佳機會。
直到這時,我才曉得滿五娘屋里來了一個很清秀的妹子。只是她從來不亂走動的,規規矩矩地呆在屋里,像個怕丑的妹子。我覺得這個妹子很不錯,跟村里的那些妹子不一樣,那些妹子的眼睛和臉上都是呆滯的,像剛病過的一樣。她身上呢,卻有一種特別的東西,臉色光澤,潤滑,尤其是她的眼里,有兩股水一般的靈氣,顯得透亮而聰明。
我很想接近接近她,跟她玩耍。
我又不便冒昧地去滿五娘屋里,我以前根本不去的,也不想去,其中的原因,在前面已有了說明。如果我現在突然去,滿五娘肯定對我很反感的,她會想,哦,你平時不來,或是不敢來,看見小青來了,你就來勁了哦。
所以,我心里還是有一定的障礙。
又很想跟小青玩耍,即使她比我小三兩歲。
我認為,跟這樣的妹子玩耍,心里頭會感到十分的舒暢。我還覺得,她呆在屋里一定是不好玩耍的,陪著那個老婦人,玩什么耍什么呢?年齡相差也太大了。如果有我在的話,她肯定就好玩耍了,我覺得,我們之間有許多的話說,也會想一些游戲玩耍的。我卻沒有更好的理由順理成章地打進滿五娘屋里,所以,我只好故意在她的屋門口走來走去,好像在散步,也好像在思考問題,當然,也好像是在看槐樹上的喜鵲。總而言之,我出現在她的屋門口,是希望小青能夠看見我,然后,叫我進去坐坐。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切顯得很自然了,沒有尷尬,沒有難堪,也沒有拘謹。而讓我感到特別失望的是,滿五娘的那扇門,雖然是大打開的,卻沒有出現過小青那張青春的面孔,從外面看去,屋里面黑鴉鴉的,似乎彌漫著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迷霧和少有的空寂。
我不心甘。
我想,小青肯定會出現在門口的,或是看看外面的風景,或是出來透透氣,她每天呆在空蕩蕩的屋里,一定是索然無味的。她耐不住那種清靜,她不像她的姑媽。
有一天,我又故意走過滿五娘屋子,碰見小青竟然站在門口,怔怔地看著那棵老槐樹,她在用目光捕捉那只躲在樹上唱歌的喜鵲,喜鵲清脆的叫聲不絕于耳,像鄉間一個充滿山野之氣的歌唱家,放肆而毫無顧及。這時,她往樹上射去的目光忽然降了下來,不經意地落在我的臉上,目光中先有幾許驚訝,然后,變成了一絲驚喜,還咧開小嘴對我微笑。我趕緊笑了笑,近乎于有點討好的意思。我意識到自己的笑容很不自然,卻的確是發自于內心的,只是不應該加上討好的成分。讓我感到微微惱火的是,她并沒有說話,也沒有示意我進屋里坐,然后,像一只鳥忽然消失了。
顯而易見,她不便自作主張叫我進去吧。
這道門檻,分明成了阻礙我們來往的一堵隱形的墻。
第二天,我去井邊挑水,看見小青站在路邊歇氣,桶里是滿滿的水,她一手扶著扁擔,一手擦著額頭上的汗水。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大膽地笑著說,哎,你挑不起吧?
小青輕輕地嗯一聲,好像有點羞澀。
我沒有猶豫,老子得抓住這個絕好的機會,我馬上放下肩上的水桶,拿過她手中的扁擔——她并沒有拒絕——挑起水往滿五娘屋里走。她跟在我的后面,低著頭,似乎害怕別人看見。我倒是沒有什么顧慮,挑著水,悠悠晃晃地走進她屋里,利索地把水倒進了水缸。
這時,滿五娘從豬欄里走出來,一眼看見我,有點驚訝,然后,滿面笑容地說,呃,哪里還要麻煩你呢?她狐疑地看著小青,小青趕緊解釋說,姑媽,我突然肚子痛,挑不動嘞。
我沒有說什么,放下空水桶。
我明白,萬事開頭難,而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從此,我和小青的交往,將會徐徐地拉開序幕。滿五娘沒有叫我坐,小青也不便說,所以,我也沒有停留,滿懷信心地走出來,并不計較這一時的得失。
小青說,你要來耍呀。她站在門口,揚起舒展而光澤的臉,一點也不像肚子痛。
我頓時感到滿身清爽,說,我明天會來的。心想,哎呀,小青真是一個鬼精精,她哪里肚子痛呢?她只是找個借口,制造一個機會留給我。
由此可見,她實在比我聰明多了。
從此,我就名正言順地去滿五娘屋里玩耍了。滿五娘對我很好,每回看見我來,就叫小青,小青呀,老姜來了嘞。
小青還以為是誰來了,從睡屋出來一看,立即嗬嗬直笑,說,姑媽,人家才多大呀,你竟然叫他老姜,難聽死了。小青笑得眼睛瞇起來,像被強烈的陽光耀花了。
滿五娘也笑,說,村里人都是這么叫的,我也改不了口。
小青撒嬌地說,別人怎么叫我管不到,姑媽,你不能這么叫嘞。
滿五娘讓了步,說,好好好,叫小姜可以吧?
僅憑這一點,小青就足以讓我感動,雖然男女老少都叫我老姜,甚至,連半大的細把戲也叫我老姜,我也不反感,早已習慣了。而小青這么說,的確讓我很感動,她讓我得到了我應當得到的恰如其分的稱呼。
后來,小青只要見我來了,就大叫,姑媽,倒茶。或者說,姑媽,炒瓜子。或者說,姑媽,拿紅薯絲來。看見她大大咧咧地指揮她的姑媽,我覺得非常好笑,小青真是來做客的,自己什么事也不做,把個老姑媽指揮來指揮去的,好像姑媽是她手下的兵嘍嘍。好在她姑媽并不跟她計較,小青說什么,她就做什么,很順著小青的。
我看得出來,滿五娘沒有崽女,很痛愛這個小侄女。
我經常來滿五娘屋里玩耍,心里沒有任何的顧慮了,我已經順利地取得了通行證,滿五娘那道高高的門檻已任我成功跨越。有時,小青居然叫我告訴她做作業——我明白,她這是不愿意冷落我——這對于我來說沒有什么問題,我肚子里還有幾滴殘存的墨水,教她還是綽綽有余的吧。我每每幫她解開一道難題時,小青就要舒展微皺的眉頭,高興地驚叫起來,拍手稱快,哈哈,又攻克了一座堡壘。小臉上興奮地泛起淡淡的紅暈,然后,竟然癡癡地看我。她的目光很清澈,十分單純,又有幾許迷離,像一把無形的鵝毛扇輕輕地拂在我的臉上。我當然喜歡她這樣看我,這讓我感到十分得意和滿足。她并不是偷偷地看我一眼就馬上把目光移開,居然是無所顧忌的,久久的,癡癡的,好像要將我臉上的細菌也一粒粒地查看出來。
每次,我都把臉乖朝著她,坦蕩地微笑著,讓她看個飽。
小青每次來她姑媽這里,一般只住幾天,五六天,七八天不等。所以,我很珍惜小青在村子的那幾天時間,我只要有了空閑,就往滿五娘屋里鉆。像這樣鉆進鉆出的,你如果猜測我跟小青會發生什么故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什么故事也沒有,兩人就是說得來,我們在一起,都感到舒暢和愉悅,另外,還有一點小小的默契。她想說的話,就是我想說的話,我想做的事,就是她想做的事。
對于這一點,我們暫時都無法解釋,只是會心地笑笑。
小青每次離開村子時,都是依依不舍的,嘟著嘴巴咒道,這個鬼日子過得太快了,像飛一樣的。
我也無奈地嘆息說,是呀,太快了。
我總要默默地送她一程。此時,兩人的心情已不太愉快了,黯然無光,好像是最后的訣別。
小青明亮的眼睛望著我,幽幽地說,哎,我走了,你會想我嗎?
我說,想。
我說,我希望你不要走,你多住幾天吧。
我說,我希望你搬到你姑媽這里來。
我說,那我們每天能夠在一起了。
小青聽罷,情緒低落地說,那是不可能的嘞。
小青也舍不得走,腳步慢吞吞的,一步,一步,再一步,像在仔細地丈量彎曲的路程。她一直走到了橋頭,才說,我走了。低著頭,走幾步,又轉過身向我揮揮手,然后,向前走去。
我站在古老的小橋上,望著她背起書包,提著網袋子慢慢遠去,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
所以,在下一個假期尚未到來之時,我的心情十分黯淡,幾乎天天都在猜測,不曉得此時的小青在做什么,是在靜靜地看書?是在悠然地放牛?或是跟她的伙伴玩耍呢?她告訴過我,她家住在牛山河,離我的村子足足五十里路,沒有車。其實,五十里路并不可怕,我是可以去看她的,即使我能夠去看她,也令我感到十分為難,我難道走到她那里,看看她就馬上離開嗎?我怎么對她的父母解釋我來看她的理由呢?凡此種種,讓我躊躇再三,怎么也拿不定主意,惟有天天在心里數著那些漫長的日子,把厚厚的晝夜一頁頁地翻過去,翻著翻著,我居然一點耐心也沒有了,翻得焦急而狂燥。而那些日子,偏偏跟我做對似的,我明明已經把它們翻過了許多,仔細查看,后面仍然堆積著厚厚的一沓。
惟有等到假期到來,小青終于出現在我的眼前時,我才清醒地明白,那些堆積著的厚厚的日子,終于被我又一次翻完了,我和小青高興得跳躍起來,兩人似乎很想擁抱,又顧忌什么,就激動地打著手板,顯得極其興奮。我們甚至忘記了問候,忘記了說話,像細把戲一般,響亮地拍打著手板,直到把對方的手板打得緋紅,像兩皮熟透的楓葉。
這就是我們相見時的方式,很有分寸,當然,也足以表達了我們快樂的心情。
滿五娘不太管我們,任我們聊天,或是擺著算盤打九九歸一,或是做作業,間或去山上玩耍,她忙著切豬草,喂豬,打鞋底,縫補衣服,淋菜,煮飯菜,或是做其它的雜事。她似乎并不反對我和小青的來往,有了我,她的侄女不至于寂寞和孤單了,有了我,她的侄女在學習上有了長足的進步。我不遺余力地把肚子里那點殘存的墨水潑撒出來,點點滴滴地潑撒在小青的頭腦里,點點滴滴地潑撒在她的作業本上。
有一次,滿五娘叉開雙腿,坐在堂屋切豬草,嚓嚓的聲音很有節奏,聲音里含有青草嫩嫩的氣味,不時撲面而來。我和小青坐在桌子邊,我在教她做作業。我們跟滿五娘相距不遠,大概四五米遠吧,她是面對著我們坐的。滿五娘一直低著頭切豬草,神情專注,好像在欣賞從刀下切出來的節節翠綠,也好像忘記了我們就坐在她的對面。所以,當滿五娘于不經意間抬起腦殼時,眼睛隨便掃了我們一眼,突然發現小青手里拿著筆,正在癡癡地看我——她這樣看我已成了家常便飯,只是滿五娘沒有發現而已——滿五娘忽然顯得慌亂起來,甚至是不滿,然后,故意將菜刀咣當地丟在腳盆里,似乎用這種特有的方式提醒小青,叫她不要用那種異樣的目光看我。
小青卻全然不顧,依然一動不動地癡看我。
其實,我也是于無意間才發現滿五娘的目光的,那不滿的目光陡地讓我驚悚不已,像她手中的菜刀唰唰向我雪亮地飛來,我立即別過臉,故意看著空蕩蕩的門外,好像并沒有接受小青的癡看。同時,我忽然有了不妙的預感,滿五娘一定會阻止我與小青繼續來往的。
當時,我想暗暗地扯一下小青,或在桌子底下踢她,提醒她不要繼續癡看我了,而在滿五娘那近乎于敵意的尖銳的目光下,我任何一個細小的動作,都將徹底暴露。我心里的焦慮簡直無法言說,我甚至想突然跑出去,暫時脫離這個窘境,又覺得過于突兀。小青呢,這個蠢妹子,似乎沒有聽見姑媽丟下菜刀的聲音,也不在乎刀聲為什么不繼續響亮了,更沒有注意姑媽那不滿的眼光。
這時,我急中生智,馬上抽身而出,說要去上茅室了。然后,趕快躲避這個無聲而讓人擔憂的境地。
不出我意料,有了這一次,滿五娘果然對我的態度冷淡起來,即便是笑,也是佯裝出來的,不再是那種自然的微笑了。我呢,如果再來滿五娘屋里,心里無端地生出了一種畏懼感,像個賊牯子似的縮手縮腳。與小青說話時,我十分的緊張和拘束,居然前言不搭后語,吞吞吐吐,好像害怕誰來抓我似的。
小青并不曉得其中的內幕——我也不便向她解釋——她張著迷惑的眼睛看我,說,哎,你怎么啦?
我裝著很平靜地說,我沒怎么呀?
小青嘀咕道,那你怎么像被鬼捉到的呢?
我沒有回答,飛速地朝站在灶屋門口的滿五娘瞟一眼,她的目光尖銳地朝我射來,讓我不寒而栗。
小青顯然看到了我的目光轉向她的姑媽,還以為我是害怕她,轉過臉說,姑媽,你不要站在那里看我們好啵?
滿五娘沒有說話,這才像幽靈般無聲地消失,消失在掛滿黑色灰線的灶屋。盡管如此,我還是不能夠恢復到過去那種自然的狀態。我明白,滿五娘開始對我十分警惕了,誤以為我居心不良,在悄悄地勾引小青——其實,是小青喜歡癡看我的。所以,我已經無法控制住內心的擔憂和害怕,又無法不去看小青,如果不看她,心里像有了一個空缺,似如一片翠綠的秧田扯走了一大塊,而這空缺的一大塊,是什么東西也不能夠彌補的。
——我竟然也是這樣的無可救藥。
我曉得,這次離小青走的日子只有三天了。
那天晚上,我吃過飯,又去滿五娘屋里。堂屋沒有人,擺在桌子上的油燈,在透明潔凈的燈罩里穩穩閃亮,并不害怕夜風魯莽地干擾。我靜靜地站一陣子,想等著小青走出來,卻沒有見她出現在堂屋。
這時,我聽見廂屋有人說話,側耳一聽,原來是滿五娘在悄悄地對小青說話,她說,蠢崽,你千萬不要跟人家老姜好嘞。
小青說,人家是小姜,姑媽你說吧,我為什么不能跟他好呢?
滿五娘說,哦哦,是小姜,你問為什么?我告訴你,他出身也不好,是大地主嘞。
哦——小青長長地一聲,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意味。
此時,我像被人揭穿了一個巨大而丑陋的秘密,渾身似乎長滿了鐵刺,刺得我疼痛難受,滿面羞愧,我再也沒有勇氣呆下去,悄悄地溜了出來。
第二天,小青也沒有叫我去玩耍了,即使在挑水時碰見,她竟然也不理睬我,眼皮怯怯地一耷,就匆忙地走開了,十分害怕我似的。這個巨大的變化,讓我一時難以承受,想一想,又有幾分理解。當然,我也沒有叫她,默默地看著她的背影慢慢消失。
在我后來插隊的日子里,不論是放寒假,還是放暑假,小青再也沒有來滿五娘這里了,好像在這個世上消失了。我不便問滿五娘小青為何不來了,即便問她,她也未必回答我。后來,滿五娘如果有了什么病痛,也只見小青的父母急匆匆地趕來。
小青呢,再也沒有來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