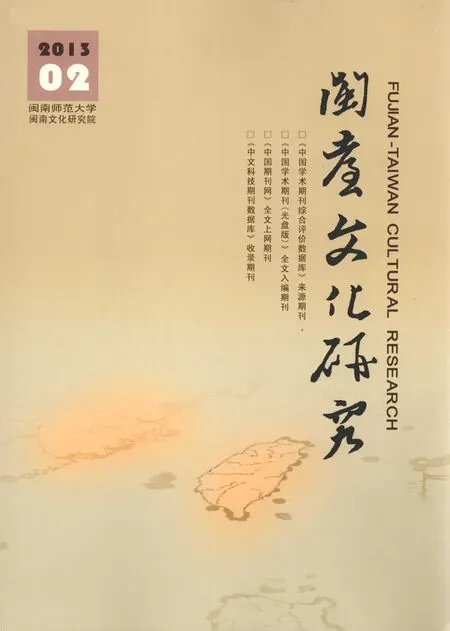朱熹葉適詩歌理論之比較
許光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350007)
朱熹葉適詩歌理論之比較
許光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350007)
朱熹與葉適雖同為儒家文化的倡導者,但在“道”目標上兩人卻發生了分歧,從而導致了他們在詩歌理論上存在著差異。朱熹從“文道一體”的文學本體論出發,倡導“溫柔敦厚”的詩教,講求法度,追求平淡雅正之作,尊古非律。而葉適則在“經世致用”的大旗下,秉持“德藝兼成”的詩教,尊古而不陋今,追求平淡自然的審美情趣。
朱熹;葉適;詩教;平淡自然
全祖望在《水心學案·按語》中曰:“乾、淳諸老既沒,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齦齦其間,遂稱鼎足。”這段文字論述了南宋中期三大學派三足鼎立的盛況,其中以朱熹為代表的正統理學派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因秉持理念不同,彼此爭勝,各不相讓。而朱、葉兩家詩歌理論差異則是兩大派別對立爭勝的文學表現之一。朱、葉作為文壇的領袖人物,其詩歌理論直接指導著詩壇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當時詩壇的面貌。因此,研究朱、葉詩論之異同,對于研究和解釋整個宋詩創作中的某些現象,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詩教觀
在中國傳統儒家文藝理論中,“文”與“道”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的命題,荀子開其源,楊雄助其瀾,劉勰最終匯其成。到了唐宋時期,文道關系得到了更突出的重視,古文家的“文以貫道”和“文以明道”論對后來的理學家的文學觀念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理學家之中,周敦頤首先提出“文以載道”說,把古文家的“文以貫道”說從本體方面向前推進了一步,其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周敦頤認為,如果僅有“文”的外在形式而失去了“道”的內涵就如同“輪轅飾而人弗庸”。其實,周敦頤并不完全反對文飾,只是反對不載道的徒飾。其后,走上極端的程頤不但強調“有德者必有言”,而且用道體排斥文藝,提出“作文害道”說和“玩物喪志”說,其曰:“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程頤最大程度的表現了對文藝的偏見,認為追求文辭華美的文章就是玩物喪志的表現。
相比較而言,朱熹對待文學的態度要緩和很多。從理學立場出發,朱熹構建了“文章皆從道中流出”的文學本體論。其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然而又曰:“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矣。”朱熹此論打破了古文各家分裂文道為二物的格局,即“文自文,道自道”的格局,將僅限于道德內容與辭章關系的文道說升華到體用關系的高度,所以莫礪鋒先生就認為“由于有了‘文道一體’的觀點,朱熹的重道輕文就與二程等人的重道輕文有本質上的不同,……‘文’與‘道’是不可分割的,雖然‘道’比‘文’重要,但‘文’也即文學仍有存在的理由。”故而錢穆亦總結說“輕薄藝文,實為理學家通病。惟朱子無其失。其所懸文道合一之論,當可懸為理學文學雙方所應共赴之標的”。
以“文道一體”說為基礎,朱熹認識到詩與文有不同的價值導向,于是將傳道之文與抒情之詩加以區別“文自道中流出,詩從情中發出”。他把詩歌歸結為人類主體情感的外在表現,認為詩的產生是情感自然流露的結果。因此,“詩本言志”就具有了超越道學內涵以外的內容,詩歌抒發情感的功能也得到了確認。與此相應的是,朱熹特別重視詩歌感發人心的作用,要求詩歌能促進人的情志和道德的升華,滿足倫理教化的需求。
從儒家詩教傳統出發,朱熹倡導“溫柔敦厚”的詩教,其于《南岳游山后記》云:“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覺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于詩哉?……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郁,優柔平中,而其流乃至于喪志……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御之哉?詩歌是用來宣泄心中情感的,但是必須束之以“優柔平中”,不能失之末流,喪失詩本。至于如何表達情感,其總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諷刺人,安得‘溫柔敦厚’!”《詩集傳序》亦云:“曰:然其何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音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朱熹認為只有圣人之言足以為教,詩歌要有所諷勸,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這種“溫柔敦厚”的詩教觀與葉適的詩教觀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由于朱、葉兩人對“道”的認識不同,所以其詩教主旨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首先,葉適曾對物與道的關系作過細致辨析,其曰:“余嘗怪五言而上,往往世人極其材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巨伯輒不能工,何也?按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斯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物與道的關系在這里被深刻闡釋出來,葉適認為理非先天的存在,因為有物之存在,道才能以體現。而《水心別集》又曰:“詩之興尚矣,夏商之前皆磨滅而不傳,豈其所以為之者至周人而后能歟?夫形于天地間,物也:皆一而不同者,物之情也。”葉適認為,“物”是第一性的,“情”是第二性的,情是物的外在表現形態。通過對“物”與道關系的論述,葉適得出詩為抒情工具的結論。
其次,葉適并沒有承續程朱所建構的道統,而是對儒家道統進行了重新的闡釋。其曰:
道始于堯……次舜……次禹……次湯……次伊尹……次文王……次周公,治教并行,禮刑兼舉,百官眾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義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圣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然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傳。葉適所謂的“道”是“治道”,是闡明于孔子的三代之治道,明顯不同于朱熹等人的“道”。不僅如此,葉適還對朱熹等人所建構的孔子以后的道統傳人逐一進行辨析,對他們傳“道”的史實進行了否定:“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此外,針對程朱學派對北宋理學諸家發明的千載不傳之學的觀點,葉適也給予了否定,他認為周、張、二程參以佛老,根本不是孔子思想“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
既然程朱不合道統,那么誰才是道統的傳人呢?當然是葉適自己,他的學生孫之弘曾對其老師的道統做過全面的總結:
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饑食之切余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腧中盲之速于起疾也;推跡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圣之緒業可續,后世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郞,無異親造孔室之閎深,繼有宗廟百官之富美,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
這段論述既推尊了葉適的道統地位,又解釋了葉適的“治道”之“道”。
葉適論詩非常重視有益治道,其對《詩經》的論述最能體現這種有益治道的認識傾向。葉適認為《詩經》由于包含了周人的“治道”,才能流傳千年而不衰:
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于與天地同德者,蓋已教之詩,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矣。……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葉適認為通過《詩》的渲染和陶冶,可以使天下人性情歸于“中正平和”“是故古之圣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葉適認為后世論詩作詩者,應當以有益治道為指導,他在《跋劉克遜詩》一文中曾云:“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成而家益大矣”。強調作詩要以孔子詩教為準則,講求有用于世。試看葉適的下面一段評論:
是故古之圣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大關于政化,下極于鄙俚,其言無不到也。當其抽詞涵意,欲語而未出,發抒情性,言止而不窮,蓋其精之至也。儒家傳統講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葉適“大關于政化,下極于鄙俚”的范圍比朱熹所秉持的“政教人倫”寬泛得多。葉適的“政教觀”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詩教的階級局限和雅正傳統,把正統的人倫教化引向社會下層和社會萬物,使得詩教的影響范圍進一步擴大,群眾基礎也迅速增長,與其經世致用思想相互映襯,互為表里,與朱子所秉持的“風上化下”觀迥異。
朱熹和葉適雖然都承襲了儒家詩教的傳統,把詩教和儒道內容放在相當突顯的位置,但由于對道統本質的認識存在差異,所以就決定了其詩教內容和主旨是不同的。葉適詩論是以客觀物象為哲學基礎,強調詩歌要經世致用,為突出詩歌的實用,葉適甚至批評理學家的言理詩以玩物為道,不切實用“邵雍詩以玩物為道,非是。”而朱子詩論是以“理在事先”為哲學歸結,從“文道一體”的本體論出發,講求“溫柔敦厚”之詩教,秉持“風上化下”的詩教觀,貶黜浮華功利之習氣。
二、詩史觀
南宋后期詩壇存在兩種詩學傾向,既有唐、宋詩之辨,亦有古體、律體之辨。朱熹尊《選》排律,表現出濃厚的厚古薄今的傾向。而葉適卻尊古崇律,表現出古今并重的詩學傾向。下面筆者擬將對這一問題作出縱向的歷史考辨,探尋這一現象背后的緣由。
朱熹曾于《答鞏仲至》一書中提出過古今詩“三變三等”之說,云: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后,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尤未變。至律詩出,而后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朱子認為魏晉以前詩歌法度接續《詩經》而來,是一脈相襲的。而格律化之后,詩歌法度消失殆盡,古素的風貌不復存在,于是在朱子心目中,以《選詩》為代表的漢魏古詩的價值是要遠遠高于律詩的。朱熹為什么如此看重漢魏古詩而貶低律詩呢?這就需要我們聯系朱熹的哲學觀和詩歌價值觀來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首先,這種尊古非今的詩學觀是與朱熹的哲學觀點相關聯的。理氣之辨是宋明理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朱熹秉持“理在事先”的觀點,認為“理”是第一性的,是形而上的,是萬事萬物的規律,而“氣”是形而下的,是第二性的,是組成萬事萬物的材料,“理”生“氣”并寓于“氣”中。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指引下,朱熹自然要追尋事物之“理”而忽略事物之“氣”。魏晉詩歌是古樸的代表,沒有華美的形式和格律,卻有厚實與深邃的內容。如果硬要對應的話,我們可以認為魏晉古詩是“理”的成分多,而律詩是“氣”的成分多。秉持“理在氣先”的朱熹自然會把魏晉詩歌置于律詩之上的。關于詩歌的價值高低的判斷,其曾論曰:
某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在朱子的詩歌觀念中,形式是“氣”的表現,是第二性的,所以藝術上的爭奇斗艷是次要的,言志抒情才是首要的,文辭形式越是精美,詩歌的言志功能就愈低下,詩歌的價值就愈低,詩文在形式上的巧麗是文學在思想和功能上的衰退。至于興起于齊宋,興盛于隋唐律體詩,在朱熹看來已經不復古人之風了,徒具“氣”的形式,不能與漢魏古詩相比肩。但就律詩內部結構來說,朱子認為“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余味也”,稱贊王韋律詩具有古詩傳統,繼承了《詩經》的蕭散之趣。
在朱熹尊古貶律的同時,葉適卻尊古崇律。葉氏作為永嘉學派的領袖人物,時刻強調道統思想,一直以孔子儒學真傳人自居,這使得葉氏的詩論中必然會有某種程度的復古傾向。但與朱子不同的是,葉適在尊古的同時也崇律,這種詩史觀是與葉適的哲學觀表里的。在哲學層面,葉適不認同朱熹等理學家提出的“理在事先”的觀點,認為理非先天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現實的事物之中,認為“物之所在,道則在焉”。對于詩人來說,就是要描摹自然界萬事萬物的本真狀態,從而更好的指導人們認識情和理。秉承這種詩學觀念的葉氏自然要對晚唐那些工于刻畫物象的詩作表露出了贊賞的態度。其于《徐文淵墓志銘》論曰:
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生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蓋風騷之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繇此復行矣”。
葉適把律詩褒揚為風騷之精,認為“四靈”宗唐是唐詩復興的表現。此外,為對抗江西之學,葉適還將唐詩分為“唐人之學”和杜甫兩個傳統,江西詩派宗法杜甫,而四靈則是繼承“唐人之學”,葉適把“四靈”和江西詩派相對峙,其實就是要抬高“四靈”的地位,來抵制江西詩派的影響,扭轉詩壇審美風尚。
圖4給出了所提出算法用于推導電弧滅弧時間的均方根值跟蹤方法,其中rmsvol[j]是每個數據窗口內電壓波形的均方根值。εrms是用于檢測次級電弧滅弧的微分閾值。持續時間閾值和確定值分別是對應的樣本計數器和采樣數,它們表示持續時間來區分次級電弧的完全滅弧和重新沖擊。當前均方根值與先前均方根值在每個時間步長上的差值,即rmsvol[j+1]-rmsvol[j]≥εrms時,持續時間閾值將增加,并且一旦達到確定值,則表示次級滅弧和重合閘命令信號以激發重合閘繼電器。
值得注意的是,葉適與四靈在詩歌理念上確實有一致的地方,但葉適對“四靈”的夸贊和提攜并不等于葉適把晚唐作為自己詩學的歸宿。其實,葉適主要是為對抗江西詩派“篇幅擴大,汗漫廣漠”的詩歌傳統,才推出了篇幅短小,功夫深刻的晚唐體與之對抗。正如程千帆先生所云“作為永嘉學派的宗主,葉適的文學思想無疑對“四靈”有直接的影響,他既反對朱熹貶抑唐詩,又不滿江西詩派只學老杜一家的局限,因而大力肯定四靈的復尊唐體。……所以‘四靈’的出現,實是對江西詩派的反動;但就其思想根源而言,卻又和永嘉學派對抗程朱理學有關聯。”實際上,葉適的詩歌理想不僅止于晚唐,而是上追盛唐,正如永嘉后學吳子良在《荊溪林下偶談》所論曰:“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因此,雖然四靈繼承了晚唐詩歌傳統,但葉適還是對其抱有遺憾的,葉氏知道唐詩的高峰實際上是在盛唐和中唐,中盛唐詩歌才是自己的詩學取向所在。
與哲學思想一致,葉適肯定唐律的審美取向必然與朱熹的審美取向發生沖突。唐律的聲律形式和言志功能在朱熹這里是矛盾的,朱子認為詩歌的文辭形式會妨礙道德內容的抒發,因而對聲律作了否定性的評價。而葉適卻將文辭形式與道德內容分開,從事實上肯定了聲律文辭的獨特價值。
三、風格論
與其理學家溫柔敦厚的理學旨趣相一致,朱熹崇尚平淡雅正的詩歌風格,其平淡之美是理學中清心寡欲的要求,是“有道者對人生、對自然的體悟,其終極會歸于大道,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朱子欣賞有平淡之美的詩人,他贊美韋應物和王維的律詩有“蕭散之趣”,對李白的灑脫俊逸亦贊不絕口“李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就連韓愈詩歌的平淡自然之處,朱熹也贊賞有加“韓詩平易。孟郊吃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朱熹喜歡自然自在,不刻意為之的詩作,他欣賞陶淵明的那一份自然形成的悠然平淡,“陶淵明詩平淡處于自然”,“陶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
朱熹不僅要求詩歌具有平淡的風格之美,而且還要求詩歌在平淡之下要有雅正之義,要符合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觀。朱熹在《楚辭集注·序》中認為“其辭旨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對屈原激烈抒發情感的方式并不認同。他接著說:“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常了。”又評白居易《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云,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這些論述都表明朱熹主張詩歌風格應符合儒家溫柔敦厚之旨,不應作激烈之情感。
平淡雅正之風除了與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相符合以外,也是扭轉當時詩風的一味良藥。朱子曾云“古人之詩,本豈有意于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咸苦澀,則見其淡耳”標舉平淡之風明顯具有針對江西詩派反動之風的意味。朱熹對自然平淡之風的欣賞溢于言表,他曾云“自有詩之初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出無不出此。”此論簡直把淡雅之風抬高的無以復加的地位了。朱子不僅在理論上為其搖旗吶喊,在實際創作中更是身體力行,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為理學家中為數不多的文學家,錢穆先生曾對朱熹的平淡詩風做過總結,曰:“北宋如邵康節,明代如陳白沙,皆好詩,然皆不脫理學氣。陽明亦能詩,而才情奔放,亦朱子所謂今人之詩也。惟朱子詩淵源《選》學,雅淡和平,從容中道,不失馳驅。……亦當在《文苑傳》中占一席位”,錢穆此論中肯恰當,實至名歸。
實際上,崇尚平淡貫穿于整個宋代詩壇,葉適也不例外。在詩歌理想風格上,葉適把陶謝奉為圭臬:
蓋自風雅騷人之后,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盡棄眾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擬可到。
獨淵明、蘇州,縱極力仿像,終不近似。……天籟自鳴,不待雕琢,證此地位,則其不然。同朱熹一樣,葉適欣賞余味無窮,語工意新的自然平淡之作。這既是對江西詩派反動詩風的回應,也是自己“中和”審美趣味的映射“是故古之圣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更是對《詩經》和孔門詩教的推崇。
葉適曾對“四靈”中徐道輝的詩歌提出過批評“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他認為能從淺近平淡的語言中得到雋永的意蘊的詩歌才是優秀的詩作,這樣的詩作即其所謂的“情瘦意潤”,達到看似平淡實則意味深遠境界。為了實現這種美學倡導,他要求詩人在寫詩之前要一番斟酌、鍛煉以及吟詠的功夫,這種斟酌功夫近似于晚唐詩人苦吟之功,這也就不難解釋葉適為何要贊賞賈島、孟郊了。雖然是苦吟,但葉適也要求詩歌不能露出斧鑿的痕跡,就如“盤摺生語,有若天設”一般。在《跋劉克遜詩》中,葉適論曰:“……克遜既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閑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既是稱贊克遜之人,也是對“怪偉伏平易”詩風的認同,在不露斧鑿的雕琢中,閑遠沖淡的高遠情趣展露無余。
朱熹的審美情趣與葉適明顯存在差異,朱子認為平淡詩風是詩人虛空之心的自然外露,不是刻意為之的平淡,而是淵明“質而實綺”之平淡。而葉適雖也主平淡之美,但卻對“怪偉伏平易”平淡之美也表現出贊賞的態度,兩者異同,顯而易見。
通過對朱、葉詩論的全面比較,我們對南宋詩壇出現的朱、葉詩歌理論異同現象也就不難解釋了。朱熹以“文道一體”為導向,以漢魏古詩為鵠的,追求溫柔敦厚的平淡之美,而葉適高舉“經世致用”的大旗,以唐律為法,取徑較寬,形成了宗唐詩派獨有的文學審美傾向。這兩種詩歌審美傾向有力的重塑了南宋中后期宋詩的審美格局。
注釋:
[1]黃宗羲:《水心學案·按語》,《黃宗羲全集》第五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6頁。
[2](宋)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頁。
[3](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39頁。
[4][10]洪柏昭,王景霓,蔣述卓等著:《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82頁,第871頁。
[5][8][9][24][25](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77~1278頁,第956頁,第4028頁,第256頁,第243頁。
[6]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4頁。
[7][39]錢穆:《朱子新學案》,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第1700頁,第1714頁。
[11][31][32][33][34][37][38]吳文治:《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133頁,第6113頁,第6110~6111頁,第3324頁,第4008頁,第3348頁,第3340頁。
[12][13][14][15][16][17][22]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 702頁,第 254頁,第 735~738頁,第739頁,第740頁,第759~760頁,第706頁。
[18][19][20][26][40][41][42][43]葉適:《水心文集卷二十二》,《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 613頁,第215~216頁,第656頁,第410頁,第55頁,第215~216頁,第613頁,第613頁。
[21]葉適:《水心別集》卷五《進卷·詩》。
[23]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496頁。
[27]程千帆:《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8頁。
[28]吳子良:《四靈詩·荊溪林下偶談卷四》,四庫全書本。
[29]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81頁。
[30][35][36]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325頁,第2070頁,第3323頁。
〔責任編輯 李 弢〕
The comparison of Zhuxi and Yeshi's poetic theory
Xu Guang
Although Zhu Xi and Ye Shi are bearers of confucion culture,they have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on the" DAO",which cause their differences in poetic theory.Zhu Xi advocates that poem teaching should be"gentleness and sincerity",also emphasizes the testimonies,still pursuits the"insipid proctive",aswell as idolizes ancient-verse and criticizes regular-verse from the un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morality.However,Ye Shi holds the view of"equal emphasis on both moral education and artistic expression"poetry theory and idolizes ancient-verse.But he respects regular-verse and pursuits the aesthetic taste of natural flat poems.
Zhu Xi;Ye Shi;poetry teaching;natural flat poems
許光(1987~ ),男,安徽省滁州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2011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