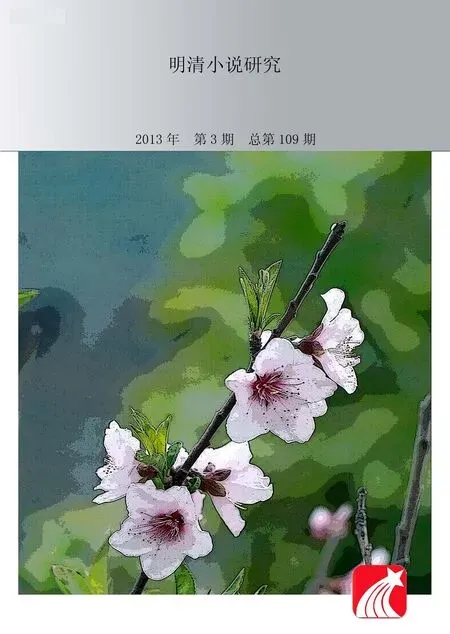《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綜論
· ·
晚明以迄民國,總共有六人次對(duì)《金瓶梅》作有評(píng)點(diǎn):其一是竄入《金瓶梅詞話》正文中的批語,其二是繡像本《金瓶梅》上的評(píng)點(diǎn),其三是張竹坡的評(píng)點(diǎn),其四是文龍的評(píng)點(diǎn),其五是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藏《新刻繡像批評(píng)金瓶梅》(以下簡(jiǎn)稱繡乙本)墨批,其六是徐州市圖書館藏《第一奇書》康熙乙亥本上的墨批。在張竹坡評(píng)點(diǎn)《金瓶梅》之前,僅有竄入《金瓶梅詞話》正文中的批語(參見劉輝《文龍及其批評(píng)〈金瓶梅〉》,載其《〈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和繡像本《金瓶梅》上的評(píng)點(diǎn),而前者極為稀少簡(jiǎn)疏,可忽略不計(jì)。
其繡像本《金瓶梅》上的評(píng)點(diǎn),僅眉批、夾批兩種形式,據(jù)劉輝、吳敢輯校本《會(huì)評(píng)會(huì)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版)統(tǒng)計(jì),計(jì)有眉批1442條、夾批1195條,總2637條,二萬余言。
這次評(píng)點(diǎn)很像是一個(gè)閱讀記錄,時(shí)讀時(shí)批,即興而為,隨意點(diǎn)撥,沒有統(tǒng)一的籌劃,以致各回評(píng)點(diǎn)條數(shù)眾寡懸殊(第七十五回最多,有眉批44條、夾批36條,總80條;第四十四回最少,僅有夾批2條)。另外,一個(gè)字的夾批比例較高。自然也有點(diǎn)睛恰當(dāng)之處,如第一回“西門慶熱結(jié)十兄弟,武二郎冷遇親哥嫂”寫應(yīng)伯爵來找西門慶敘說武松打虎之事,書中寫道:“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成?’伯爵不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著。’”在此處,繡乙本夾批曰“妙”。應(yīng)伯爵混窮到西門慶家打秋風(fēng),又不好意思直說,西門慶則有意捉弄,明知故問,而應(yīng)伯爵機(jī)敏閃躲,設(shè)局猜謎,雖尷尬而解嘲,此一“妙”字,既有西門慶、應(yīng)伯爵問答之妙,亦有《金瓶梅》作者描寫之妙,點(diǎn)睛可謂得體。但可批可不批之處所在盡多,如第二回“俏潘娘簾下勾情,老王婆茶坊說技”,寫武大郎聽武松話早早收攤關(guān)門守家,惹得潘金蓮罵街:“日頭在半天里,便把牢門關(guān)了……也不怕別人笑恥!”而“武大道:‘由他笑也罷……’”,繡乙本于此處夾批曰“是”,便無關(guān)痛癢。
然這次評(píng)點(diǎn)雖為讀書筆記,其能夠起到導(dǎo)讀作用,亦不容置疑。譬如小說立意的提醒,如全書起首說到“酒色財(cái)氣”:“假如一個(gè)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那討余錢沽酒?(繡乙本夾批:酒因財(cái)缺)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云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夠與人爭(zhēng)氣?(繡乙本夾批:氣以財(cái)弱)……到得那有錢時(shí)節(jié),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繡乙本夾批:酒需財(cái)美),真?zhèn)€瓊漿玉液,不數(shù)那琥珀杯流;要斗氣(繡乙本夾批:氣用財(cái)伸),錢可通神,果然是頤指氣使。”可謂一路導(dǎo)引,循序漸進(jìn)。又如藝術(shù)手法的點(diǎn)撥,其“伏脈”二字夾批,自在前述“酒色財(cái)氣”議論隨后點(diǎn)出之后,全書隨處可見。如第一回引出主人公西門慶起始,即在其十兄弟之一卜志道死后,以“伏脈”二字點(diǎn)明此乃昭示西門慶死后之筆,緊接著又在以花子虛填補(bǔ)十兄弟空缺處一次、兄弟主仆提到李瓶兒時(shí)二次、描寫玉皇廟掛像時(shí)一次、敘述潘金蓮出身時(shí)一次,繡乙本一連六處夾批“伏脈”,真是生怕讀者看書不細(xì),辜負(fù)了作者苦心。
關(guān)于評(píng)點(diǎn)者為何方人士,學(xué)術(shù)界眾說紛紜,有李漁(劉輝、吳敢、胡文彬、沈新林等持此觀點(diǎn))、馮夢(mèng)龍(魏子云、黃霖、朱傳譽(yù)等持此觀點(diǎn))、沈德符(魏子云)、謝肇淛(王汝梅)等,亦有認(rèn)為評(píng)點(diǎn)人與改寫人(詞話本在前繡像本在后論者)為一人者,但不管為誰人所評(píng),也不管評(píng)點(diǎn)者與改寫者是否一人,其評(píng)點(diǎn)中的不少觀點(diǎn),均足資存鑒。
首先,評(píng)點(diǎn)對(duì)《金瓶梅》主旨的把握比較準(zhǔn)確。其第一段評(píng)點(diǎn),即為放在全書起首的眉批,在繡像本所有版本(以下僅稱繡像本)中均為:“一部炎涼景況,盡在此數(shù)語中。”這里所說的“此數(shù)語”是一首詩,曰:“豪華去后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舞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絕、咽、沉、滅,豪華不再,簫箏不響,雄劍無威,寶琴零落,一副破敗景況,而且是絕的是華,咽的是樂,沉的是劍,滅的是寶,兩相對(duì)照,炎涼立現(xiàn)。
此詩后面,緊接著便是關(guān)于酒色財(cái)氣的議論,內(nèi)中有如此一段言論:“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見得堆金積玉,是棺材內(nèi)帶不去的瓦礫泥沙;貫朽粟紅,是皮囊內(nèi)裝不盡的臭淤糞土;高堂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錦衣繡襖,狐服貂裘,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即如那妖姬艷女,獻(xiàn)媚工妍,看得破的,卻如交鋒陣上將軍叱咤獻(xiàn)威風(fēng);朱唇皓齒,掩袖回眸,懂得來時(shí),便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增惡態(tài)。羅襪一彎,金蓮三寸,是砌墳時(shí)破土的鍬鋤;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在這段言論上面,繡像本有眉批曰:“說得世情冰冷,須從蒲團(tuán)面壁十年才辨。”
“世情”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美學(xué)的基本理論范疇,在中國古代小說評(píng)點(diǎn)中,這是第一次提及。后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以《金瓶梅》為例,對(duì)“世情書”界出定義,引發(fā)出迄今風(fēng)起云涌、數(shù)以千計(jì)的“世(人)情小說”研究成果。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者并不是偶然使用“世情”概念,而是隨著評(píng)點(diǎn)的逐回進(jìn)行,反復(fù)多次出現(xiàn)。如第二十回“傻幫閑趨奉鬧華筵,癡子弟爭(zhēng)鋒毀花院”寫李桂姐被西門慶包養(yǎng)后又偷去接客,于是西門慶帶領(lǐng)奴仆打鬧麗春院,繡像本于此眉批曰:“此書妙在處處破敗,寫出世情之假。”
第九十一回“孟玉樓愛嫁李衙內(nèi),李衙內(nèi)怒打玉簪兒”內(nèi)有這樣一段文字:“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dāng)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cái)好色,奸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yǎng)漢的養(yǎng)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零挦了。常言三十年遠(yuǎn)報(bào),而今眼下就報(bào)了。”這段文字上面繡像本亦有眉批曰:“此一段是作書大意!”
這一類議論,在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中,俯拾皆是。這說明評(píng)點(diǎn)者獨(dú)具慧眼,一語破的,充分肯定了《金瓶梅》描寫現(xiàn)實(shí)、暴露黑暗、揭示人生、警戒世情的意義。
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中更多的是關(guān)于人物形象與寫作手法的議論。譬如潘金蓮,第一回介紹其出身寫至“做張做致,喬模喬樣”時(shí),繡乙本夾批曰“一生伎倆”。綜觀《金瓶梅》里的潘金蓮,與《水滸傳》里的潘金蓮,其最大不同之處,即行為模式的變化。《水滸傳》里的潘金蓮是在尋求般配的情侶(只不過后來為人算計(jì)誤入歧途方才性質(zhì)改變而已),而《金瓶梅》里的潘金蓮是在爭(zhēng)寵求歡(至少是被娶入西門大院以后是如此,而《金瓶梅》方由此才書歸正傳,此前的潘金蓮還帶有《水滸傳》的濃重痕跡)。具備資質(zhì)的潘金蓮,因?yàn)樯矸莸拖拢瑢で笄閭H仍然要積極主動(dòng),所以《水滸傳》主要描寫其投懷送抱。而做了五娘、變成主子、有了身份的潘金蓮,尋歡作樂成為其生活主體。只是西門大院群芳爭(zhēng)艷,尤其是李瓶兒加入西門慶妻妾行列以后,這個(gè)各方面都不弱于她而財(cái)力、性情超過她的六娘,更成為她的天敵。要享受西門慶的寵愛,要保持尊寵第一的位置,不使用手段,不嘩眾取寵,甚至不心狠手辣,便有可能前功盡棄。而潘金蓮固寵的基礎(chǔ)就是“做張做致,喬模喬樣”,并且非常及時(shí)得體。
第二十七回“李瓶兒私語翡翠軒,潘金蓮醉鬧葡萄架”回首寫潘金蓮摘與不摘、戴與不戴、送與不送瑞香花,這樣一件細(xì)小之事,潘金蓮與西門慶幾番口舌,來回折騰,打情罵俏,可謂極盡“做張做致,喬模喬樣”之能事,此處繡像本有眉批曰:“金蓮之麗情嬌致,愈出愈奇,真可謂一種風(fēng)流千種態(tài),使人玩之不能釋手,掩卷不能去心!”潘金蓮正是靠這類伎倆,用漂亮女人的百種模樣、風(fēng)流女子的千般媚態(tài)、穎慧妻妾的萬類矯情,讓西門慶愛不釋手。因此,潘金蓮知道西門慶支使她離開以便與李瓶兒幽會(huì),便“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回來悄悄躡足,走到翡翠軒槅子外潛聽”。她聽到西門慶說愛李瓶兒的屁股白,已是妒火中燒,當(dāng)?shù)弥钇績簯言校穷A(yù)感到危機(jī)。所以等孟玉樓來到,西門慶要用肥皂洗臉時(shí),她有了發(fā)泄的機(jī)會(huì):“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股還白!”繡乙本于此處夾批道:“尖甚。”潘金蓮猶不盡意,當(dāng)西門慶、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人在翡翠軒吃酒作樂,孟玉樓問她為何只坐涼墩兒時(shí),她說:“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小說接著繼續(xù)寫道:“潘金蓮不住在席上之呷冰水,或吃生果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里沒閑事,怕甚么冷糕么?’羞的李瓶兒在旁,臉上紅一塊白一塊。”此處繡像本有眉批曰:“字字道破,不管瓶兒羞死,俏心毒口,可愛,可畏!”“毒口”用“俏心”說出,“可畏”與“可愛”相伴,表面是美女,內(nèi)心是毒蛇,這就是潘金蓮,排異爭(zhēng)寵、拿人做大、固寵得趣,這就是“做張做致,喬模喬樣”,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者可謂深得《金瓶梅》之三昧!
關(guān)于《金瓶梅》的寫作技巧,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者非常欣賞其藝術(shù),為之總結(jié)歸納出一系列手法,如“閑處入情”法(第二回)、“躲閃法”(第二十一回)、“文章捷收法”(第五十七回)、“綿里裹針”法(第十回)等。評(píng)點(diǎn)者特別賞識(shí)小說的“針線”,如第一回在作者詳細(xì)介紹西門慶身世處,繡像本有眉批曰:“好針線!”為什么是“好針線”?原來洋洋灑灑一部書,均圍繞西門慶而作編排——縱便西門慶死后的二三十回,其人物、情節(jié)亦基本在西門慶生前鋪墊完備——而西門慶在全書中展示出來的所有能耐、行徑,均在開篇第一回伏設(shè)齊整。此亦即前文提到的“伏脈”。這里僅是一段總的針線埋伏,其后行文所至,則一路點(diǎn)明其針線細(xì)密之例證。如第一回寫西門慶看見武松打虎游街,小說寫道:“西門慶看了,咬著指頭道:‘你說這等一個(gè)人,若沒有千百斤水牛般氣力,怎能夠動(dòng)他一動(dòng)兒?’”繡像本于此眉批曰:“伏數(shù)語,便挑動(dòng)酒樓之避,一針不漏。”再如第二回寫潘金蓮掉落窗竿打中西門慶,西門慶先欲惱怒、轉(zhuǎn)而驚艷、繼而賣乖、臨去顧盼這一路白描,卻被賣茶王婆看見,繡乙本于此夾批曰:“千古奇緣,不意更有奇人作合。”繡像本在西門慶臨去頻頻回眸處眉批曰:“傳神在阿堵中!”又如第二十七回寫西門慶與潘金蓮淫樂戲語,繡像本眉批曰:“數(shù)語,金蓮雖若戲說,西門雖若戲應(yīng),然一腔愛惱,自針針相對(duì),冷冷叫破。畫龍點(diǎn)睛之妙。”
對(duì)《金瓶梅》的語言風(fēng)格特點(diǎn),評(píng)點(diǎn)者也有準(zhǔn)確的把握。如第二十八回寫潘金蓮要西門慶辨認(rèn)宋蕙蓮的鞋,西門慶佯裝不知,潘金蓮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著我,黃貓黑尾,你干的好繭兒!來旺兒媳婦子的一只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里拜帖匣子內(nèi),攪著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著。甚么稀罕物件,也不當(dāng)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繡像本于此眉批曰:“只是家常口頭語,說來偏妙。”又如第五十一回寫來寶要改去東京公干,到韓道國家相約揚(yáng)州見面之處,韓道國的妻子王六兒置辦酒菜與來寶餞行,因向其丈夫說道:“你好老實(shí)!桌兒不穩(wěn),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像沒事的人兒一般。”此處繡像本有眉批曰:“此家常閑話,似無深意,然非老婆作主人家,決無此語。”《金瓶梅》以明代口語為主要語匯寫成,是中國第一部當(dāng)代口語白話長篇小說,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者感同身受,將這一語言特點(diǎn)隨處評(píng)議。
盡管這次評(píng)點(diǎn)有如上述不少可足稱道之處,但本次評(píng)點(diǎn)只是一個(gè)簡(jiǎn)明的讀書筆記,審美觀照不足,條分縷析欠缺,諸多理論范疇尚未涉及,披沙揀金尤感粗糙,還算不上真正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綜觀中國古代小說的評(píng)點(diǎn)歷程,固然宋元間劉辰翁評(píng)點(diǎn)《世說新語》早己開其先河,但直至晚明,方才隨著白話小說經(jīng)典的風(fēng)起云涌與文學(xué)評(píng)點(diǎn)的廣泛應(yīng)用而形成氣候。萬歷三十八年(1610)容與堂刊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評(píng)忠義水滸傳》與萬歷三十九年(1611)前后袁無涯刊一百二十回本《出像評(píng)點(diǎn)忠義水滸全傳》,不論其評(píng)點(diǎn)人是李贄還是葉晝或是其他人,其使用回末總評(píng)的形式,已是黃紙黑字,不容置疑。而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僅為眉批、夾批而未使用回評(píng),似可說明其評(píng)點(diǎn)時(shí)間在此之前,至少也要在金圣嘆評(píng)點(diǎn)《水滸傳》與毛倫、毛宗崗父子評(píng)點(diǎn)《三國演義》之前(金批《水滸》與毛批《三國》均以回評(píng)為主體)。如此則詞話本《金瓶梅》與繡像本《金瓶梅》成書與刊刻孰早孰晚,都有了可資參考的新的佐證,但這已超出本文范圍,此不贅言。
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作為最早一次《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繡像本的評(píng)點(diǎn)為其后張竹坡的評(píng)點(diǎn),不僅開啟了端緒,而且規(guī)整了方向。像《金瓶梅》的出現(xiàn)預(yù)示著中國古代長篇世情小說黃金時(shí)代即將到來一樣,繡像本的評(píng)點(diǎn)也預(yù)告了《金瓶梅》的經(jīng)典評(píng)點(diǎn)不久就要橫空出世!
康熙三十四年(1695)正月,張竹坡26歲,“旬有余日”(《張氏族譜·仲兄竹坡傳》),完成了對(duì)《金瓶梅》的評(píng)點(diǎn)。張竹坡評(píng)點(diǎn)《金瓶梅》的文字,總計(jì)約十幾萬字。其形式大致為書首專論,回首總評(píng),和文間夾批、眉批、圈點(diǎn)等三大類。屬于專論的,就有《竹坡閑話》、《金瓶梅寓意說》、《苦孝說》、《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冷熱金針》、《批評(píng)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雜錄小引》等十幾篇之多。明清小說評(píng)點(diǎn)中使用專論的形式,始于張竹坡。中國小說理論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組織結(jié)構(gòu)體系。從文學(xué)欣賞方面說,張竹坡的各篇專論以及一百零八條《讀法》,是《金瓶梅》全書的閱讀指導(dǎo)大綱;而回評(píng)與句批則是該回與該段的賞析示范。
張竹坡的《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或概括論述,或具體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畫龍點(diǎn)睛,對(duì)這部小說作了全面、系統(tǒng)、細(xì)微、深刻的評(píng)介,涉及題材、情節(jié)、結(jié)構(gòu)、語言、思想內(nèi)容、人物形象、藝術(shù)特點(diǎn)、創(chuàng)作方法等各個(gè)方面,其最有價(jià)值者為:
第一,系統(tǒng)提出“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給《金瓶梅》以合法的社會(huì)地位,使其得以廣泛流傳。張竹坡認(rèn)為《金瓶梅》亦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他說:“今夫《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褰褰》、《風(fēng)雨》、《萚兮》、《子衿》諸詩細(xì)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為懲勸之韋弦,反以為行樂之符節(jié),所以目為淫書。不知淫者自見其為淫耳”(《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他在《讀法·五十三》中也說:“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所以他要“急欲批之請(qǐng)教”,以“憫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第一奇書非淫書論》)。經(jīng)過他鞭辟入里的分析,雖然不能從官方的禁令中,但是從人們的觀念上,將《金瓶梅》解放了出來。《金瓶梅》的刻板發(fā)行,在張竹坡評(píng)點(diǎn)之前,只有萬歷丁巳本與所謂崇禎本;在張竹坡評(píng)點(diǎn)之后,卻出現(xiàn)了十幾種刊本。帶有張竹坡評(píng)語的《第一奇書》,成為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金瓶梅》,這不能不說是張竹坡評(píng)點(diǎn)《金瓶梅》的功績。
第二,指出《金瓶梅》“獨(dú)罪財(cái)色”,是泄憤之作,具體肯定了這部小說的思想性、傾向性。眾所周知,《金瓶梅》描寫了西門慶一家暴發(fā)與衰落的過程。張竹坡分析了該書“因一人寫及全縣”,由“一家”而及“天下國家”的寫作方法,認(rèn)為通過對(duì)西門慶的揭露,暴露了整個(gè)社會(huì)的問題。他說:“《金瓶梅》因西門慶一分人家,寫好幾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應(yīng)伯爵一家,周守備一家,何千戶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東京不算,夥計(jì)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算,凡這幾家,大約清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讀法·八十四》)這就是魯迅說的“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中國小說史略》)。所以他認(rèn)為:“讀《金瓶》必須列寶劍于右,或可劃空泄憤。”(《讀法·九十五》)不僅如此,張竹坡進(jìn)一步將小說中的人和事放到冷、熱、真、假的關(guān)系中考察,他在《竹坡閑話》中說:“將富貴而假者可真,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熱也,熱則無不真。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于此。……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說明他認(rèn)識(shí)到,《金瓶梅》并及揭露到人心世情、社會(huì)風(fēng)尚、道德觀念等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讀法·八十三》:“《金瓶》是兩半截書,上半截?zé)幔掳虢乩洌簧习霟嶂杏欣洌掳肜渲杏袩帷!睆堉衿掳训谝换匚淖志蜌w結(jié)為“熱結(jié)”、“冷遇”,并說:“《金瓶》以冷熱二字開講,抑孰不知此二字,為一部之金鑰乎?”(《冷熱金針》)他的冷熱說就是:“其起頭熱得可笑,后文一冷便冷到徹底,再不能熱也。”(《讀法·八十七》)
第三,緊緊把握住《金瓶梅》的美學(xué)風(fēng)貌,以“市井文字”概括其藝術(shù)特色,從小說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這部小說在中國文學(xué)史中的地位。《讀法·八十》:“《金瓶梅》倘他當(dāng)日發(fā)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金瓶梅》以前的中國長篇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寫的是歷史、英雄、神魔,著墨最多的是正面人物的刻畫與傳奇經(jīng)歷的描述。《金瓶梅》則不然,他的主要人物都是反面角色,他的情節(jié)多系家庭日常瑣事。不同的社會(huì)生活面,不同的人物形象群,必然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文學(xué)風(fēng)貌。張竹坡看到了這種不同,并且超越前人,從理論上準(zhǔn)確地給予了總結(jié)。“西門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奸險(xiǎn)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癡人,春梅是狂人,敬濟(jì)是浮浪小人,嬌兒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蓮是不識(shí)高低的人,如意兒是頂缺之人。若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與李桂姐輩一流,總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皆是沒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皆是枉為人也”(《讀法·三十二》)。《金瓶梅》寫的就是這些反面角色,這些反面角色又多是市井中人,寫這些人物的文字,張竹坡批道:“直是一派地獄文字。”(第五回回評(píng))小說寫的不是才子佳人、英雄俠女,所以不能用“韻筆”寫成“花嬌月媚”文字;小說寫的是奸夫淫婦、土豪惡仆、幫閑娼妓這些市井小人,所以只能用俗筆寫成“市井的文字”。
中國古代小說批評(píng),到明末清初形成氣候,金圣嘆、毛綸毛宗崗父子、張竹坡等都出現(xiàn)在這一時(shí)期,可謂空前絕后。毛綸、毛宗崗父子的《三國演義》評(píng)點(diǎn)側(cè)重于思想內(nèi)容分析,表現(xiàn)了封建正統(tǒng)觀念與儒家民本思想,間或論及小說藝術(shù),所概括的名目,多玄虛莫定,無所適從。金圣嘆的《水滸傳》評(píng)點(diǎn),雖也沿用文選的一些術(shù)語,不少地方牽強(qiáng)附會(huì),但藝術(shù)評(píng)論分量顯著增多,其“靈心妙舌,開后人無限眼界,無限文心”(馮鎮(zhèn)巒《讀聊齋雜說》)。
張竹坡的《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方式方法雖多淵源于毛氏父子、金圣嘆,其藝術(shù)評(píng)點(diǎn),至少有三點(diǎn)是他首創(chuàng):其一,書首專論,中國小說理論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組織結(jié)構(gòu)體系。其二,新立了不少名目,總結(jié)了因《金瓶梅》出現(xiàn)所豐富了的小說藝術(shù)。其三,緊緊把握《金瓶梅》的美學(xué)風(fēng)貌,以“市井文字”總括其成,在中國小說批評(píng)史上因此高枝獨(dú)占。特別是第三點(diǎn),前張竹坡的中國小說理論家均未如此入眼落筆。
《金瓶梅》的產(chǎn)生,使中國小說取材、構(gòu)思、開路、謀篇擴(kuò)及社會(huì)整個(gè)領(lǐng)域,寫生活,寫現(xiàn)實(shí),寫家庭,寫社會(huì)眾生相,成為小說家的基本思路,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shí)代。張竹坡“市井文字”說的提出,使中國小說理論擺脫了雕章琢句、隨文立論的八股模式,全書立論,總體涵蓋,顯示了大家氣度,奠定了中國古代小說美學(xué)的基本支柱。
第四,全面細(xì)微地點(diǎn)撥《金瓶梅》的章法技法,形成系統(tǒng)的《金瓶梅》藝術(shù)論。張竹坡的《金瓶梅》藝術(shù)論,總結(jié)出三四十種名目,歸納起來,約可區(qū)分為以下三類:
一是大處著眼,總體立論。“《水滸傳》圣嘆批處,大抵皆腹中小批居多。予書刊數(shù)十回后,或以此為言。予笑曰:《水滸》是現(xiàn)成大段畢具的文字,如一百八人各有一傳,雖有穿插,實(shí)次第分明,故圣嘆止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隱大段精采于瑣碎之中,止分別字句,細(xì)心者皆可為,而反失其大段精采也”(《第一奇書凡例》)。張竹坡不囿前法,別具只眼,提綱挈領(lǐng),總攬全書,落筆不俗。
二是把握人物,尋繹規(guī)律。張竹坡的《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用筆最多的是人物塑造。《金瓶梅》注重人物性格刻畫,張竹坡很好地總結(jié)了小說這一方面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特別抓住人物個(gè)性的展現(xiàn),對(duì)《金瓶梅》的創(chuàng)作方法作了一些規(guī)律性的概括,如他的“犯筆”說:“《金瓶梅》妙在于善用犯筆而不犯也。如寫一伯爵,更寫一希大,然畢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談吐,一絲不紊;寫一金蓮,更寫一瓶兒,可謂犯矣,然又始終聚散,其言語舉動(dòng)又各各不紊一絲;寫一王六兒,偏又寫一賁四嫂;寫一李桂姐,偏又寫一吳銀姐、鄭月兒;寫一王婆,偏又寫一薛媒婆、一馮媽媽、一文嫂兒、一陶媒婆;寫一薛姑子,偏又寫一王姑子、劉姑子;諸如此類,皆妙在特特犯手,卻又各各一款,絕不相同也。”(《讀法·四十五》)小說是怎樣做到“用犯筆而不犯”的呢?張竹坡說:“《金瓶梅》于西門慶不作一文筆,于月娘不作一顯筆,于玉樓則純用俏筆,于金蓮不作一鈍筆,于瓶兒不作一深筆,于春梅純用傲筆,于敬濟(jì)不作一韻筆,于大姐不作一秀筆,于伯爵不作一呆筆,于玳安不作一蠢筆,此所以各各皆到也。”(《讀法·四十六》)
三是隨文點(diǎn)撥,因故立目。張竹坡為《金瓶梅》的寫作手法所立的名目,還有如“兩對(duì)法”、“節(jié)節(jié)露破綻處”、“草蛇灰線法”、“對(duì)鎖法”、“開缺候官法”、“十成補(bǔ)足法”、“烘云托月法”、“反射法”、“趁窩和泥處”、“襯疊法”、“旁敲側(cè)擊法”、“長蛇陣法”、“十二分滿足法”、“連環(huán)鈕扣法”等,雖然沒有跳出明清評(píng)點(diǎn)派的窠臼,不免瑣屑龐雜,其具體闡述,自有真知灼見。如第十三回回評(píng):“寫瓶兒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蓮口中,再用手卷一影,金蓮看手卷效尤一影,總是不用正筆,純用烘云托月之法。”此類點(diǎn)撥,隨文皆是,用張竹坡的話說是“《金瓶梅》一書,于作文之法,無所不備”(《讀法·五十》)。
橫空出世的明代長篇白話小說《金瓶梅》,破天荒第一次打破帝王將相、英雄豪杰、妖魔神怪為主體的敘事內(nèi)容,以家庭為社會(huì)單元,以百姓為描摹對(duì)象,極盡渲染之能事,從平常中見真奇,被譽(yù)為明代社會(huì)的眾生相、世情圖與百科全書。得益于此,《金瓶梅》的評(píng)點(diǎn)評(píng)議也水漲船高,為有識(shí)者所重視。而張竹坡的評(píng)點(diǎn),在《金瓶梅》古代所有的評(píng)點(diǎn)評(píng)議中最為出色。隨著世界思想解放的浩蕩潮流,隨著新時(shí)期中國百家爭(zhēng)鳴的和煦春風(fēng),隨著新學(xué)科、新課題的叢出不窮,《金瓶梅》研究被尊為“金學(xué)”,中國小說理論史、中國評(píng)點(diǎn)文學(xué)史被視為熱點(diǎn),張竹坡研究不但成為金學(xué),而且成為中國小說理論史、中國評(píng)點(diǎn)文學(xué)史、中國文學(xué)批評(píng)史的重要分支。
在后張竹坡的《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中,繡乙本墨批計(jì)有眉批3條、夾批14條總17條,未知何人所評(píng),亦未知評(píng)于何時(shí),觀其文意,與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無異。關(guān)于徐州市圖書館藏《第一奇書》康熙乙亥本上的墨批,據(jù)其封面墨署“壬子暮春彭門鈍叟訂補(bǔ)”,墨批人即此彭門鈍叟。而其所謂“壬子”,乃乾隆五十七年(1792)、道光二年(1852)、民國元年(1912)三者之一,后二個(gè)年份的可能性要大一點(diǎn)。封面墨署后鈐一陽文印“皇漢遺民”,顯系彭門鈍叟之另一號(hào)稱。這一墨批計(jì)有眉批13條、夾批48條總61條,觀其文意,與張竹坡評(píng)點(diǎn)相仿佛,而尤偏袒潘金蓮。如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歡,鬧茶坊鄆哥義憤”在描寫潘金蓮的一首【沈醉東風(fēng)】后墨批曰:“一路寫來,寫出婦人美媚嬌容,足以動(dòng)人魂魄,真是個(gè)天生尤物。”又如第七十九回“西門慶貪欲喪命,吳月娘喪偶生兒”在潘金蓮騎在西門慶病體上淫欲處,墨批曰:“婦人美哉,西門休矣。此全怪月娘,西門已得病而猶聽在潘金蓮房內(nèi),可謂月娘該死。不然,恐猶有救也。”
其尤當(dāng)評(píng)議者,乃文龍對(duì)《金瓶梅》的評(píng)點(diǎn)。自光緒五年(1879)5月10日至光緒八年(1882)立冬前兩日,文龍于光緒五年、六年、八年前后三次評(píng)點(diǎn)《金瓶梅》,用的底本都是在茲堂本《第一奇書》。文龍的評(píng)點(diǎn)有回評(píng)(缺第15、16、22、38、81、82六回)、眉批(2條)、夾批(46條)三種形式,約五六萬言。
文龍?jiān)u點(diǎn)的是《金瓶梅》小說,并非完全針對(duì)張竹坡的評(píng)點(diǎn),但張?jiān)u近在手頭,觀點(diǎn)相左之時(shí),當(dāng)然要彈出不同的音符。在其評(píng)點(diǎn)中,文龍24次點(diǎn)到“批書者”、“批者”、“閱者”,均指張竹坡。對(duì)于吳月娘、孟玉樓、龐春梅三人的評(píng)價(jià),是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對(duì)于張竹坡貶吳揚(yáng)孟安龐的觀點(diǎn),文龍大不以為然,其24處批評(píng)有21處為此。如第九十一回回評(píng)曰:“獨(dú)是西門慶群妾中,李瓶兒先死無論矣,李嬌兒歸娼而嫁張二官,潘金蓮?fù)等硕仃惤?jīng)濟(jì),孫雪娥盜財(cái)而隨來旺兒,龐春梅勾奸而嫁周守備;此一回孟玉樓又大大方方、從從容容而嫁李衙內(nèi)矣。固無一人心中、目中、口中有一西門慶,亦如批書者處處只貶吳月娘,而竟忘此書原為西門慶報(bào)應(yīng)而作也,亦可謂不求之本矣。”
文龍對(duì)張竹坡《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的批評(píng),屬于文學(xué)批評(píng)方法論范疇。文龍認(rèn)為文學(xué)批評(píng)應(yīng)“就時(shí)論事,就事論人,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第三十二回回評(píng))。所謂情理,文龍說:“理之當(dāng)然,勢(shì)之必然,事之常然,情之宜然。”(第八十五回回評(píng))而不能“有成見而無定見,存愛惡而不酌情理”(第三十二回回評(píng))。文龍批評(píng)張竹坡沒有做到這一點(diǎn),而是“愛其人其人無一非,惡其人其人無一是”(同上)。
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文龍對(duì)張竹坡的批評(píng)并非全無道理,有的還相當(dāng)準(zhǔn)確和深刻。不過,文龍畢竟只是閑中消遣,只是對(duì)作品的賞析,而沒有像張竹坡那樣有意識(shí)地全方位進(jìn)行文學(xué)評(píng)論,因而沒能站在小說理論發(fā)展的高度去認(rèn)識(shí)張竹坡,便不能不失之狹隘。
但文龍所作的也是較為系統(tǒng)的獨(dú)立的《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有必要對(duì)其作出全面的評(píng)介。首先,推進(jìn)了《金瓶梅》非淫書這一重要命題。其第十三回回評(píng)曰:“皆謂此書為淫書,誠然,而又不然也。但觀其事,只男女茍合四字而已。此等事處處有之,時(shí)時(shí)有之,彼花街柳巷中,個(gè)個(gè)皆潘金蓮也,人人皆西門慶也。不為說破,各人心里明白。一經(jīng)指出,閱歷深者曰:果有此事;見識(shí)淺者曰:竟有此事。……若能高一層著眼,深一層存心,遠(yuǎn)一層設(shè)想,世果有西門慶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惡之不暇,陽世之官府,將以斬立決待其人;陰間之閻羅,將以十八層置其人。世并無西門慶其人乎?舉凡富貴有類乎西門,清閑有類乎西門,遭逢有類乎西門,皆當(dāng)恐懼之不暇,防閑之不暇,一失足則殺其身,一縱意則絕其后。……然則書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書又何嘗淫乎?”
其次,確定《金瓶梅》的立意在“警世”(第十七回回評(píng)),故所寫皆“性賭命換”(第二十九回回評(píng))之徒,“書中無一中上人物”(第三十一回回評(píng)),而是“一個(gè)喪心病狂、任情縱欲匹夫,遇見一群寡廉鮮恥、賣俏迎奸婦女,又有邪財(cái)以濟(jì)其惡,宵小以成其惡,于是無所不為,膽愈放而愈大,心益迷而益昏,勢(shì)愈盛而愈張,罪益積而益重。聞之者切齒,見之者怒發(fā)。……人不得而誅之,雷將從而劈之矣;法不得而加之,鬼將從而啖之矣”(第十八回回評(píng))。
復(fù)次,認(rèn)為《金瓶梅》對(duì)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極為成功。如其第七十九回回評(píng)曰:“《水滸傳》出,西門慶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門慶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時(shí),遂無人不有一西門慶在目中、意中焉。其為人不足道也,其事跡不足傳也,而其名遂與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為誰,而但知為西門慶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為誰,而但知為西門慶批也。西門慶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罵。世界上恒河沙數(shù)之人,皆不知其為誰,反不如西門慶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門慶未死之時(shí)便該死,既死之后轉(zhuǎn)不死,西門慶亦幸矣哉!”
文龍?jiān)u點(diǎn)《金瓶梅》的突出特點(diǎn),就是格外留意人物形象,并且往往以對(duì)比手法分類描述。如其第二十三回回評(píng)云:“讀《水滸傳》者皆欲作宋江,讀《紅樓夢(mèng)》者皆欲作寶玉,讀《金瓶梅》者亦愿作西門慶乎?曰:愿而不敢也。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恐武大郎案犯也,恐花子虛鬼來也。既不敢又何以愿之乎?曰:若潘金蓮之風(fēng)流,李瓶兒之柔媚,與龐春梅之俏麗,得此三人,與共朝夕,豈非人生一快事乎?然則不敢非不敢也,但愿樂其樂而不愿受其禍耳。”又如其第九十七回回評(píng)云:“故金之淫以蕩,瓶之淫以柔,梅之淫以縱,嬌兒不能入其黨,玉樓亦不可入其黨,雪娥不配入其黨,此三人故淫婦中之翹楚者也,李瓶兒死于色昏,潘金蓮死于色殺,龐春梅死于色脫。好色者其鑒諸!貪淫者其鑒諸!”
另外,文龍?jiān)u點(diǎn)《金瓶梅》時(shí),不時(shí)結(jié)合時(shí)政,也是有為而作。如其第二十三回回評(píng)云:“夫蕙蓮亦何足怪哉!吾甚怪夫今之所謂士大夫者,或十年窗下,或數(shù)載勞中,或報(bào)效情殷,捐輸踴躍,一旦冷銅在手,上憲垂青,立刻氣象全非,精神頓長,揚(yáng)威躍武,眇視同僚,吹毛求疵,指駁前任,幾若十手十目不足畏,三千大千不能容,當(dāng)興之利不知興,應(yīng)去之弊不能去……此皆蕙蓮之流也。”又如其第四十九回回評(píng)云:“請(qǐng)巡撫,遇胡僧,皆西門慶平生極得意之事。雖告之曰請(qǐng)須破財(cái),遇則喪命,不顧也。亦匪獨(dú)西門慶為然,遍天下皆是也。官場(chǎng)之中,得大憲多與一言,多看一眼,便欣欣然有喜色,向人樂道之;而況入其門,登其堂,分庭抗禮,共席同杯,其榮幸何如?千金又何足惜哉!流俗之輩,買春藥以媚內(nèi),服補(bǔ)藥而宿娼,正自有人,姑且勿論。即現(xiàn)在鴉片煙一物,食之者多,大半皆以其壯陽助氣,可以久戰(zhàn)而食之。于是花街柳巷,無一不預(yù)備此物,而況一厘可御十女,一粒可盡五更,有不以為異寶奇珍者哉!”
在《金瓶梅》古代評(píng)點(diǎn)史上,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者、張竹坡、文龍,前后紹繼,彼此觀照,相互依連,貫穿有清一朝,形成筆架式三座高峰。繡像本評(píng)點(diǎn)拈出世情,規(guī)理路數(shù),為《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高格立標(biāo);文龍?jiān)u點(diǎn)引申發(fā)揚(yáng),撥亂反正,為《金瓶梅》評(píng)點(diǎn)補(bǔ)訂收結(jié);而尤其是張竹坡評(píng)點(diǎn),繼金圣嘆、毛宗崗之后,成為中國古代小說評(píng)點(diǎn)最具成效的代表,開啟了近代小說理論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