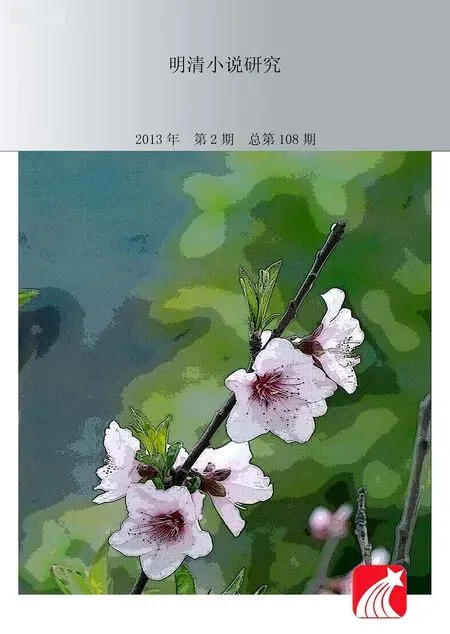明代小說家清溪道人考辨
··
在明清文學(xué)史上,白話小說異軍突起,成為這一時(shí)期的代表性文學(xué)樣式。不過,這只是我們對(duì)白話小說在明清文學(xué)或整個(gè)古代文學(xué)中的地位所作的歷史考量,而在明清時(shí)期,當(dāng)時(shí)的士民一般僅將其作為茶余飯后、夜雨孤航時(shí)的消遣,至多也不過是將其看作稍有裨益的“史余”、“小道”。也就是說,與“正統(tǒng)”的詩文相比,小說特別是白話小說的創(chuàng)作仍然是為大多數(shù)人所不屑的,這也就造成了小說的作者們常用別號(hào)、筆名來題署的現(xiàn)象。而這種現(xiàn)象帶來的后果是:許多小說作品問世后不久(即使流傳很廣),其作者的身份即已成為謎團(tuán)(如《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世易時(shí)移,后人更是難以理清頭緒,而這也成為深入研究一些古代小說作品的主要瓶頸。一方面是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舉世公認(rèn)的繁難度,是應(yīng)擱置不提還是該迎難而上呢?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這兩種意見都不乏有支持者,而筆者更傾向于后者:束之高閣畢竟不是解決問題之道,在古代小說研究創(chuàng)新越來越難的情況下,與其在文本的闡釋上修修補(bǔ)補(bǔ)(更不用說大量的重復(fù)研究),倒不如在小說作者的考證上取得點(diǎn)滴的進(jìn)步。雖然一些小說作者的身份連同時(shí)代的人都不甚了了,但與古人相比,現(xiàn)今的研究者也有自己的優(yōu)勢(shì),那就是接觸到的文獻(xiàn)資料如各種野史筆記、地方史志、墓志家譜等要比古人豐富的多。所以說,如果我們能夠持續(xù)的關(guān)注,逐步的積累,在某一個(gè)點(diǎn)上取得突破完全是有可能的。本文即對(duì)明代中后期的《禪真逸史》、《禪真后史》、《掃魅敦倫東度記》(以下簡(jiǎn)稱《東度記》)三部小說的作者——清溪道人的身份作一簡(jiǎn)要辨析,廓清前人的一些模糊認(rèn)識(shí),以期拋磚引玉,促進(jìn)該問題的最終解決。
《禪真逸史》、《禪真后史》、《東度記》三部小說雖不能與《水滸傳》、《西游記》等相提并論,但也各有特色,如《禪真逸史》、《禪真后史》中既有戰(zhàn)爭(zhēng)場(chǎng)面,又有神魔故事,還有許多細(xì)致的世情描寫,也就是借鑒、融合了歷史小說、神魔小說、世情小說等不同小說類型的要素和描寫手法,這體現(xiàn)了小說作者試圖創(chuàng)新的努力,同時(shí)也代表了明代中后期長篇白話小說的演變趨勢(shì)。而《東度記》塑造了許多意念化的妖魔鬼怪,用來象征酒、色、財(cái)、氣、貪、嗔、癡等,即“借酒色財(cái)氣逞邪弄怪之談。一魅恣,則以一倫掃”(《東度記序》),將乏味的說教形象化、故事化,也是很有特點(diǎn)的一部作品。當(dāng)然,這三部小說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guān)注還有另外一個(gè)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三部小說的作者為同一人——清溪道人方汝浩。如果真是這樣,那他無疑會(huì)是古代小說史上一位不可忽視的高產(chǎn)通俗小說作家。那么,《禪真逸史》、《禪真后史》、《東度記》三部小說的作者真的會(huì)是同一個(gè)人嗎?下面我們就依據(jù)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對(duì)這一問題進(jìn)行具體的分析。
一、《禪真逸史》、《禪真后史》作者清溪道人身份辨析
《禪真逸史》現(xiàn)存版本較多(最早為明天啟年間刊本),皆題“清溪道人編次”,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禪真逸史》的作者即為清溪道人。至于清溪道人的真實(shí)身份,據(jù)日本慈眼堂所藏明刊本《禪真逸史》較其他版本所多出的自序的題署“瀔水方汝浩清溪道人識(shí)”可知,清溪道人姓方,名汝浩,“瀔水”人。方汝浩于史無載,但此題署卻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價(jià)值的作者身份信息。
從“瀔水方汝浩清溪道人”的題署來看,雖不排除瀔水為寄籍的可能性,但在沒有確切證據(jù)的情況下,將其理解為里籍應(yīng)是比較合乎情理的解釋,這也符合古代文人一般的署名格式和習(xí)慣。那么,瀔水到底指稱何地呢?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據(jù)題署判定方汝浩為洛陽人,即認(rèn)為瀔水是河南洛陽的代稱。以后的學(xué)者多承襲了此種論斷,使其成為了學(xué)界的主流觀點(diǎn)。但也有學(xué)者持不同意見,如戴不凡《小說見聞錄》“頗疑‘瀔’系‘瀫’之誤;瀫水,衢江也”,即認(rèn)為方汝浩是浙江蘭溪一帶人。對(duì)于此種觀點(diǎn)響應(yīng)者不多,因?yàn)榇鞑环蚕壬皇翘岢隽艘环N可能性,并未進(jìn)行深入的解釋,所以后來的研究者多認(rèn)為此種看法是推測(cè)之詞,事實(shí)根據(jù)不足。但筆者以為,戴不凡先生對(duì)于“瀔水”的意見或許更接近于事實(shí):
首先,從民眾對(duì)瀔水和瀫水的熟悉程度來看,用瀫水指稱籍貫的可能性更大。“濲,《廣韻》、《集韻》并古祿切,音谷。水名,在河內(nèi)。顏延之詩:伊瀔絕津濟(jì)。或作榖。”瀔水“即今河南洛河支流澗水及其上游澠池縣南澠水”。但在古代典籍中“瀔水”一般寫為穀水、谷水,如《國語·周語下》“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將毀王宮”中之“穀”即指穀水。而“瀔水”這一寫法的使用率并不高,具體的例證除上面引文中提及的顏延之《北使洛》詩外,其他基本上只見于歷代字典韻書的收錄(這些字典韻書在舉用字實(shí)例時(shí),也只是提到了顏延之的《北使洛》詩)。“瀫,《集韻》胡谷切,音縠。水聲。又水名。《廣輿記》:瀫水在金華府城南,西至蘭溪界。《集韻》或作縠。”瀫水,唐代時(shí)改稱衢江。但在唐以后瀫水的名稱并未在日常生活中消失,而是基本成為了蘭溪的別名:“(蘭溪)其源有二……二水合而匯于蘭陰,類羅瀫文,又名瀫水。”在蘭溪縣更有許多與瀫水相關(guān)的風(fēng)物,如晚唐既已聞名的蘭溪名酒瀫溪春,明代在蘭溪縣設(shè)置的驛站——瀫水驛,而時(shí)至今日,蘭溪八景中仍有被稱作“瀫紋漾月”的景觀。翻閱古代典籍,瀫水之名也屢見不鮮,特別是頻繁出現(xiàn)在江浙文人的詩文集中,如著名的蘭溪籍文人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類稿》中就出現(xiàn)了幾十處“瀫水”、“瀫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浙江之“瀫水”的認(rèn)知度要遠(yuǎn)高于河南之“瀔水”。而在表征籍貫(或居住地)時(shí),古人的確常常使用地名的古稱、別稱或代稱,但這些稱謂基本上都是人們所熟知的,如將南京稱為金陵、江寧,將杭州稱為武林、錢塘、西湖等等。所以說,將本已非常知名的古都洛陽用生僻的瀔水來指稱恐不符合情理。而瀫水與蘭溪的密切程度高,并且瀫水這一名稱一直沒有脫離現(xiàn)實(shí),因此用瀫水指稱浙江蘭溪要比用瀔水指稱河南洛陽更加可信。

基于以上分析,《禪真逸史》“瀔水方汝浩清溪道人”之“瀔水”為“瀫水”之誤并非無稽之談,并且這種錯(cuò)誤可能并不是由筆誤所造成的,而是當(dāng)時(shí)許多人就是以瀔水來指稱蘭溪的。因?yàn)樗麄兏揪蜎]有意識(shí)到“瀔水”與“瀫水”的區(qū)別(這既包括字形上的差異,也包括它們所指的河流的具體位置)。
《禪真后史》“與前史源流相接”(《禪真后史源流》),“皆所以補(bǔ)《逸史》未備”(《禪真后史序》)。也就說,《禪真后史》在故事、立意上皆承接《禪真逸史》而來,我們可以將二者稱作是“禪真”系列小說。明崇禎二年崢霄館本《禪真后史》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最早刊本,題“清溪道人編次,沖和居士評(píng)校”。翠云閣主人陸云龍?jiān)凇缎颉分幸仓赋觯骸叭舴蚯逑廊嗽囂嵝延谇懊炎髂宪囍福幻豌Q錘于后勁,允為暗室之燈。”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禪真后史》的作者清溪道人與《禪真逸史》的作者為同一人即方汝浩。



二、《東度記》作者清溪道人身份辨析
《東度記》全名《掃魅敦倫東度記》,又稱《續(xù)正道書東游記》。現(xiàn)存最早版本是明崇禎八年萬卷樓刊本,題“滎陽清溪道人著 華山九九老人述”。那么,這位滎陽清溪道人又是誰呢?說到這里,我們不得不提到明代萬歷年間萬卷樓所刊出的另一部小說——《三教開迷歸正演義》(以下簡(jiǎn)稱《三教開迷》)。《三教開迷》署“九華潘鏡若編次”,前有《三教開迷序》末署“九華山士潘鏡若撰”,可知九華山士是潘鏡若的別號(hào)。《三教開迷序》中寫到:“蓋予先嚴(yán)清溪道人喜談釋,嘗與名淄辯難。”而《東度記》中華山九九老人所作的《引》開頭即說:“清溪道人,下愚先人,喜談禪而好行善事。”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兩處對(duì)清溪道人的描述基本一致:喜談佛理,并且都將清溪道人稱為先人,這樣看來,《三教開迷序》中提到的清溪道人與《東度記引》中的清溪道人即《東度記》作者應(yīng)為同一人。要想證明這一結(jié)論,關(guān)鍵點(diǎn)在于確認(rèn)《三教開迷》中的九華山士與《東度記》中的華山九九老人為同一人。對(duì)此,除上面提到的《東度記引》和《三教開迷序》中的表述外,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來證明:
首先,從二者的籍貫來考察。《東度記》題“滎陽清溪道人著”,即作者為滎陽(鄭州)人。華山九九老人稱清溪道人為先人,則華山九九老人也應(yīng)是滎陽人。《三教開迷》雖為小說作品,但“事跡若虛若實(shí),人名或真或假”(《三教開迷演義跋》)。如第二回中就有一個(gè)以作者為原型的人物(下文將會(huì)詳細(xì)說明),第七十三回作者則對(duì)自己的家世進(jìn)行了介紹:“卻說濟(jì)南府商河縣有個(gè)滎陽潘氏,隨大明皇祖征進(jìn)金陵,家世居京,代傳一個(gè)仙游了的清溪道士,乃九華山士的先人”(此處有眉批曰:“借假寫真”)。據(jù)此,九華山士祖籍也是滎陽。
其次,從二者的身份地位來考察。《東度記引》后鈐有“解元之章”的印章,表明華山九九老人曾經(jīng)科舉考取了解元。《三教開迷》第二回中有如此介紹:“這士人年近五旬,乃都城內(nèi)一個(gè)武解元,姓潘,別號(hào)鏡若。”(可見鏡若也非真名,而是別號(hào)。)這與《三教開迷序》中“壯而孔門未遂,首為鷹揚(yáng),拔淹蹇長安四十余載”的描述也是一致的。因此,九華山士也為解元身份。



綜上所述,《東度記》的作者清溪道人,姓潘,祖籍滎陽,世居南京。其子潘鏡若,著有《三教開迷歸正演義》。
三、結(jié)語:兩位清溪道人之關(guān)系辨析
前文我們已經(jīng)說明《禪真逸史》作者清溪道人和《禪真后史》作者清溪道人為同一人,此清溪道人(以下簡(jiǎn)稱《禪真》作者)與《東度記》作者清溪道人有沒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呢?其實(shí),通過以上的分析答案已經(jīng)非常明顯,但由于對(duì)此的誤解長期、普遍地存在,所以我們下面再具體說明一下。


綜上,就目前的文獻(xiàn)資料來看,我們?cè)谔接憽抖U真》與《東度記》的作者時(shí)還是應(yīng)分別予以討論:《禪真逸史》、《禪真后史》的作者清溪道人即方汝浩,應(yīng)為浙江蘭溪人;《東度記》的作者清溪道人為滎陽(鄭州)潘氏,世居南京。
注
:① 如果具體分析不同的小說作品,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還有很多,如避禍心態(tài)、社會(huì)風(fēng)氣影響等,對(duì)此前人論述較多,本文就不再詳細(xì)介紹。
② 本文所引《禪真逸史》、《禪真后史》、《東度記》、《三教開迷歸正演義》之序、跋、引以及正文等皆據(jù)《古本小說集成》所收版本,除有必要,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③ 此版本的題署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頁)。慈眼堂藏明刊本《禪真逸史》為孫楷第先生所親見,但現(xiàn)在已不知所蹤。
④ 戴不凡《小說見聞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頁。
⑤⑧ 《增訂篆字殿版康熙字典》巳集上,廣益書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版,第41、44頁。
⑥ 魏嵩山《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7頁。
⑦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92頁。
⑨ [明]薛應(yīng)旂《浙江通志》,臺(tái)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頁。據(jù)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
⑩ 本文所依據(jù)的《少室山房類稿》是1924年胡宗楙輯《續(xù)金華叢書》本,此版本據(jù)明萬歷間刊本刊刻,題“瀫水胡應(yīng)麟明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