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綴那一方坍塌的文化天空(上)
盛和煜
現在戲劇、影視的創作狀態很令人擔憂,包括我們湖南的狀態也是如此。湖南人原來那種敢為天下先,不服輸、不信邪的精神,在戲劇、影視創作這一塊,反而成了我們的精神包袱:不服輸、不信邪變成了不服行[hán],坐井觀天、夜郎自大,總以為湖南人了不起,倔強。這個倔強用得不是地方,變成了倔強地不承認別人的長處。這從我們舞臺劇的創作中可以看出來,近兩屆湖南藝術節,比較慚愧,一、二名都被我拿了,上屆藝術節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我的劇本;這屆藝術節第一名是我學生的劇本。我在戲劇、影視界都是邊緣人物,特別在家鄉,多少年沒有回湖南參加戲劇活動了。拿到這第一第二名,說心里話我并不高興。為什么呢?這說明我們湖南的戲劇創作進步不大。如果在座的能像我們當年“谷雨社”那樣,我就高興了。我多少次給家鄉的領導、同行說外面的進步,可惜聽者寥寥。再一個,影視創作也好,戲劇創作也好,有很多錯誤的方向和令人擔憂的問題,有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前不久有記者采訪張黎導演,他有一句話,“要求接地氣是可恥的”,說是從我這里來的。事實上,因為要求接地氣,有了多少庸俗的作品。這些作品開始還有一點現實主義的東西,后來完全成了偽現實主義的東西。以接地氣來掩蓋他的庸俗、空乏蒼白和令人發指的胡編亂造。如果真要接地氣,就應該是敢于直面社會、直面人生、直面苦難。我人微言輕,但每次談創作我都愿意來,我希望把自己的觀念提供給大家。我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就要有責任、有使命感、有這么一點很微弱的聲音發出來。我希望我的作品,成為一顆顆色彩斑斕的女媧補天的小石子,來補綴我們中華民族已經坍塌了的那方文化天空。這是我的夢想。
在我們湖南,曾經有原來的“谷雨社”、戲劇湘軍。當時中國有三個戲劇窩子:四川自貢、福建莆田、湖南常德,那時候我經常說,單打獨斗,我們還沒有特別有影響力的劇作家,但是拿出我們整體實力,我們一個常德地區就有200多個編劇,48個專業編劇,多少人都能夠寫,打團體賽我們能打冠軍。我剛才講了我的幾個擔憂:一個,是所謂的接地氣;一個,是偽現實主義;再一個,是過度娛樂化。我覺得對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走向,對我們青少年的培養,嚴重地來說是個戕害。所以我希望發出我的這種聲音,我們要寫真正的黃鐘大呂式的(小橋流水也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帶著時代精神的又真正能夠感染人的電視劇、舞臺劇去影響大家,奮起抵抗卷地而來的庸俗化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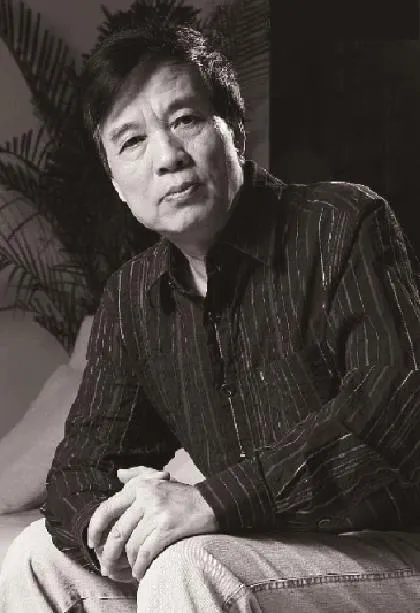
盛和煜近照/本人提供
下面講我的“老三篇”。所謂“老三篇”,是我從事創作這么多年來的三點心得。我為什么不說是經驗而說是心得呢?因為經驗是成熟的,而一旦成熟,離腐朽也就不遠了。我當“知青”的時候當了公社文化輔導員,等于群藝館的編外工作人員。第一次我寫了一個叫作《搬家》的戲。內容是要修水庫了,要把這個地方搬遷,大家克服了自己的一些自私的思想、服從大局,最后就搬了。我準備把它寫成一個小話劇。寫了“搬家”這題目,然后寫場景,那時候我們沒有受到這么多的技術教育,就開始想怎么寫場景。我想寫一張桌子,這張桌子上面貼的是舊報紙,我就想寫出那種感覺來,但怎么都寫不出那種感覺。還有,這桌子是放在舞臺的左側還是右側,靠觀眾近一點還是遠一點,我在心目中有那么一個位置,但是我始終表達不出來。就為這個桌子怎么擺,我用文字要怎么表現,三天沒有寫出一個字。所以說創作,先天應該有些東西,創作天賦是第一重要的,但是后天的訓練,技術性的問題必須要學習。它和寫詩不同,所以作為編劇要有一定的生活閱歷。這是我一個感覺。后來這個戲還是寫成了。寫成以后,就到縣里去匯演,當時老師講評這次匯演的劇本時,我坐在后面,好想聽到老師能提到我的名字,但老師整個就沒提我的。我以為我寫的好得不得了,但是老師卻對我那劇本根本沒有印象。所以我太理解我們作為文學青年往上努力時的那種心態,直到今天還有這種心理。
好了,現在就開始我的“老三篇”,題目還是那樣,《藝術創作中的逆向思維》,分為一個導言和三個部分:第一、主題的提煉,第二、人物陌生化,第三、獨特的敘述框架。
導言兩句話,第一句話:一切紀錄都是為打破而存在的。跳高的紀錄,劉翔跨欄的紀錄,這些紀錄是為打破而存在的。當初劉翔打破紀錄是多么高興,但是劉翔的紀錄還是被古巴小將打破了,所以一切紀錄都是為打破而存在的。我當初調到湖南省湘劇院,準備了兩個題材,一個就是準備用來寫廣播劇的《屈原》,一個就是《夾山鐘聲》,寫李自成在我家鄉所屬的石門縣夾山寺出家當和尚的故事。考慮了很久,寫《夾山鐘聲》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戲劇結構、內容都比較充實。但是一個朋友對我說,要寫就寫別人沒看到過的,這句話對我意義重大,我決定了寫《屈原》,也就是后來的《山鬼》。創作《山鬼》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正是好戲多得不得了的時候。我把當時最好的劇本都擺在我案頭,很虔誠地學習,懷著崇敬的心情,很仔細地看這些劇本。看著看著就覺得還有些問題,看著看著就覺得我也能寫出來,再看下去就覺得我能寫得比它好。這就是紀錄是可以打破的。我就看著它們、學習它們、然后希望超越它們。就是這樣,如此而已,沒有任何別的東西,但是你學的時候要真地學,不是說一上來就要掀翻它們。好的東西擺在那里是希望你超越它,我創作的時候從來不以任何藍本為我的藍本,我從來不照抄人家的,包括改編都極少。
第二句話,當一項藝術方案出來,百分之六十的人贊成,為時已晚。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要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但是我們的藝術方案拿出來,所有的人都叫好,這個作品的品質就值得懷疑。因為人的個性是有差異的。都說這個不錯時,為時已晚,已經就有很多庸俗的東西在里面了。我的《十二月等郎》寫出來以后,他們拿去評獎。我是第一屆曹禺劇作獎第一名的獲得者,但是后來我老是評不上了,為什么呢?大家平時看慣了兩萬多字的劇本,一看到這八千多字的劇本,他怎么看都覺得有點單薄。
我這兩個(導言的內容)都是解釋逆向思維的,我寫劇本從來不把任何一種成功模式當成我的藍本。這就是逆向思維的導言。逆向思維貫穿在整個創作之中。
現在講第一個問題:主題的提煉。如果用個通俗的說法,我叫它鶴立雞群法。下午講評的時候我會問在座的這幾個劇作者,你們寫的時候,想表現一個什么東西?這是很重要的。比如說,電視劇京漢大鐵路要我寫,江南造船廠要我寫,開灤煤礦、首鋼都要我寫,都是老總們出面,因為寫了《走向共和》,所以他們就讓我寫。我就想,你們要我表現什么東西?葉劍英也要我寫,賀龍元帥也要我寫。就是說,你拿到這個東西的時候,你要問自己。賀龍很傳奇,故事很好聽,為什么不寫?賀龍元帥和葉劍英如果同樣兩部電視劇作品,你要寫的時候,你要表現什么?不是表現他個性的不同、故事的不同,那不是目的,那只是另外講了一個故事。一樣的故事你要提煉出你的主題,你想干嘛?你想表現什么?這主題的提煉就決定了我們拿到一個題材以后這個戲的品質,鶴立雞群,立意很高。取法乎上則得其中,取法乎中則得其下。你的立意高,你的作品才與眾不同。我拿著一個題材,我首先想的就是怎么樣才不重復前人的窠臼,怎樣不同凡響,怎樣就算是在同類題材中也高出人家一籌。一定要有這個想法,否則糊里糊涂,這個故事好聽、人物有味就這樣寫下去,當然這也都重要。我們的文藝概論教導我們主題要多元化,是不錯。文藝概論還教育我們,不要主題先行,主題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只能露出1/7,其余的要深深留在海面以下,都不錯,都是真理。主題要隱蔽好,這都是不錯的。但是在創作的時候,心中沒有個高人一籌的主題和目標,這個不行。
《走向共和》的主題是什么?寫《走向共和》的時候,有關戊戌變法、民國風云這樣的文藝作品從小說到戲劇不勝枚舉。但是我在寫這個的時候,我就要想,我們的主題是什么。他們的主題大多是表現什么袁世凱、什么奸雄或者創業的艱難什么的,不對。我在寫的時候,我和大家商量,主題是什么?我們提煉出:找出路。李鴻章也好,誰誰誰也好,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他們絕對不是什么賣國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出路。洋務派也好,君主立憲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找出路,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沒有誰是天生的賣國賊,沒有誰從娘胎里出來就口含天憲,一貫正確。這是《走向共和》,因為定了這個主題,這也成了它的貫穿行動線,“找出路”貫穿我們這部電視劇的始終。這主題出來了,起點一下就高了。

京劇《梅蘭芳》劇照

湖北花鼓戲《十二月等郎》劇照
再就是,《恰同學少年》,它的主題是什么?《恰同學少年》是歐陽常林臺長的創意,叫我們寫的,為了寫這個才把我從湘劇院調到湖南電視臺去。我最后的主題是為中華崛起而讀書。
京劇《梅蘭芳》是一個著名的劇作家寫的,要我去討論。我本來是不去的,后來他們說過士行去了,我就去了。為什么呢?因為你看每次《劇本》月刊發表作品,總是話劇擺在最前面,你戲曲寫得再好也是擺在第二、第三,話劇寫得再孬,也是頭版頭條。我們國家對話劇、歌劇的重視總比對戲曲高一籌,我就不服這個氣。其實在中國戲曲學院高端演講那次我就說了,“我們戲曲文學是我們母語中的精髓,我們不能這樣糟踐它,不能這樣瞧不起它”。因為過士行兄是話劇大腕,他去了,我也去,我就是為表現自己去的,要讓你們知道戲劇界還有能夠和你們抗衡的人。在座諸位都對京劇劇本發表了一通言辭,好,說到我飯碗里來了,我就接著侃了一通,侃得他們瞠目結舌。由于我這一番耍表現,編劇就落在我頭上了,推都推不掉。我說這劇本的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主題的提煉上。它把梅先生塑造成一個愛國者,塑造成一個政治人物,而且是當時左聯的那種政治人物。它把梅先生完全塑造成一個是三、四十年代的、左聯的、政治的、愛國的人物,我就覺得這主題出現了問題。我覺得梅先生是可以和上天對話的人,他不僅是中華文化,他是人類的文化,要這樣認識這個問題,所以我就提煉這個主題。梅先生是演女人的,女人是什么?不是說女人是水嗎?由此我想到我們中華民族性格。世界上多少彪悍的民族都隨著歷史灰飛煙滅,它們曾經比中華民族強悍得多。中華民族的性格逆來順受,就像水一樣,你打一拳會縮回去,你不打了,他又上來了。上善若水是什么意思,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它藏污納垢,能夠包涵一切、容納一切、最后澄明澄清一切,這才是上善若水,和厚德載物一個意思。我們的大地母親,承載著世界上的一切物品,有惡的、有善的、有好的、有壞的,這才是厚德,才能載物。我就提煉出我們的民族性體現在梅先生身上,他以一個人的抗戰,打敗了整個日本軍國主義,這就是上善若水,這就是主題體現,這就是我在創作之前和創作之中反復考慮的,提煉出來的。提煉出上善若水這個主題,就有別于一切寫梅先生的粉墨春秋的作品,就到達了一個新的境地。張和平局長、陳薪伊導演他們非常高興,在哪個地方都講,都一直對這個主題認可,因為這樣一來就大不一樣了。
《山鬼》大家討論的很多,在座的老朋友們也看過這個戲,都是很贊賞的。《山鬼》演出的時候,很有爭議,甚至爭議到國外去了。在北京首演的時候,影響非常大,丹麥、日本、美國、德國等11個國家的大使館都要票,都沒有票了,組委會臨時調的票,那時候在北京演出,影響也很大。但《山鬼》剛出來的時候,遭到很多人的懷疑,“屈原能這樣寫嗎?”,我說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兩千年集體生存心理的一種表現,屈原的主題今天我自己來說是“人是在不斷追求完美的,唯其追求完美達不到,才不斷地追求”,后來有人解釋說兩種文化沖突,見仁見智,反正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這是山鬼的主題。
《十二月等郎》的主題,這是一個寫農村留守女人的戲,不僅僅是關注農民工,更重要的是關注“千百年來中國女人的等待究竟是為什么?”這個問題,我自己也不能回答,所以這個戲很多人看了以后又感動又惆悵。
《李貞回鄉》的主題是什么?最早的劇本是“反封建”,但是十年以后重新拿出來的時候,就覺得這個主題不對了。我原來的主題是“反封建的戰士最后又被封建所束縛”。后來的主題是“共產黨搞斗爭是為人民謀幸福,而不是為了斗爭人民”,這種主題是需要勇氣的,最后還是被容納了。
在說主題提煉的時候,還有一個最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編劇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者。我們不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回答什么問題。比如股份制改革的時候說股份制好,然后好像這就能夠解決一切,這都是從人家那里批發來的一些觀念。作為編劇,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為什么要從人家那里批發一些觀念來呢?改革開放,鄧小平都要摸著石頭過河,你編劇有那么大的能耐,在你的劇本中提供現成的答案和靈丹妙藥?但是我們很多編劇仍然以為自己在作品中能夠回答或解決我國種種社會問題并且以此自豪,這就有點黑色幽默了。你可以提出問題,一個作品能提出一個問題引人深思、給人啟迪就行了。我們真的不是政治家,政治家解決問題有時候也解決得不盡人意嘛!一個作品最高的、最好的品質就是能夠提出問題。請大家記住,我們不是政治家,我們是思想者。(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