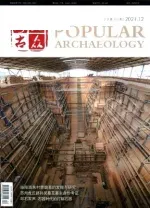“文化”與“自然”存有共同的法則
我們迄今所面對的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自然世界,一個是文化世界。“自然世界”是“上帝”之手創造的,包括人也是“上帝”創造的產物,即人首先是自然之子,而“文化世界”是由人創造的,文化世界實際上是“上帝”之手的延伸,它通過人這種“萬物之靈”的手創造了一個有別于自然世界的人文世界。然而,“自然世界”與“文化世界”真的是完全有別嗎?它們難道真的存在完全不一樣的運行法則嗎?考古學研究告訴我們,不是那樣的,“文化世界”與“自然世界”在常態下有許多本質的相同性,比如:
一、有序性。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呈現出發展的有序性。人類創造的文化也呈現出時間、空間、結構與功能及其動力上的有序性,如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從狩獵采集經濟到農業畜牧經濟再到工業和后工業經濟;從游蕩生活發展到農村定居生活,再到城市生活的誕生;從某種文化的“點”狀起源,到逐步向周邊“面”的擴散;一定的器物造型適應于一定的功能等等。有無數的實例可予證明,而這種“有序性”的背后正是一種邏輯性的存在。
二、遵守美的法則。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動物植物、地形地貌,無不呈現出獨特的美的造型和質感。人類也一樣,幾乎所有的文化創造,大到城市、宮殿、園林、寺廟,小到文具、尺牘、鈕扣、針頭,幾乎都表現出諸如對稱性,具有恰當的結構比例,富有韻律美,色彩是那么的協調等,而在這具象美的背后潛藏的都是對真、對善、對愛的抽象表達。
三、有用性。從科學的角度而言,自然界的一切都具備有用性。人類也一樣,因需求而創造文化,無論是物質的文化,還是非物質的文化,實際都是一種有意義的存在。無用性的文化最終會退出歷史舞臺。
四、規律性。自然規律的普遍存在是科學界的共識。文化也一樣,幾乎所有的文化事象,無論是石器、陶器,還是房屋、都市,無論是文字、繪畫,還是食品、服飾,都遵循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的運動規律。超常規的異態文化事象雖然也會出現,但它不代表文化發展的正常狀態和法度。
五、存在文化創造的多種可能性或多樣性,但“多樣性”和“統一性”的有機結合才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總體特征。在自然界,如果有可能、有必要和條件,物質世界是可以重組的。文化也可作如是觀。迄今為止,盡管人類不同民族的發展過程具有很強烈的統一性,各種文化事象也呈現出某種規定性,但是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從機械化時代到電氣化時代,從自動化時代到信息化時代;或者是從歐洲到亞洲,從非洲到美洲,從草原到平原,從山地到海島;或者是從歐羅巴人種到尼格羅人種,從亞細亞人種到澳洲人種;或者是從社會上層到社會低層,從知識分子到農民工人,甚至社會成員個體之間,“文化”都無不充滿著“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恰恰是人的文化創造存在無限可能性、不確定性及復雜性的實證。然而,這種“多樣性”所反映的“偶然性”相較于“必然性”而言是暫時的,或者說隱藏在“多樣性”背后的“必然性”、“規定性”和“統一性”才是文化發展主導的力量,即“多樣性”和“統一性”的有機結合才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總體特征,這一點也是自然界存在和發展的法則。
六、和諧性。觀察人類300多萬年以來的各種創造,同一文化生命體內的不同文化因素之間,不同文化生命體之間,文化世界與自然世界之間存在著永遠的“和諧要求 ”與“和諧關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只是表現狀態之一,但不能絕對化,對抗、競爭、淘汰不是發展的主要力量,和諧、合作、和合、共生才是世界根本的生存與發展原則。不和諧或“斗爭”的狀態是暫時的,否則系統就會崩潰。歷史上許多文化與自然的不和諧導致“文化共同體”的滅亡,一些文化內部的不和諧也導致其結構的瓦解和重組。可以說,沒有一種不和諧的文明可以長期持續發展,也沒有一種不和諧的“人地關系”可以長期共生。
當然,“文化世界”畢竟是由那些具有高級思維的人類所創造的,它肯定與“自然世界”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包括形態、結構、目的、動力等等,這種“差異性”與兩者內在的“相同性”一樣,都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