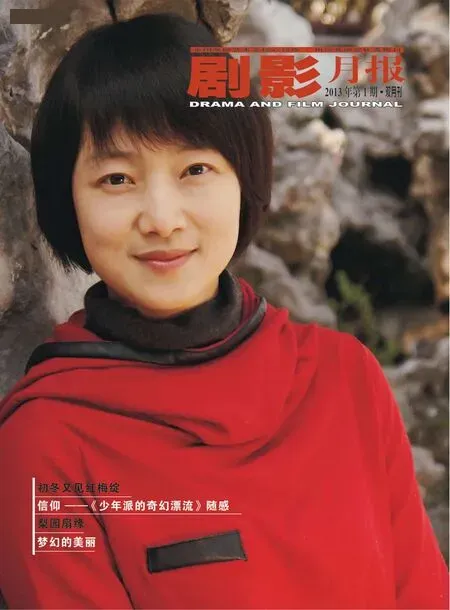柳琴戲原生態的回歸和時代性
■劉敏
柳琴戲原生態的回歸和時代性
■劉敏
一.柳琴戲的原生態
“原生態”是近年來被頻頻使用、炒作的新語匯,大多是指某種藝術初生時的形態,在央視舉辦的原生態民歌大賽中,側重的是民歌原有的聲調旋律和表演形式,而很少對某種民歌原有的生存狀況作深入的探討。我這里所談的是柳琴戲的原生態,則是柳琴戲這一戲曲門類原有的生存狀態。
柳琴戲的前身拉魂腔孕育于清朝康熙至道光年間,流行于蘇、魯、豫、皖接壤區域。它純粹生于農村,是貧困農民上門乞討時敲梆打板的一種說唱,俗稱“唱門子”,后來逐漸衍變為柳葉琴伴奏,融進“軸鼓子”打擊樂器,又發展為歌舞表演形式的“壓花場”,從一人扮演多種角色的“當場變”,到家族戲班,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形成柳琴戲專業戲班。這一、二百年時間,幾乎全是農民創作、農村“跑坡”(即地攤演出)、農閑娛樂。直至建國之后,柳琴戲才發展為打著農村烙印的地方劇種。它所表現的內容,絕大部分是農村生活。這便是柳琴戲的原生態。
世上許多事物的發生、發展、成熟、衰亡的軌跡,似乎都在畫圓,其終點往往和起點復合在一起。柳琴戲一、二百年并未從“農”字脫穎而出,至今依然在它的起點或離起點不遠的地方徘徊。從創作題材到演出市場,依然和農村、農民密不可分。從一九五六年在全國獲大獎的柳琴經典小戲《喝面葉》、七十年代的《大燕和小燕》以及近年來劇團演出場次多的劇目,無一例外都是農民喜聞樂見的反映農村生活題材的作品。
看到這一點,我們便可以認識到柳琴戲和一些地方劇種共同面臨生存危機的根源。離開生養的一方水土,任何藝術之花都會枯萎。柳琴戲離開農村、農民,注定會過早的消亡。
“三下鄉”對柳琴戲來說,決不是去“恩賜”農民,或者說是為農民服務。應該說是柳琴戲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所應有的必然回歸。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在電視等傳媒強烈的沖擊下,在戲曲藝術不甚景氣的今天,我們注重研究柳琴戲原生態的回歸,正是為了給柳琴戲作出準確的市場定位,找回適應其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二.柳琴戲的現代性
原生態的回歸和時代性,似乎二者相悖。其實,在我進入江蘇省柳琴劇團近二十年的實踐中,卻感覺這二者能夠十分和諧的交融起來。
柳琴戲的觀眾80%以上是農民。今天的農民觀眾早已不是解放前一貧如洗的農民,也不是改革開放前沒有解決溫飽的農民。尤其是淮海經濟區比西部地區開發早,這里的農民不但物質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而且具有了現代意識,掌握了大量的現代信息,能夠接受現代的美學新潮。從劇團上演的頗受歡迎的柳琴戲劇目中,我們就不難發現農民觀眾的時代感。
譬如我參加排演的戲曲小品《算卦》,在農村演出的場次最多,農民的喝彩聲最高。《算卦》可謂老而又老的故事,但是由于我們賦予了它強烈的時代性而倍受農民歡迎。一個“看包裝好象是個有錢的富婆”和算卦先生的對白唱腔中,凡是農民觀眾捧腹大笑、拍手叫好的地方,都是充滿了現代生活氣息的地方。算卦先生夸口“蚊子從我面前過,我能算它幾只母來幾只公”,夸口“零八年的奧運會,我早算出比賽地點在北京,今年廣西發大水,洪水沖垮了梧州城,伊拉克絞死了薩達姆,也沒出我神算中……我不算,誰也別想,抓住基地頭目那個拉登……”國事家事天下事,農民觀眾事事通曉,一經我們柳琴戲演員的演繹,頓時心領神會,其樂無窮。這出小戲運用了大量的現代語匯,如:手機、信息、包裝、夜總會、桑拿……等等。引用了大量當今生活的新聞,如:劉翔拿了奧運會冠軍等。農民觀眾也已熟知,且津津樂道。由此,我們大可不必為柳琴戲生態回歸社會遭到拒絕、排斥而憂慮。
農民觀眾在歡迎具有時代性的柳琴戲的同時,也對傳統柳琴戲表現形式的改革逐漸認同。認同原汁原味柳琴戲的,幾乎都是老年觀眾,即使這部分的觀眾的審美情趣在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也發生了變化。如我參加排演的表現計劃生育題材的《爆炸》、新版《喝面葉》等戲,上演幾百場,特別在農村演出時場場爆滿。這些小戲將柳琴、小品、歌舞等有機地貫穿起來,已經不是原汁原味的傳統柳琴戲,但卻被農民觀眾快樂地承受下來。柳琴戲的唱、念、做、打中,傳統注重于唱,以唱腔“拉魂”。如今,在傳統唱腔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優美的旋律,在戲曲舞臺的基礎上,又融進了現代的舞蹈。這些,農民觀眾都十分樂于接受。事實證明,農民觀眾能夠接納新鮮的玩意兒。
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多元化的時代,并存、沖撞、融合、老化、新生,各種藝術也都必然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如果我們的柳琴戲在回歸原生態、回歸生養它的土地時,能夠大膽借鑒現代生活美和力的新創造,吸收激光、電子音樂等新科技手段,以此表現淮海地區農民的新生活、新理念、新追求,表現他們的喜怒哀樂,那么,柳琴戲就會煥發出更強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