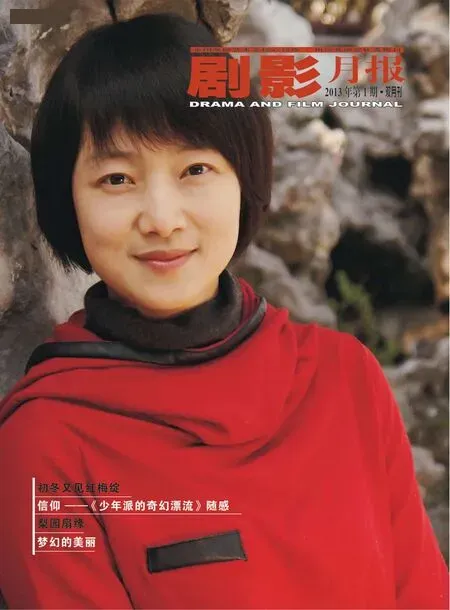書法藝術自覺論
■祁建軍
書法藝術自覺論
■祁建軍
近年來,國學逐漸熱了起來,作為傳統文化奇葩的書法藝術更是如此。不僅各種書法展賽層出不窮,書協會員成千上萬,不同檔次的書法集、論文集鋪天蓋地,不同名目的稱號、頭銜眼花繚亂,培訓雅集此起彼伏,名家大師應接不暇……真是熱鬧非凡。雖然從大眾普及的角度看,這對推廣書法藝術,提高國民素質,繁榮傳統文化的積極功效有目共睹,不容抹殺,但負面影響也隨之愈見明顯。一時書法名家大師滿天飛,至于夠不夠書法家的資格,無人追究,故而利用或借助于對權力的依附和媒體的市場炒作,呈現出“魚龍混雜”、“魚目混珠”共同“繁榮昌盛”的現象。不僅如此,隨著書法市場顯現,書壇官僚氣、江湖氣、市儈氣、名利氣漸成風氣,“泡沫”效應明顯,惟技術主義、形式主義泛濫,文化修養缺乏,人格精神低下,這不僅侵害了書法藝術的健康發展,而且貶損了書法家的高尚稱號,降低了書法的藝術品位,混淆了工藝與藝術的學術界限,誤導了創作和審美的價值取向,讓人們產生嚴重的憂慮和反思。
事實上,書法作為一種點線結合的造型藝術,人們不僅通過寫出好的書法產生一種視覺美,而且還用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給人們提供美的啟迪和享受。在中國傳統藝術當中,沒有哪一種如書法一般對人們提出了如此之高的綜合要求,除了書法的“筆法”、“墨法”、“章法”等技術層面的因素,還對書者個體的性格、人生經驗以及生命感悟,同時還有哲學、美學、文學等與中華文化相關的素養高度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誠如清末民初杰出學者楊守敬所云:習書之道,一須人品高,二須學養富。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學富則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佚等倫者也。人品與學養便成了書法審美中一個重要的準則。故而正確引導書法大眾化的健康發展,亟需增強書法家自我覺醒、自我反省的能力,自覺弘揚傳統人格精神,提高文化修養,主動承擔書家應有的社會責任。
一.自覺汲取傳統精髓,提升文化修養
書法藝術與傳統文化相表里,與中華民族精神成一體。它雖是以筆、墨、紙等為主要工具材料,卻通過漢字書寫以特有的造型符號和筆墨韻律,融入人們對自然、社會、生命的思考,表現出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文化底蘊的一種藝術實踐。歷經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書法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性符號,每個書法筆畫的背后無不蘊藏著深厚的民族文化。
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儒家文化所崇尚的中和之美深深地滋養著書法藝術的發展。《論語》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庸》強調:“不偏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古人認為,中和之書應該做到“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中和的結體與章法要表現出“勢和體均”、“平正安穩”、“四面停勻,八邊具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的藝術效果。概言之,中和對于書法藝術而言就是“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各形式要素之間互有差異卻不相干擾,相互協和卻不雷同,變化與協調這對矛盾法則在這里得到了完美的統一,這就是中和的氣象。唐代書法理論家孫過庭十分推崇中和之美,他在《書譜》中表達了自己崇尚的書法境界:“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王羲之被尊為“書圣”,他的書法被奉為典范,就是因為其書法構思通達精審,心態恬淡平和,創作時雖有情性的抒發,但都能夠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既雄渾又超邁,既剛健又婀娜,既質樸又嫵媚,超妙入神,變化萬方,集眾美于一身,集中體現了中國儒家哲學的“中庸”“中和”的審美內涵。項穆的《書法雅言》更是以中和思想貫穿全篇,并以此作為分析書法現象與評價書家書作的最高標準。在崇尚中和之美的同時,儒家也格外倡導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陽剛之氣,主張和而不同的價值取向等,這些都成為古往今來書法家不懈的精神追求。
道家陰陽之道、虛無之思對書法藝術影響深遠。《周易?系辭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宇宙中兩種最重要的力量,“陽代表陽性,主動、熱、明、干、剛等等,陰代表陰性,被動、冷、暗、濕、柔等等”,陰陽二道互相作用,就會產生宇宙間的一切事物與現象。陰陽規律體現在具體的筆墨形態中便會形成多樣性與和諧性相一致的書法形式美。“主與次”、“正與欹”、“勻與變”、“連與斷”和“逆與順”、“中與側”、“方與圓”、“曲與直”、“肥與瘦”、“疾與澀”等點畫用筆和結體取勢的多樣性就體現了陰陽變化的規律,使人感受到一種深層次的、豐富而多變的美感意趣。在虛無之思方面,《老子》云:“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淮南子》云:“有生于無,實出于虛”。書法藝術中注重對空白的經營,強調在無墨處施展才華,計白當黑,正是道家虛無觀點的具體體現。在顏真卿的《劉中使帖》、宋克的《杜甫壯游詩》、董其昌的《白居易琵琶行》、懷素的《自敘帖》中,虛實相間、黑白對立統一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書法藝術中,一紙之上,著墨處為黑,無墨處為白;有墨處為實,無墨處為虛;有墨處為字,無墨處亦為字;有字處固要,無字處尤要。白為黑之憑,黑為白之藉,黑白之間,相輔相成;虛為實所參,實為虛所映,虛實之際,互為所系,虛無之思被書法藝術中計白當黑之實踐體現得淋漓盡致。
佛法自東漢傳入以來,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影響深廣長遠。佛教認為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一切外相色彩包括書法藝術,不外是心靈的產物,是虛無不實,這樣便進入一種物我一體自由自在的境地。佛教的這種清淡空靈、寧靜超脫精神給書法藝術注入了充滿生機和活潑的內涵。書法是依靠一筆一劃,在有意無意之間,表現藝術這內心秩序,創造獨特意味的藝術。懷素的“飛動狂奔”,貫休的“奇俊超越”,文梵的“冷影清奇”,王棲的“恢詭怪異”,智永的“深沉穩重”,弘一的“圓潤疏淡”,以及歐陽詢的道勁,柳公權的清健,顏真卿的莊嚴,蘇軾的豪放,黃庭堅的素麗,米南宮的飄逸,趙子昂的秀美,朱奇的超然,石清的蒼茫……所有這一切絢麗多采的書法大家之風,并存于佛教藝術圣壇之中,究其根本,正是由于佛教的博大精深與不凡氣宇。
作為中華文化的奇葩,書法蘊含和承載著中華文化的底蘊和精神,體現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展現了東方文化的神韻。如果我們不領悟到書法的這層審美意義,無法進行真正達到更高的書法境界。不相信書法的“書以載道”的藝術屬性,我們也不能在真正意義上“讀”懂傳統文化與書法藝術的深層聯結。學養、胸次是書法家的立身之本,學養比技能更重要。北宋大書法家黃山谷評坐蘇東坡的書法時說:“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胸中有書數千卷,則書不病韻。”東坡有學問,所以書的品格就高。書的品格高下是建立在深厚的學養基礎之上的。功夫在詩外。“去俗唯有讀書”。一個書家不讀書,不做學問,書法境界就不可能高,只能淪為“書匠”而已。故而書家在當下的讀圖時代,只有自覺加強對具有5000年“根”的傳統文化的研習,不斷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才能參透對書法藝術的深刻認識和理解,才能為書法藝術的提高和升華奠定堅定的基礎。
二.自覺加強人格修養,重建當代書法品格
書法其實既有生命,也有情感和品格。徐悲鴻先生曾說書法之美在情在德,在于表現的情感和品德。西漢時揚雄提出:“書,心畫也。”自唐之后,科舉取士,書法也是評定標準之一。這標準既是考測才學,也是甄別性情和人品。清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揚子以書為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
書法是心靈的藝術,是心的軌跡,是心里頭流出來的線條,所以杰出的書法家寫字都不是僅僅用手寫,是同時用心在寫,而且只有他用心在寫,他的書法作品才具有很強的魅力,才會感動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杰出的書法,它和人的精神相通,不僅表達人的一種情感,更表現人的品格。一部中國的書法史就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史,古往今來對王右軍正直高華、顏真卿忠貞愛國、柳公權筆諫皇上、蘇東坡博大深邃、黃道周堅貞不屈、八大山人清高孤絕、弘一法師博愛仁慈的推崇,對秦檜、蔡京的蔑視,清楚地證明我國傳統書法歷來重視“字如其人”,把人品和書品相提并論,恪守人品高、書格自然高的真諦。
千百年來,晉人王羲之的書法,為什么始終都被推為第一?書法理論家金開誠先生曾評曰:“右軍人品高,故書入神品”。孫過庭稱: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櫝仍存……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王羲之的人品,從史料可知:出身望族,草圣有傳,見其氣質高華,不落俗塵;少時假寐避禍,見其聰慧機警;冶城勸謝,見其骨梗耿介;坦腹東床,見其不拘細行;屢征不就、墓誓歸隱,見其志行高潔,不慕榮利;樂志山水,服食優游,見其質樸超邁;書經換鵝,見其純真稚氣,脫略塵俗。王羲之的品格既修齊治平,又超塵脫俗,最終以追求人品的正直和精神高度自由為歸宿。人品高峻至此,書法焉能不妙?
懷素行為放達,飲酒吃肉,結交名士。然而,他酷愛書法,一生勤奮。其草書氣勢磅礴,瘦硬強健,千變萬化,恣肆放達。正所謂其人也放達,其書也放達。若是把懷素的性格和書風放在一起,恐怕世人難以區分哪是懷素的為人,哪是懷素的書法。
顏真卿出身書香世家,為人正直,剛正不阿,一腔忠心,大氣凜然。唐代宗時,李希烈叛亂,皇帝派顏真卿前往勸諭。顏真卿明知必死,依然凜然前往,果被李希烈縊殺。后來,李希烈叛亂被平定后,他的尸骨運回長安,皇帝親自出城迎接靈柩。顏真卿的書法,樸實渾厚,雍容大度,端莊豪邁,恰如其人堂堂正正。《祭侄文稿》追懷、贊頌在安史之亂中以身殉國的侄子顏季明,雖是草稿,但如果不知道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不了解顏真卿的為人,就無法真正意義上理解其藝術價值。由于當時顏真卿心情極度悲憤,情緒已難以控制,《祭侄文稿》渴筆和牽帶的地方歷歷可見,時有涂抹,能讓人通過行筆的過程和筆鋒變換,感到他情真意切,既凝重峻澀,而又神采飛動,筆勢圓潤雄奇,姿態橫生,純以神寫,得自然之妙。元代張敬晏題跋云:“以為告不如書簡,書簡不如起草。蓋以告是官作,雖楷端,終為繩約;書簡出于一時之意興,則頗能放縱矣;而起草又出于無心,是其手心兩忘,真妙見于此也。”顏真卿名垂書法史的還有《多寶塔》和《勤禮碑》等,渾厚剛健,方正莊嚴,元氣大度的字體后面,也無不蘊含著他剛直不阿、一腔正義的人格,所以流傳久遠,為后人追慕。
柳公權雖被唐憲君任命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但怠于朝政的皇上向其問及如何才能將書法發揮得盡善盡美時,他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即寫字,先要握正筆,用筆要訣在心,只有心正了,筆才能正。皇上當即正色改容,知道柳公權是以書法來巧妙地勸誡自己。
明末清初著名書法家傅山為人處世以及作學問,處處表現得孤傲不群,特別是在以寄托胸臆,抒發性情為載體的書法方面,更是把表現自己的人格特征作為主要目的。他對書法的理解首先建立在人格的完善之上,認為人格骨氣是書法格調高低的關鍵。他說:“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因此,他的書法一直秉承正氣,注重個性宣泄。他批評當時追求嫵媚軟俗格調的風氣,強調要從古、拙、奇、樸上著眼。面對趙孟頫、董其昌柔靡之風充斥書壇,傅山為追求民族氣節的人格理想,提出了與之相對的“四寧四毋”: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并把這種創作原則追求了一生,發展到了極致,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地位。這與他后半生誓不與清政府合作一脈相承,顯示出其剛正不阿的民族氣節。
考察古代書論的若干術語,如中和、雍容、敦實、剛直、雄壯、質樸,磊落、放縱、威猛、俊逸、妍美、嫻雅、凝重等,就會發現它們與人格的形容密切相關。在書法的審美理論中最重要的幾對范疇,如神采與形質、風韻與氣勢、法度與姿態,也無不與人格的象征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古人練字其實就是練志,憑借有意味的書寫形式,書寫人生的精神世界,體現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價值追求,反映書家獨特的精神氣質,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在浮躁之風彌漫,道德世風下滑,社會形態發生巨大變化的當下,書家只有注重將德育品行滲透在書法追求的過程中,不斷提煉、豐富和升華自己的修養、品質,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著眼于養浩然正氣,塑高尚品格,做到寫字就是“寫心”、“寫志”,才能創作出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才能在成就書法之路陶冶自身的同時感染后人,激勵書法的繼傳者和受傳者。
總之,中華文化精神和對人格的不懈追求深深地影響著書法藝術的發展。古代書家的顯揚,是得之文化、人格、書藝的整合高度,名家大師的出現都離不開文化和人格的支撐、積淀。我們崇仰有加的書史大家,如顏真卿、蘇東坡、黃庭堅、米芾等皆為政治家、文學家或飽學之士,沒有一個不學無術之輩,沒有一個不是高人雅志。現在書法門檻很低,很多人隨便介入書法,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文化底線,將書法淪為簡單的寫字,這無異于糟蹋書法。書法需要寫字,但寫字并不是書法的全部,它的堂奧很深,不僅需要重視字內功的錘煉,更要強調字外功的儲備和修為,二者的珠聯璧合方為書法的理想境界。透過有意味的藝術形式,書法凝結著的是一個書者學識涵養的反映,是一個書家性格氣質、人格人性的表征,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審美追求與精神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