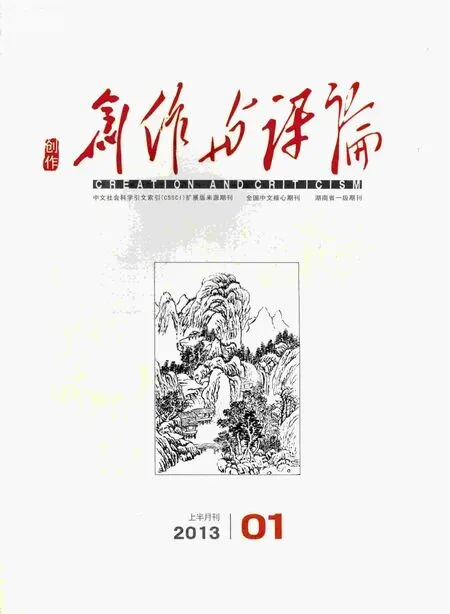重新打開記憶之門——韓少功《日夜書》對知青經驗的反省
○ 劉復生
正如某些理論家所指出的,記憶從來都不是自然的生理過程,它往往是權力運作的結果,同時也可以是自覺的文化實踐。另外,記憶本身就是遺忘,就是一種記憶反對另一種記憶,這是記憶的辯證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知青生活的記憶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遺忘與反遺忘的斗爭,知青文學正是以反遺忘的名義,以個人化的訴苦、悲悼與懺悔,達成了它最初的解放功能。但與此同時,它也建構了一種關于知青的歷史形象和集體話語,強迫性的選擇性記憶使整個記憶運動變成了以個人名義進行的集體情感抒發儀式和觀念實踐。于是,知青記憶慢慢地蛻化為一種主流常識,一種公共化的意識形態,一種抽象的政治結論。
新的記憶之門必須被重新打開,它不僅意味著重新深入到知青生活的最初情境中,去復活那些被意識形態抽象化的具體的鮮活記憶,同時意味著重新建造進入記憶的另外的門戶和門后的路徑。這必須是對記憶的重構或者說重新組織,它既需要發現新的記憶內容,還需要打碎舊的記憶邏輯和記憶模式,掙脫既定的意識形態敘事的征用,讓舊的記憶內容閃現新的光澤,顯露新的意義。因而,記憶并不是恢復過去,也不是簡單地、無約束地重構過去,而是一個批判性的生產過程,為了使記憶擺脫各種復雜的權力關系的糾纏,記憶在某種程度上的碎片化是有效的策略。而這也正是《日夜書》的一個表面特征。
韓少功的《日夜書》就是要開啟這樣一個重新記憶的旅程。這是一個雙向的辯證過程,一方面,它要疏離于甚至對抗逐漸庸俗化了的、權力化了的知青記憶——它由既往的知青文學(包括回憶錄、訪談、口述史、記錄片等)建構起來。重新喚醒被這個超級記憶所遮蔽的個體記憶,拂掉年深日久的灰塵,恢復其生動性和切身性,同時,逃離記憶的黑洞,重新選擇那些被刻意遺忘的差異性內容。另一方面,這種新的記憶帶領我們重新返回當下的現實。因為所謂現實其實已經是被原來的集體記憶所塑造的現實,攜帶著另類的記憶,以之為批判性的新支點,韓少功得以用新的視野觀照當下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日夜書》作為知青寫作是一次反知青寫作,包括反抗自己曾經的知青記憶和知青寫作。
《日夜書》從各種意識形態的敘述下面解放出來,呈現了以前的知青文學所不曾呈現的知青生活場景、事件,以及“奇特”的各色知青人物。擺脫既往固定化的意識形態的壓制,知青生活的復雜面相顯露出來,它的多樣性和含混性,無法被某種主流的意識形態所收納、化約和解釋,知青生活重新被“還原”為一個個活生生、具體化的情境與細節。生活本身的曖昧性和質感顯現出來,饑餓感,痛感,“看秋”的孤獨感,已與舊有的知青敘述中的社會性迫害模式脫鉤。既往在社會意義框架中理解的知青人物,顯示出各不相同的,不似以往知青形象的個體性特征,或許,舊有的知青敘述過分強調了知青經歷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作用——顯然,這是“傷痕”、“反思”小說控訴政治、社會迫害的內在需要。《日夜書》中,知青的群體社會性特征淡化了,所謂知青生活只不過人們生活的具體情境罷了(其中不只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知青,還包括當地的農民及干部),盡管知青生活對青年人有著巨大的影響,但它畢竟只是影響人格的部分因素,甚至都不好說是很重要的因素。
既往被表述為一個整體的知青生活,具有某種內在本質的知青經驗,即負載了特定社會政治意涵的知青想象瓦解了。小說以對知青生活的復調性敘述代替了單聲的敘述,在重新回憶中,它內部的復雜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多重的張力出現了。如果我們進行一點知青文學的互文式的聯想的話,不難發現,整部小說的回憶敘述暗含著一種對舊有知青記憶機制的反諷意味。某種意義上,呈現豐富性和差異性本身不可避免地就帶有對知青敘述的批判性審視。
既往的知青文學一般總是具有悲劇性或荒誕性的調子,常見壓抑性的灰暗,間或夸張的崇高。《日夜書》不再為一種主導性的情緒和敘述風格所宰制,力求呈現知青生活的多色調和豐富性。
但是,知青生活的多樣性、豐富性和矛盾性卻被知青群體自己所遺忘,并日漸被偏執地窄化。其實,知青經驗只是表象,從根本的意義上說,無論是紅衛兵、知青,還是革命的挑戰者,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子。知青群體,為紅色革命所催生,而后又逐漸將革命的激情導向革命自身。在那個特定的歷史年代,在從壓抑性的舊的革命體制脫身而出時,他們恰恰以否定性的方式真正延續了革命的精神,并在此過程中迸發出巨大的生命潛能,這才是所謂知青群體作為一代人更為本質的方面。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不起眼的賀亦民、姚大甲、安燕們為何具有那么大的經折騰的生命能量和不可思議的創造力,同樣,我們才能明白知青中的精英們在鄉下何以進行自我啟蒙,正如《日夜書》中所講述的,他們讀書,思考,身居鄉土卻關心世界,并以少年人的意氣互相標榜,斗氣,樂此不疲,在此過程中,他們以求秀異的姿態挑戰著平庸的現實生活,在思想的領域里尋找著理想生活,馬濤等人的“反革命集團”事件只不過是這種不安分的極端表現罷了。然而,他們在真誠地追求個體自由,否定舊有的革命秩序時,恰恰忽略了他們是在繼續革命。在隨后的開放年代,知青一代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能量很快耗盡,在一種虛假的自我意識中,在對所謂現代目標的堅持中,他們的精英分子落入了歷史的狡計與預備的陷阱。
某種意義上,馬濤、賀亦民、安燕等人以不乏悲喜劇的方式,保持了所謂知青的本色,馬濤更是一如既往地停留在天真狀態中,他的悲劇在于,他那些政治姿態在既經改變的歷史中已經變味了,他仍然以一種自命不凡的驕傲支撐著,不過,盡管偏執,盡管顯得可笑,他自己倒是一以貫之。
馬濤們的這種自我意識或自我幻覺往往使他們習慣于自我英雄化,滋生出一種對歷史和社會的索債心態。這導致了他們的自私性和狹隘性,這種封閉性鮮明地體現在他們自我封閉,拒絕傾聽上,永遠像才女蔡海倫一樣自說自話,不斷重復,從來不關心別人在想什么,即使是母親。
對馬濤們來說,知青生活的苦難——它來自體制性的迫害,保證了他們本身的正當性和崇高性,仿佛是一張累計利息的有價證券或欠條,給了他們向歷史、社會索取債務的權力,更何況還有坐牢這樣的神圣履歷。即使是普通的知青,也分享了這種身份意識,在重返插隊農村的旅游中,不是大家都認為有權利吃飯不付賬么?
這種“自我中心”的心態使知青一代人顯現出某種青春性格固化的精神病特征。馬濤表現出了讓人難以容忍的自私褊狹,從不體諒他人。如果要說社會、歷史傷害了他們,就是讓他們形成了這種性格和自我意識,而它直接來源于對知青生活的選擇性記憶。未經充分反思的知青經驗被馬濤們濫用和揮霍了。這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劇。此種心智結構一旦固化再難改變,馬濤在國外的尷尬處境非但沒能讓他有所改變,反而使他更加偏執。這種青春期人格的固執造成了知青精英們無法處理與下一代的關系,因為他們自身還仍然停留在上一代的心智水平上,馬濤的女兒笑月、安燕的女兒丹丹,基本上都屬于問題少女,這不能僅僅歸罪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失敗,更應歸因于父母的不成熟狀態。“我”(陶小布)在小說結尾遭受的笑月的質問不僅僅是針對陶小布個人,更代表了來自下一代的對知青一代的歷史審判,這也可以視作知青葬送的現實與未來一代的審判。
于是,我們發現,知青虐待了歷史,因為他們總以為他們被歷史所虐待。一個奇妙的辯證法出現了,正是在對政治專制等外在壓抑的刻意、夸張的反抗中,知青們使他們努力反抗的權力成為建構自我的內在構成部分,在施虐與受虐的關系中,對抗的激情轉化為快感,一種對歷史撒嬌的姿態由此產生。馬濤等啟蒙一代,一直生活在表演中,一直和權力默契地玩著虐待與受虐的游戲,它甚至在肉體感覺比如性快感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安燕在性行為上的變態道出了他們與所謂政治暴力的真實關系。他們需要它,沒有就要虛構出來。馬濤從政治英雄到思想英雄的狂想,正代表了典型的啟蒙心態。他所獲的癌癥更像是一種歷史的絕癥。敘述人對馬濤是充滿同情的,其中有對一代人的同情,這是他們的原罪。
《日夜書》由此具有了對知青一代的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盡管未必是小說的重點所在,卻給我以深刻印象。韓少功作為曾經參與過知青文學史的知青作家,對知青,也對知青文學史進行了質疑。知青文學具有一種普遍的索債和撒嬌的心態,習慣于對自己的歷史形象進行自我美化,喜歡推諉歷史責任,即使1990年代以來個別知青題材的小說進行了一些假模假式的抽象懺悔,對于權力化的知青進行了超然的外部揭露,也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回避了最核心的問題。而韓少功以巨大的體諒看待包括自己在內的一代人,也對它進行了嚴苛的批判,事實上,他對自己這一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青這一代人不應辜負了歷史,枉歷了一番豐富的苦難的饋贈與教誨。這是真正的自我批判,它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知青進行道德主義的審判,而是充滿了猶疑,他更多地是以豐富復雜的現場化的,歷史化的“生活本身”來呈現知青一代人的精神癥狀的來源,同時,他以關于知青的另類敘述粉碎了陳舊的壓抑性的知青敘述,打開了重新理解現實的可能性空間。
人們總是太習慣把自己的墮落,隨波逐流看作外在壓力所致或受迫害的結果,很多知青總喜歡這么給自己辯解。相比之下,外號“秀鴨婆”的梁隊長,或許因為不是知青吧,具有完全不同的心態,以巨大的道德力量,承擔起在世的責任。這是真正的偉大。不知道韓少功這一筆是不是信手的閑墨?
《日夜書》采取了復調的敘述,打破了以往知青敘述單聲的意識形態化敘事。為了寫出知青生活內部的差異性和復雜性,韓少功必須找到一種具有充分張力和包容性的敘述方式。在小說中,敘事人穿越于回憶與現實之間,敘述與沉思相互交叉,使敘事人不斷跳離,而不是沉浸在記憶中,也使他避免過久地以某一個或幾個人物組織整體性故事。敘事人不斷地講述互相沒有直接聯系,形態各異的故事,而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又由一個統一的敘事人串聯起來。“我”并不總是一個故事角色,有時更像一個故事的見證者或轉述人,盡管在某些段落中“我”是一個主要的人物,執行著重要的敘事功能,但從整部小說看起來,與其說“我”是一個主要故事角色,不如說更像一個見證者更恰當。通過這種方式,“我”保持著一個反思主體的冷靜,不時脫身而出,進行頗為理性化的思辨與討論。這種敘事策略既保持了敘述的整體性,又避免了總體化的壓抑性結構,從而很好地保持了敘述空間內部的差異性和張力,也制造了反思性的間離效果。
韓少功的知青寫作也經歷過“傷痕”與“反思”等階段,盡管他總是疏離于文學潮流,別有懷抱,卻也與主流知青文學分享了一些共同的觀念。但此后,他與意識形態化的知青敘述拉開了越來越遠的距離。對于他們這一代來說,知青經驗是一所煉獄,只有真正的穿越它才能獲得心靈的解放,而這種解放只能靠知青一代自己。知青經驗,如經過認真清理和反省,代表了經過真正的現實人生的歷練和消毒的理想主義,它既不同于那種拋棄理想,犬儒化的虛無主義,也不同于缺乏底層生活歷練的簡單化的理想主義。
只能真正消化了知青經驗,才能獲得眺望未來的新視野。知青記憶由是才能得到超度與升華。1990年代以來,韓少功一直沒有在真正意義上正面涉足過知青題材,這或許也是他多年來想寫而又不愿寫,不敢寫的領域。閱讀這部小說,我似乎隱約感受到他在寫作過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停歇的狂暴的內心風雨,飄搖不定的情感激蕩,其中有一代人的沉重命運和一代人隱秘的內心路程。
《日夜書》,是讓人記住那些既經流逝又永遠活在當下的日日夜夜嗎?日夜書,不只是知青,每一代人都要進行這樣的功課吧。或早或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