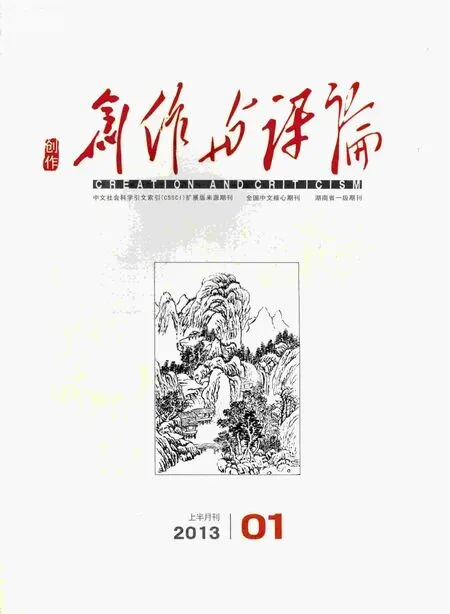甫躍輝的創作流變
○ 康凌 金理
一
甫躍輝出道之際,其實面對著一條狹窄的路。他的前輩莫言、王安憶、余華們以先鋒姿態進入文壇,當時的文學體制比如重要的純文學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后當代文學轉型為“常態的中年期”(陳思和),他們構建了今日中國文壇的中流砥柱,在穩定的環境里,從容磨礪寫作技藝、豐富世界觀、摸索讀者的口味,不斷推出的作品是主流獎項的候選者、學院批評家的關注對象和圖書市場的看點。即便是橫向地和同齡人相比,和那些完全和新的傳播媒介、新的文學生產方式水乳交融、互為推波助瀾的弄潮兒相比,躍輝也顯得有點“落伍”。在很多人看來,“80后”寫作、“青春寫作”本就和商業包裝、高點擊率、喧囂的網絡論壇、“玄幻”、“穿越”相伴隨。由此看來,躍輝真是選擇了一條最狹窄的路。
不過他在這條窄路上卻走得安心、從容不迫、穩穩當當。因為關于文學的“變”與“不變”,他有獨特理解:“回顧現在活躍在文壇上的前輩作家們,他們剛開始進入所謂文壇或在文壇成名時是以怎樣的方式?‘30后’作家王蒙,開始寫作時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遙寫了《人生》;‘50后’王安憶最開始引人關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華和蘇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則臣最初引起關注的是《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這些作品都寫的是年輕人,都是在一個連續的傳統里。這些都沒有被冠以‘青春寫作’,可到了‘80后’就變了。剛才提到的‘70后’的徐則臣屬于成名較晚的,比較早成名的像衛慧、棉棉,她們作品中的年輕人與徐則臣作品中的年輕人截然不同。徐則臣是與前幾輩作家一脈相承的,而衛慧、棉棉是另外一副樣子。衛慧、棉棉和之前的‘傳統寫作’斷裂了,卻又被后來的徐則臣等人接續上了。我覺得‘80后’目前進入公眾視野的這一批人承襲了衛慧、棉棉這一脈,盡管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許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卻全都成了這樣的。我在《上海文學》雜志社做編輯,接觸到很多年輕人,他們也是從期刊發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經進入公眾視野的‘80后’寫作者決然不同,這一撥人將會像徐則臣他們那樣,接續上被同輩人扯斷的傳統。反叛然后回歸,常常是一代人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70后’還是‘80后’的寫作者,在與所謂‘傳統寫作’發生斷裂的同時,也暗暗地有了承續。”①“70后”作家分化確實可作為今天“80后”們的借鑒。剛開始是炒作“美女作家”這個概念,但現在看來,在“70后”作家中真正成熟的,與當年炫目的美女作家相比往往顯得低調,甚至自覺遠離媒體視線,在文學的年輪中默默成長,在積累、沉淀之后給人水到渠成、春來草自青的感覺。
所以躍輝一點不著急,安安心心讀小說,寫小說,“學院派”的步步為營,顯出了和一起步就在流行市場里匆匆打拼的“青春文學”不同的風致。《丟失者》的開篇起筆,《驟風》結尾的視角轉移,《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對文本結構與動機的打磨,凡此種種,在青年小說家的學習時代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對前輩作家的亦步亦趨,更是自1980年代先鋒而來的當代文學脈絡在他身上的綿延賡續。對“傳統”的繼承在他那里,被具體化為對上一輩作家作品細致的閱讀和研習,和對“小說”這門“手藝”的默會心知,而他也由此立定了自己在當代文學版圖里的淵源與位置。
二
聽躍輝講過很多故鄉鄉間的故事,其中的一些已被他寫入小說中,那惝恍迷離、鬼影綽綽的氣氛、少年在想象的世界里夜游的經歷,很讓人想起沈從文先生筆下《哨兵》一類的篇章。躍輝的這一類創作質量穩定,已基本上構成一個其來有自的文學世界,這是躍輝創作的起點。其實這已非易事,提筆寫作并不就意味著一個人找到了自己的創作起點。
這批創作小說中,印象最為深刻的當推《初歲》。十多年前,主人公蘭建成是跟在送去屠宰的豬后面“難過又無能為力的小男孩”;等到第一次操刀前“咬緊牙齒,身子顫抖,激動和緊張混雜在一塊兒”;殺豬過程中“有一瞬間,他又隱約觸到了小時候的那種疼痛,但轉瞬即逝”;后來“時隔多年,蘭建成已經不能體會面對一只豬的死產生的那種痛苦了,甚至為自己當年竟然那么痛苦感到難為情”……蘭建成面對殺豬時的體驗——借用布魯克斯和沃倫的話——可看作對“邪惡的發現”,而從恐懼緊張到安之若素,蘭建成內化了成人世界的秩序和機制,從而與純真的兒童世界告別。小說中殺豬這一情節,由此可理解為告別兒童向成年轉化過程中經受考驗的寓言和儀式。小說最精彩的地方,寫到蘭建成從豬身上抽出刀子,“血接踵而至”,那一剎那,“恍然覺得血是從自己身上流出去的,不知不覺中,他的呼吸竟和豬的達成一致”。從上述過程和細節來看,成長如此殘酷,意味著對痛楚的漸漸麻木,甚至意味著殺死“對象化的自我”。小說還寫到了侄女小微,她在屠宰場大聲哭泣的表現恰如十多年前的蘭建成,更年輕一代的成長也必須重復這樣的殘酷嗎?小說寫到這里——告別/成長的轉型中對殘酷的發現——似乎并無太多新意;然而,有意味的是,小說所展示的“小微—蘭建成”這一成長序列,還可延展成“小微—建成蘭—老董”,也就是說:小微固可視為以前的蘭建成,但老董也可看作未來的蘭建成。老董在小說中著墨不多卻讓人過目難忘,他在凡庸的崗位上從容盡著生命之理,身上閃爍著《莊子》中那位“技進乎道”的庖丁的影子。這里的沉靜與前面的殘酷形成豐富的意味,似乎為成長開放著可能性。與網絡文學、媒體文學更多追求生產、流通、消費的高速不同,傳統文學當以更沉穩的心態關懷人類社會及人性經驗的全部復雜性(甫躍輝曾聽從導師王安憶的教導而停筆一年,以保持小說的文學品格)。在眼下的青春文學中,概念化的人物、簡單的情節、虛擬封閉的情境比比皆是,正是在這方面,躍輝的創作給出了有力修訂。
就題材而言,《我的蓮花盛開的村莊》有點像余華的《活著》,但差異也是明顯的:后者那里高頻率的死亡、出人意料的轉折等元素構成的“苦難+溫情”的策略,在躍輝筆下卻都被節制地略去了。恰如小說末尾所寫:奚奎義仍然坐在廟門口嗚嚕嗚嚕吹喇叭,“他也不知道自己吹的是什么曲子,不知道是哀樂還是喜樂,所有的悲和喜都亂成一片,在很遙遠的地方回響”……我以為,小說正是在悲喜泯然中寫盡了一個普通人對日常生活的莊嚴態度。而《暖雪》無疑是一曲挽歌。彌漫著松脂味的樹林、蓊郁大山及山中的生靈、還有打獵的老人,都將一去不返。“亮子遲遲沒做出決定要不要去城里”,小說結尾卻以生機乍現的自然場景(“猛地跳出一團橘紅,圈在水庫里的水們一霎時全活了,聽得到無數的歡笑、吵嚷。……”)掩飾了選擇的無奈。我覺得《暖雪》不妨和躍輝的另一中篇佳構《魚王》對讀。小說中都出現了“外來者”形象,《暖雪》中來水庫旅游的城里人貪婪、無禮,這是典型的鄉土中國的闖入者——在《暴風驟雨》中可以是帶來“歷史開端”的土改工作隊,在張煒筆下可以是隆隆的推土機和瘋狂掠奪的開采工程組——他們的“進入”鄉村或者代表一種現代文明對民間“小傳統”的對立、改造;或者意味著對大地和自然的肆意索取、破壞。而《魚王》卻貢獻了新鮮的“外來者”形象,老刁和海天熟稔鄉村倫理(比如挨家挨戶地送魚),敬惜大自然(比如海天和魚王之間的神秘呼應),取予有道……無論是“外來者”抑或“原鄉者”、是離開抑或留守,但愿他們都能找到適合其態度與方式的生存之地。
三
除了“外來者”和“原鄉者”外,“回鄉者”更構成了躍輝筆下的一組豐富形象。《牙疼》里的小艾從“要坐火車、汽車,加起來三天三夜不止”的浙江回鄉,不僅帶回來一個雙手和“翅膀一樣細長”的浙江男人,更帶來了自己難產、被拋棄的命運,攪動起整個鄉土沉滯的倫常土俗——在鄉人們看來一定會自殺的她,竟然重新梳妝打點準備遠行,“她的美麗如灼灼桃花,灼痛了所有人的眼睛。”《舊城》里的小易,曾經為了躲開母親而報考中師,離開故鄉,“母親大吵一架,就走了,一走就再也沒回來過”。然而,正如《初歲》里的蘭建成借由殺豬的過程,受洗般地重新進入藏污納垢、生氣盎然的民間鄉土。重回故土的小易,也在故鄉日常瑣碎的灑掃庭除里驀然驚覺,“自己竟然和母親如此相像”,與母親的和解正是與故鄉的和解,一趟回鄉之旅使她諒解了母親,也真正發現、進入了“舊城”。
遠行與回鄉,是文學史中不斷復現的創作母題,而躍輝筆下的回鄉者與原鄉之間的沖突或是和解,則可以追溯到現代文學自魯迅、沈從文以來的悠長脈絡,中國特有的城鄉結構造就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牙疼》里村人對遙遠的浙江的想象,“浙江人”用相機對鄉村世界的打量與“定格”,《舊城》里不斷催促小易回校的口吻陰森的“副系主任錢學明”,在在標示著隱綽在“鄉村”背后的“城市”的巨大陰影。對橫跨城鄉兩界的“回鄉者”或“進城者”(這里的“回鄉”,幾乎肯定是從城市回鄉,而非從另一片鄉村返回)而言,這種“一生兩世”的現代性經驗,根本無法在高歌猛進的“現代化”或“城市化”敘述中得到表達,躍輝的寫作,正是在這一點上呈示出了這一群體的內在的撕裂、沖突與焦慮。《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的李繩離開故鄉北上省城,在被女朋友揭穿了自己假冒城市大學生身份的謊言之后,神使鬼差地撥通了中學時暗戀的女同學曹英的電話,卻“仿佛有一根骨頭卡在喉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此后,每當遇到挫折,李繩便給曹英打電話,依舊是一言不發,但“每次給曹英打完電話,他總能獲得一段時間內心的寧靜。”融入城市的失敗催生了對故土的依戀,但面對故土時的持續的“失語”狀態,則成為“進城者”們進退維谷的存在狀態的隱喻,語言是存在的家園,是生活世界的自我呈顯,語言的失落,不僅是內在精神的焦慮與緊張,更是與整個生活世界的疏離與剝落,他們自己知道,“一旦開口說話,他和曹英之間是沒有多少話可說的。”由此,“進城者”成為真正的“零余者”,被兩個世界同時拋棄,一面無法獲得城市的身份與認同,一面也被隔絕在鄉土之外,無法回到鄉土的生活、言路之中,他們要么通過欺騙他人與自己(假裝大學生)進入城市,隨時面臨被揭穿、挫敗的可能,要么如文本末尾所寫,通過暴力乃至殺戮,強行介入曹英的生活,進入原鄉世界。在小說最后,李繩回到故鄉殺死曹英的男友,同時打電話告訴曹英自己在省城,試圖成不在場的假象。但“恰恰是那兩個電話”所留下的手機漫游記錄暴露了他的真正位置,導致了他的落網。借助手機與漫游這些現代工具與技術,躍輝精巧地表達了“進城者”的自我認同及其現實處境之間的扭曲錯位,這種錯位來源于城鄉二元的結構,并最終撕裂了被它所籠罩、壓抑著的進城者/零余者們。
四
由此,我們得以進入躍輝創作的另一端:城市生活。與鄉土世界的溫情與奇絕相比,城市則多被呈現為一個壓抑而荒謬的空間。《驟風》開篇的一句“突然,起風了”,宣告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城市颶風,“沿路卷起了灰塵、雜草、果皮、紙屑、塑料袋、小樹枝、鐵鍋、水桶、糟木板、破衣爛衫……”,人們在其中只能無助地掙扎求生。在疾風肆虐的描寫過后,躍輝筆鋒一轉,又一句“突然,起風了”,引出了三天前“我”的女朋友在大風中遭遇的車禍與死亡。如果說氣候乃至節氣在鄉村代表著自然的生息時序,那么城市驟風,便仿佛構成了一種至大無外而莫可名狀的力量,操縱著城市空間的混亂、危險、甚至倏然而至的死亡。同樣,《驚雷》中的一場雷雨,使得四個毫無聯系的人偶然地在躲雨的地方聚攏在一起,卻發現每個人都帶著生活,或者說是金錢,造成的創傷,頭頂不斷咋響的驚雷,似乎可能在每個人身上爆裂。
在《巨象》里,表達這種壓抑性力量的意象換成了主人公李生揮之不去的噩夢:“巨象”的碾壓。和女友的分手,被李生“下意識地理解為進入城市的失敗。”而剛從外地進城的小彥,則成為失敗后的補償與慰藉。在這里,戀愛關系變成城鄉結構的隱喻,對女性的欲望被悄然轉換為對城市的欲望,女性被物化為欲望都市,城市則被銘寫上強烈的陰性氣質(femininity,這一點確實可以上溯到郁達夫在國族政治與個人欲望間的奇妙轉喻),躍輝的寫作,正揭示了當代都市欲望的生產機制中的這一主導邏輯。正如黃平所說,“在‘城里人—外地人—更弱的外地人’這條生物鏈上,李生吞噬起更弱的小彥十分平靜,盡管偶爾閃過猶豫,但整體上是心安理得的。②但是,李生并未因此得到安定,不僅被女友拋棄的創傷沒有因此治愈,而且對小彥的傷害,也成為了他無法擺脫的夢魘,他腦中不斷閃現的“我還是個好人嗎?”的自我拷問,更提示了個體的倫理法則,在城市(巨象)的無情碾壓中的蕩然銷隕。正是這種惘惘的力量,誘使《晚宴》中的顧零洲產生為前女友拍裸照的扭曲欲望,推動《動物園》里的男女主人公展開一場圍繞著開窗與關窗的荒謬拉鋸,更使得《蘇州夜》里的“他”像“一個被人牽著線的木偶”一樣與酒吧女進行了性交易。城市如同一個無物之陣,所有的荒誕與悲劇都無法簡單揆諸個體的善惡對錯,每個人似乎都在城市邏輯的擺布下傷害彼此,乃至毀滅自身。
事實上,即使進入了城市,擁有了城市人的身份,也未必意味著能夠擺脫這樣的力量。《丟失者》中的顧零洲本科畢業后在城市中擁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建立了穩定而廣泛的人際網絡(手機上“目前存有534個號碼”)。但是,一次意外的手機丟失將城市生活內中真相展現得纖毫畢現。在這里,躍輝顯示了與庸常作者的距離,他既沒有著力于丟失手機后的孤獨惶惑,也沒有停留在擺脫人際關系束縛后對自我、自由的發現,相反,他很快讓主人公重新獲得了一部手機,而正是在這時,顧零洲發現,在他脫離人際網絡的這段時間里,“一個信息、一個電話沒有”,“沒有一個人詢問他怎么停機了”,想象中的“女友會發瘋一般,懷疑他、責備他、又擔憂他”并沒有發生,“無論是電腦還是手機,都那么安靜。這個世界真安靜。”意外的意義不在于意外本身,而在于它在日常生活的完滿外表上劃出了一道裂縫,讓人們得以窺探城市人際網絡熱鬧表面下的冷漠與疏離。
與此類似的,是《朝著雪山去》里那些畢業后逐漸在城市里安頓下來的同學們,他們在聽說了關良“去拉薩朝圣”,并由此戒除網游的計劃后,紛紛解囊相助。不論情愿或是不情愿,他們的資助,都使得關良此行或多或少承載了他們的集體愿望:從凡俗的庸常瑣事中“掙脫自己沉重的身子朝雪山飛去”。然而結局卻是,在遍歷各種曼妙景致到達拉薩之后,關良竟“大搖大擺地穿過街道,朝對面一家網吧走去。”他對朝圣的評價與他出發前對世俗生活的評價如出一轍:“沒意思!”
空洞的城市生活中醞釀出來的所謂朝圣理想同樣空洞,兩者互為鏡像,一體兩面,是同一套文化心理結構的產物,躍輝在和都市小資們“到西藏去凈化心靈”之類的夢想開了個小玩笑的同時,也顯示出自己的敏感與批判性,并以此繼續觀察、書寫著現代都市主體的存在樣態。
躍輝曾寫道:“文學,對那些僅僅冀望生活安穩和順的人們,究竟有多大用處呢?文學是否能如一盞可以放出光亮的燈,給人一點兒微末的安慰?當然,我可以像某些人那樣很不屑地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文學就不應該是功利的實用的。但是,但是,為什么我心中仍舊不安呢?”
所有的寫作本身都在探尋寫作的意義,這一探尋本身,也構成繼續寫作的動力。那是自己與自己的搏斗,自己對自己的說服。也只有在這種緊張里,才能真正牽拉出扎實的、豐滿的作品。
這就是躍輝所走的道路。
注釋:
①參見《新世紀十年文學:斷裂的美學如何整合?》,《文學報》2010年7月15日。
②黃平、楊慶祥、金理:《當下寫作的多樣性——80后學者三人談(之六)》,《南方文壇》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