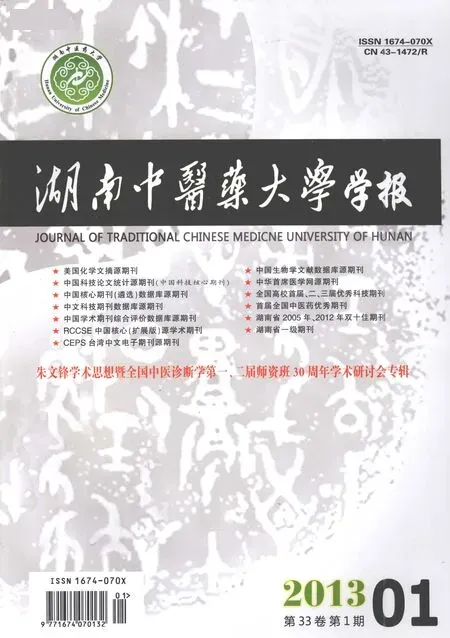癥狀計量與證素辨證
梁 昊,周小青,雷麗萍
(湖南中醫藥大學中醫診斷研究所,湖南 長沙410007)
朱文鋒教授在《證素辨證學》中提到:每一癥狀的輕重,對辨證診斷的意義也有差別。若該癥狀重或為主癥時,其定量診斷值可乘1.5,若該癥狀輕時,則可只乘0.7[1],但其著作中并未詳細說明癥狀輕重如何判斷。是否為主癥和癥狀的輕重對證型的判斷和譴方用藥的準確性均具有重要意義,癥狀的主次與等級量化均屬計量診斷范疇,需要更詳細闡明。
1 癥狀的主次
主癥對中醫疾病的診斷往往具有決定意義,任何一版中醫內科學教材,在描述各種疾病的概念時,均以“某病是因××病機,以××癥狀為主要表現”進行定義。疾病不同,即使判定為相同的證型,治法和方藥可能也會不同。如心系病中,心悸和胸痛為兩個常見癥狀,但以心悸為主癥則為心悸病,以胸痛為主癥則為胸痹心痛病,兩病雖然有相同證型,但所用方藥不同:心悸-血瘀證-桃仁紅花煎,胸痹-血瘀證-血府逐瘀湯[2]。癥狀的主次是最基本的定量,臨床中很容易辨別。辨明主癥,確立疾病,病證結合才能有精確的診斷和療效。從癥狀入手,病證結合的診斷流程,是證素辨證的進一步深化。如圖1。

圖1 病證結合診斷流程
2 癥狀的量化方法
癥狀的輕重需從多個角度加以量化,下面就以疼痛為例具體闡釋癥狀的量化方法。疼痛是臨床上最為常見的自覺癥狀之一,可見于機體的不同部位。導致疼痛的病因病機可概括為虛實兩類:因實而疼痛者,多因邪氣阻滯了臟腑經絡氣機,使氣血運行不暢所致,屬于“不通則痛”。其痛勢較劇,痛而拒按;因虛而疼痛者,多因氣血或陰精虧損,使臟腑、組織、經絡失養所致,屬于“不榮則痛”。其痛勢較緩,時痛時止,痛而喜按[3]。疼痛主要以問診為主,常結合切診(壓痛、叩痛等)進行。
2.1 誘發因素
大部分疼痛都有一定的誘因,如心絞痛與活動和情緒有關,胃痛與進食有關等。
2.1.1 總原則 0 級:一般的常見誘因不引起無疼痛;Ⅰ級(輕度):常見誘因偶可引起疼痛;Ⅱ級(中度):常見誘因常可引起疼痛;Ⅲ級(重度):無明顯誘因亦可發生疼痛。疼痛常見誘因等級量化見表1。

表1 疼痛常見誘因等級量化表
2.1.2 注意事項 (1)誘因和疼痛常可互為因果,如進食引起疼痛,則影響正常飲食,活動引起疼痛,則活動受限,甚至生活不能自理;(2)在保證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可施加該誘因進行評價,如平板試驗、步行1 km 試驗等。
2.2 疼痛強度
2.2.1 分級方法 疼痛是患者的主觀感受,醫務人員不能想當然地根據自身的臨床經驗對患者的疼痛強度做出武斷判斷,推薦采用國際通用方法——主訴疼痛分級法(VRS)[4]進行評價:0 級:無疼痛;Ⅰ級(輕度疼痛):患者有疼痛但能夠忍受,不影響其正常生活和睡眠;Ⅱ級(中度疼痛):患者感疼痛明顯,不能忍受,要求服用止痛藥,睡眠受干擾;Ⅲ級(重度疼痛):疼痛劇烈,不能忍受,需用止痛劑,睡眠受到嚴重干擾,可伴有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或被動體位。疼痛常見程度等級量化見表2。

表2 疼痛常見程度等級量化表
2.2.2 注意事項 (1)疼痛程度的評價常與預后直接相關,因此尤其要鑒別一些致命性的病證;(2)不能輕易應用止痛藥,以免影響疼痛的真實評價,耽誤診治。
2.3 頻率和持續時間
疼痛頻率和持續時間常結合在一起評價。國際公認3 個月為界分為急性和慢性疼痛[5]。急性疼痛實證居多,慢性疼痛虛證居多;每次發作持續時間長,發作次數多,以實證為主,反之則以虛證為主。
2.3.1 總原則 0 級:無疼痛;Ⅰ級(輕度):疼痛為陣發性,每次持續數分鐘;Ⅱ級(中度):疼痛為陣發性,每次持續1 小時至數小時;Ⅲ級(重度):持續性疼痛。疼痛常見頻率和持續時間的等級量化見表3。

表3 疼痛常見頻率和持續時間的等級量化表
2.3.2 注意事項 (1)急性疼痛在持續時間上可起到一定鑒別診斷的作用,如胸痛劇烈持續30 min 以上者,真心痛可能性大,需進行心電圖和心肌酶檢查;(2)不同部位疼痛頻率和持續時間在評估上有一定差異,需量體裁衣,如一些伴腰腿痛的病證從發病開始就呈持續性。
2.4 疼痛范圍
一般疼痛范圍都較局限,疼痛范圍擴大常見于腹痛。
疼痛范圍分級方法 0 級:無疼痛;Ⅰ級(輕度):疼痛局限;Ⅱ級(中度):疼痛向其他部位放射;Ⅲ級(重度):疼痛向周圍擴大、彌漫。以腹部疼痛為例常見范圍分級見表4。

表4 腹痛常見范圍分級表
2.5 疼痛緩解方式分級表
2.5.1 疼痛緩解方式分級方法 0 級:無疼痛;Ⅰ級(輕度):常規方式可緩解;Ⅱ級(中度):需要用較強的干預方式才能緩解;Ⅲ級(重度):很強的干預方式才能或不能緩解。疼痛常見緩解方式分級見表5。

表5 疼痛常見緩解方式的分級表
2.5.2 注意事項 緩解和干預的方式,可起到鑒別診斷的作用,如胸痛服用硝酸甘油緩解,則胸痹心痛的可能性大。
2.6 癥狀計量與綜合評價
總原則0 級:無壓痛;Ⅰ級(輕度):一般壓(叩)痛;Ⅱ級(中度):按(叩)后,皺眉呼痛,并有保護性動作;Ⅲ級(重度):疼痛拒按(叩)。
3 展望
證素辨證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中醫診斷學貢獻是巨大的。傳統中醫是通過直觀的望、聞、問、切四診搜集病情資料,然后按照中醫理論結合實踐經驗作出病證的判斷。表面上看,似乎是“質”的推理,實際上也包含著“量”的概念[6]。隨著中西醫結合研究的發展,尋找新的“量”的客觀指標為中醫辨證服務,是繼承和發揚中醫診斷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傳統的四診手段是科學的,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免還有一定的局限性,充分利用現代數學、計算機科學開展中醫病證的量化診斷研究是有必要的,是逐步實現中醫診斷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途徑,這與證素辨證殊途同歸。計量診斷與證素辨證的結合,能提高中醫診斷的精確性、客觀性和可重復性,使中醫診斷學更加完善。
[1]朱文鋒.證素辨證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22.
[2]周仲英.中醫內科學(第2 版)[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77-78.
[3]朱文鋒.中醫診斷學(第2 版)[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19.
[4]黃慧萍.對患者疼痛的判斷和護理[J].國外醫學·護理學分冊,1993(3):101-102.
[5]王 琦,倪家驤.慢性疼痛的評估與治療策略——JCAHO 標準解讀[J].中國醫刊,2005(4):10-12.
[6]周小青,羅堯岳,劉建新,等.中醫計量診斷理論與方法探討[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3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