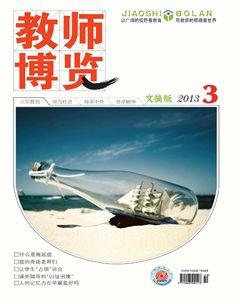“發鴻蒙”的第一課
任蒙
人生有許多“第一課”,不過都是一種借喻性的稱謂,比如吃奶,那是每個人生下來都必須學會的第一種本領。母親把她的乳頭塞在你嘴里,然后輕輕地拍打或撫摸你,她通過這種愛撫傳給你一種示意,讓你吃香,吃好,但不要吮得她疼,讓你和她完成一種最神圣而又最原始的奉獻與索取。
類似這樣的第一課,大都發生在沒有記憶的年齡,甚至多少帶有動物的屬性。只有入學后的第一課,才是真正文化意義上的第一課,才是由混沌人生走向文明人生的第一課。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人生真正的起點。因此,第一課決不是書本中最簡單的文字。
三十年代,教育當局請梁實秋編寫啟蒙課本,第一課擬為“來,來,來上學”,結果遭到許多人的強烈反對。梁實秋只好找到一位對其最不滿意的人,請他來撰擬,并預付了很高的稿酬。不料那位先生很快退還了稿酬,表示難當此任。最后幾經反復,第一課定為“去,去,去上學”。這一字之改,初看毫無必要,細加琢磨便見奧妙,即由學校和老師對適齡兒童的召喚,改為家長對孩子的主動催促和學生自己對讀書的一種自覺追求。若用于今日正在推行的希望工程,仍具有促動作用,可見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假如是當時說來,就應該是“深遠的歷史意義”了)。這樣的第一課,喚醒過多少父輩對子孫的期冀,喚起過多少孩童對求知的渴望。
人的一生中,有許多閱讀過或經歷過的東西可能被忘卻,但小學第一課卻對每個人如刀刻鏨鑿一般,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余秋雨先生長我十來歲,他上學當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回憶說第一課是“開學了”。那時文字尚未改革,第一個繁體的“開”字就那么復雜,我看還不如“去上學”生動易學,也難為他們那一代人了。我入學時,已是六十年代初期。
家鄉父老把孩子開始讀書叫做“發鴻毛(蒙)”。不知這個說法是從什么時代延續下來的,我曾經查過不少辭書,根本沒有“發鴻蒙”這個詞條,但我總認為它的涵義比書上規范的“發蒙”或“啟蒙”要豐富得多。
鴻蒙,天地未開之前的氣象,一團元氣,一片混沌。到了教書先生那里,混沌就能夠得到開辟,就可以擺脫自然氣團的蒙困。可是,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當時我們背著母親縫制的“釣客螞(青蛙)的袋袋兒”,第一次走向村邊那座只有兩間干打壘教室的小學時,在先輩們的叫法里竟如鴻蒙初開那樣神圣無比。那么,我們的“鴻蒙”是從哪兒開啟的呢?課本領到了,第一課是“一二三四五”,接下來便是“六七八九十”。也就是說,我們學認的第一個字是“一”,它最簡單也最形象,鄉親們說扁擔橫下來就是“一”,連它都不認得的人準是“睜眼瞎”;它最博大也最好理解,萬事萬物都有一,并且都無一例外地從一開始。宇宙之大,世事紛繁,發鴻蒙的第一課抓住這萬物初始的“一”字,實在是匠心獨具。可惜這“一二三四五”沒過幾年便被換成了一句政治口號,盡管那是最為莊嚴最為普及的一句口號,但有的字卻比較難寫。大概是因為這些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理由,后來的地方教材又改為“工農兵”之類。等到前些年稚子入學時,我特別注意第一課,幸好,他們又回到了當年的“一”字上了。先祖為我們設計的表示萬物起源的“一”字,用于人生的第一課,實在是太適合孩子,太有容量,太能讓人回味了。
(摘自今晚網)
責編:徐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