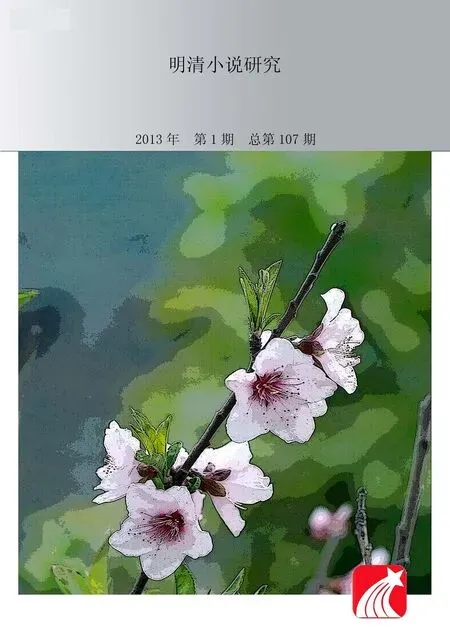論《水滸傳》文學性與語言形式的同構性
··
摘要本文試圖將《水滸傳》的文本放置于文學與語言交疊的領域,來考察其在文學特點與語言形式上所體現出來的同構性和一致性。通過對《水滸傳》的線狀情節結構、對比性人物塑造、全方位自由轉換的敘事視角的探討,結合對《水滸傳》前18回共計7740條句子的統計分析,本文認為,線狀的情節結構與流線性的動態施事句存在著焦點散落、線性發展的同構性;人物形象塑造重平行、比較,與耦合類的關系句重對偶、并舉則有著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致性;而全知全能的敘事方式與角度,與評論性主題句對范圍廣泛的話題選擇具有相似的自由度與靈活性。這說明,白話小說《水滸傳》能夠印證文學與語言具有一致性這個命題,并且提示我們突破傳統研究范式、探索文化與語言關系研究領域的新方向。
關鍵詞文學 語言 文本結構 句法結構 同構性
《水滸傳》是中國白話文學的里程碑。從其誕生之初至今,人們就以不同的視角和閱讀方式,挖掘著它在文學語境與語言范疇中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部成熟的白話小說,《水滸傳》的主題思想、社會背景、時代特點、政治倫理等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價值判斷,及情節結構、敘事模式、人物塑造、語言運用等藝術成就的得失估量,一直都伴隨著時代語境的變遷而始終成為“水滸學”研究的熱點。對于后進的研究者而言,如何超越傳統研究范疇,調整視角,建構新的研究模式,其意義并不亞于研究的本身。本著這一目標,本文試圖跨越文學與語言的界限,在二者交疊的領域內,對《水滸傳》進行文本分析,以探索其語言特征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蘊。
一、文學與語言的一致性
維特根斯坦曾經說過,“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①。如何理解這一命題?筆者以為,文學起源于人類的思維活動,是用語言文字表達社會生活和心理活動的藝術形式。從這個角度看,維特根斯坦這句話可以理解為:“語言代表著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代表著他們描繪世界的特有的眼光”。
關于語言與文學的關系,最經典的表達似乎可以用薩皮爾在《語言論》第十一章“語言和文學”中的有關論述來代表。薩皮爾認為,文學包括精神層面和語言表達層面,優秀的文學作品是“直覺的絕對藝術和語言媒介在內的特殊藝術完美地綜合”②,而與語言(語種)無關。他說:“語言是文學的媒介,正像大理石、青銅、黏土是雕塑家的材料。每一種語言都有它鮮明的特點,所以一種文學的內在的形式限制——和可能性——從來不會和另一種文學完全一樣。用一種語言的形式和質料形成的文學,總帶著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線條。”③薩皮爾還具體地指出了語言的因素對于文學的影響:“每一種語言本身都是一種集體的表達藝術。其中隱藏著一些審美因素——語音的、節奏的、象征的、形態的——是不能和任何別的語言全部共有的。”④這就是說,文學創作離不開語言,文學中的種種特質跟語言的特征密不可分。正如雕塑家用不同材料來塑造形象,造就了石像、青銅像、泥俑等雕塑作品,文學通過語言來描繪它的世界圖景,有多少種語言,就有多少種這樣的世界圖景,語言為文學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使文學成為豐富多樣的藝術表達模式和審美模式。
在文學與語言的關系上,羅蘭·巴特的表述更加直觀,他認為,“敘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質,但絕不可能只是句子的總和。敘事作品是一個大句子,如同凡是陳述句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小敘事作品的開始一樣”⑤,強調“語言和文學之間的一致性”。所謂語言與文學的一致性,筆者的理解是,一個文學作品的結構其實等同于一個句子的結構,一個句子如何選擇詞語,如何安排句子成分的順序,如何組織句子的結構,往往意味著一部作品對原始素材的選擇,對各類述題的排序,乃至對整個視野圖景的組織和架構。也就是說,一個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在敘述或描寫對象時,其詞句的選擇、語言的運用、表達的方式等等,必然與其對母語的感覺和領悟是一致的。例如:漢字的表意性及一字一音節的特性,使得漢語詩歌的字數可四言,可七言,句子可整齊可參差,語序靈活,音韻合樂,成為了一種重意境、有聲韻、可歌詠的文學品種。歷代詩歌作者正是憑借漢語的特性去感悟生活,探索生命意識,描繪他們眼中的世界景象。因此,漢語詩歌無論是絕句、律詩,還是楚辭、樂府詩,并不僅僅是語言技巧的產物,更是漢語的特性本身所帶來的多樣意趣和不同的審美力量。
文學作品需要傳達生活內容的信息,更要表現生活之上的精神特質,要蘊含感悟生活之美的審美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的語言既是工具、載體,又超越其上,具有了審美功能和民族文化的通約性。
二、《水滸傳》的線狀結構與線性施事句
《水滸傳》的結構特點,是“把許多原來分別獨立的故事經過改造組織在一起,既有一個完整的長篇框架(特別是到梁山大聚義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獨立意味的單元,可以說是一種‘板塊’串聯的結構。”⑥所謂“板塊串聯”,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線性結構。這種線性結構是以情節為中心的古典小說的典型結構特征。茲維坦·托多里夫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敘事的時間是一種線性時間,而故事發生的時間是立體的。在故事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則必須把他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一個復雜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條直線上。”⑦這種體現時間一維性的直線式敘事方法,往往成為史詩及古典小說中最為普遍的布局方式。寫事件,從發生、發展到全局;寫人物,由少年、成年到老年。例如:18世紀的英國啟蒙小說大多沿用了海上漂流的史詩及陸地旅行的流浪漢小說中遺留下來的情節結構模式,將客觀現實中人物直線運動的規律,固定為小說創作的結構模式。
《水滸傳》的線性結構同樣遵循時間的自然順序和事件的因果關系順序,將各個情節部分從頭至尾串聯起來,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結局。但中西方古典小說線性結構的不同之處在于:英國啟蒙小說中流浪漢式的主人公是貫穿首尾的,他們始終行進在情節主線上,成為故事的惟一焦點。而《水滸傳》的人物則是眾多的,一百零八將的座次雖然有別,但每個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經歷,每個英雄都有獨特的個性和特質,而他們奔赴梁山泊的動因則無一例外:官逼民反。于是,這些眾多人物的不同情節板塊猶如條條涓涓細流,在時間的流程上陸續匯入“官逼民反、梁山聚義”這一情節主線中。
以羅蘭·巴特的“敘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質”這一觀點來考察《水滸傳》的語言,我們會發現,《水滸傳》在敘事結構上的線性特點,也在其句法結構中大量地顯現。筆者對《水滸傳》前18回共計7740條句子的結構進行了逐條分析,分離出了4056條施事句,發現其中存在大量流塊狀的線性句。這些句子大多為多個動詞或動詞詞組鋪排而成的施事句,動詞或動詞詞組在意義上都與同一主語存在施-動關系,但它們之間無需關聯詞語連綴,甚至無需語音停頓,其結構形態與西方語言以一個動詞為焦點的主謂句句法結構形神迥異。例如:
1.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里來了。(4個動詞或動詞詞組)
2.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5個動詞或動詞詞組)
3.眾人吃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攧翻無數。(6個動詞或動詞詞組)
4.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7個動詞或動詞詞組)
5.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著,卻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8個動詞或動詞詞組)
6.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吃了,打拴了那包裹,撇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樸刀,又和小嘍羅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9個動詞或動詞詞組)
據我們統計,在7740條句子中,這種流水般的線性動句超過2000條,在施事句中所占比例甚至多于西方語言那種典型的“主-動”或“主-動-賓”結構的句子,其中7個以上動詞(詞組)連續鋪排的句子竟也達到了20條之多。這種流塊堆疊的線狀句子結構幾乎無法直譯成任何一種西方語言,說明漢語句子結構的組合視角具有漢民族的獨有特性。如同線性的敘事結構中散落著一百零八位人物,這種線性的句子結構也隨著時間的順序或事理邏輯的順序,引領讀者的視點不斷在鋪排的動詞之間遷移轉換,隨走隨停,從一個地方來到另一個地方,遭遇一個又一個的人物,參與一個又一個的事件,體現了重時間的線性運動的內在文化精神。正如文化語言學者申小龍先生所言:“漢語的流塊建構與漢民族其他文化藝術形式在‘流’態動感上具有通約性。我國古代的雕刻、書法與繪畫都不重視立體性,而注意流動的線條、飛動的美。于疾徐波折、自由流轉的線條之中透出勃勃的生氣和生命的旋律,于‘移視’中可體會它的流動氣勢。”⑧
三、《水滸傳》人物塑造的對稱性與句法結構的偶意
《水滸傳》塑造了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體現了傳統小說中群像設計及類型化的特點。作者在這些人物之間建立起一種平行、比較的關系,像武松的勇武豪爽,魯智深的嫉惡如仇,李逵的戇直魯莽,林沖的剛烈正直,都能夠同時得到渲染烘托,于對比中凸現完整而姿態各異的人物群像。
我們發現,在《水滸傳》的每一個章回中,出場的重要人物通常都是兩個,這從回目中也可見一斑,如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第十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第十七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第六十回“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等等。不僅人物的名號或綽號及地名兩兩相對,連事跡與事件也有偶合之功。這固然有漢字一字一音及表意性的特點所帶來的便利,但我們不能不說“偶合”的思維方式是造成《水滸傳》從人物形象到結構布局,乃至句式表達上趨于兩兩成雙的主要動力。試看第十三回楊志與索超比武一節對二人出陣前的描寫:
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正牌軍索超出馬,直到陣前兜住馬,拿軍器在手,果是英雄。……
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槍出馬,直至陣前,勒住馬,橫著槍在手,果是勇猛。……
再看第十三回對朱仝、雷橫出場時的描寫:
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
這馬兵都頭管著二十匹坐馬弓手,二十個土兵;那步兵都頭管著二十個使槍的頭目,一十個土兵。
這馬兵都頭姓朱名仝,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須髯,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云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疏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
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胡須。為他膂力過人,能跳二三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后來開張碓坊,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匾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
作者對楊志與索超、朱仝與雷橫的形象描寫與敘事構造,幾乎都是在一種左右(前后)對稱的框架內進行的,甚至詞語的選擇、字數和句數的鋪排,都呈現出一種整齊劃一、偶合對稱之勢,讓我們無法忽視作為一種思維定式的“偶意”,對于《水滸傳》形象設計、組織布局以至句法結構的影響。
在我們對《水滸傳》前18回所作的句型統計中,有著偶合之意的關系句達到了192條之多。例如:
1.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著兩眼淚。
2.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
3.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卻是一個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
4.隨著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抬頭看時,卻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
5.林沖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檐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
6.晁蓋卻去里面拿了個燈籠,徑來門樓下看時,士兵都去吃酒,沒一個在外面。
這些句子從語義上看,(加點文字)前后兩個部分都可以獨立成句,或者納入傳統語法中“并列復句”或“聯合復句”的范疇,然而細細品味,它們既無法在語感上斷開,也不能用“并列”、“聯合”一以概之。它們只有“兩兩成對,句意上互為映襯,節律上互為依托,才成一完整的表述單位”⑨。申小龍在他的漢語句型系統中將這類句子命名為耦合句,以“只見”、“看時,只見/果然/卻是”等為形式標記。
早在《周易》、《淮南子》等古籍中,中國古人辯證統一的思想就清晰可辨:認為太初之時渾然一體的元氣可判分為二,形成天地等物質實體。有天地,就有陰陽,陰陽分立而又相合,它們的運動貫串于各個方面,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呈現出矛盾雙方永不間斷、兩兩分而相合的狀態。“偶意”因此貫穿在中國各類傳統文學藝術(如詩歌、曲賦、戲曲、建筑)的精神氣質之中。而另一方面,漢字的表意及單音節特性又順應了這種“偶意”,為詞語構造、句子構造,乃至文本的組織構造提供了對偶、對稱的便利。可以說,漢語和漢字從產生伊始,就自然而然地為對偶創造了條件。
那么,漢民族是先有了“偶合性”思維方式,才有了漢字的特點,還是因為漢字特點造就了“偶合性”思維的慣性?這也許已經很難辨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對偶”、“對稱”早已成為漢民族組詞造句乃至安排文本結構時的一種慣用思維模式。因此,人物塑造、結構布局與大量“耦合句”在“對稱”、“偶意”上的一致性,在《水滸傳》中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實質上正是漢民族認識世界、感知世界的特有模式。
四、《水滸傳》的敘事角度與話題評論句式
《水滸傳》取材于民間傳承的歷史故事,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欣賞趣味。羅貫中、施耐庵雖是文人,但他們都曾在元末繁華的杭州城生活過,因此,他們對水滸故事的藝術加工仍然延續了宋元話本講史、說經的模式,留有說話藝術的痕跡。作者仿佛就是說話人,面對著聽眾,娓娓地講述著動人的故事給他們聽。這使得《水滸傳》的敘事方式與敘事角度帶有某種引導讀者(聽眾)的性質,表現在行文之中即為隨處可見的“話說”、“且說”、“但見”、“只見”、“話休絮煩”、“不在話下”、“看官聽說,有詩為證”之類的篇章語,這實際上就是說話人對聽眾所做的提示性語言。這種話本殘留遺跡在章回體小說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控制敘事的節奏,布局情節的走向,掌控讀者的注意力,便于作者于緊要關頭突然停下,設置懸念。于是,“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或“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就成了章回之間的程式化套語。
上述因素為《水滸傳》造就了中國傳統小說那種以全知視角自由轉換時空的特長。說到魯智深,視角就是魯智深的;說到林沖,視角便轉為林沖的;說到武松,讀者便隨武松喝酒、打虎、殺西門慶。這種敘事方式無需關注人物內心,只需聚焦外部信息,如人物之間的對話和行動,周圍的環境等等即可。當然,作為說話人的職責,作者還需不時地點評、議論、解釋,這是代替內部信息如心理活動、思想情緒的最好方式。
如人們談論最多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一節,作者就充分調動了視覺、味覺、聽覺諸感官的敘事角度,為讀者帶來了極為直觀的感受,可謂淋漓盡致的審美享受:
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醬油鋪:咸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味覺視角)
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脧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滾將出來。(視覺視角)
又只一拳,太陽上正著,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磐兒,鈸兒,鐃兒一齊響。(聽覺視角)
《水滸傳》這種敘事角度全方位的自由轉換,也可以在一類以評論話題為功能的句式中找到同構。按照申小龍建構的漢語句型系統,主題句是與施事句、關系句鼎足而立的一個大句類,具有名詞趨向,其功能主要在于評論,其句子焦點往往是一個話題。在主題句中,話題的范圍極為寬泛,如同移動的視角,視野所及,無論是人物、事物,還是事件、經歷,抑或屬性、特征,都可以成為評論的話題。因此,句子中的主題語(話題)可能是一個詞、一個詞組,甚至是一個句子。例如:
1.洪大尉倒在樹根底下,諕的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廝打,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卻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斗敗公雞,口里連聲叫苦。(主題語:洪太尉,人物)
2.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主題語:你,人物)
3.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主題語:那里,方位)
4.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主題語:小人房錢,事物)
5.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主題語: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并列短語)
6.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主題語: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并列短語)
7.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主題語:量些粗食薄味,句子)
8.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凈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污。(主題語: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同位語短語)
由此看來,《水滸傳》自由轉移的敘事視角和敘事方式,與主題句以評論話題為目標的功能具有很強的同構性。
在我們統計的7740條句子中,除去存現句、祈使句、呼嘆句、有無句、名詞句及篇章語句等小句類,施事句、關系句、主題句合計所占比例接近90%,其中施事句(含多段動詞句)4056條,關系句(含耦合句)1554條,主題句1250條。由于本文本分析只涉及《水滸傳》部分內容,而非窮盡性專書分析,所以各統計項目與窮盡性分析的結果可能會存在某些差異或出入,但我們相信,三大句類的基本格局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從文學與語言的一致性角度看,這似乎可以說明《水滸傳》的時代,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描述,更集中于對人物行為、事件發生等外部動態信息的關注,與此同時,人們對人物的評價、事件的評述等靜態信息也具有相當的興趣。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學的現代轉型,這一點在后世的小說(如《紅樓夢》、晚清譴責小說等)中可能會越發凸顯出來,這將是筆者進一步探索的方向。而漢民族在文本結構與語言組織模式中所體現的心理特點等文化精神內涵,同樣是我們在任何文本分析過程中無法忽略的因素。
注:
① [英]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頁。
②③④ [美]愛德華·薩皮爾《語言論》,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01、199、201頁。
⑤ [法]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見《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第2卷),胡經之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頁。
⑥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下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
⑦ [法]熱·熱奈特《敘事語式》,見《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頁。
⑧ 申小龍《當代中國語法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頁。
⑨ 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