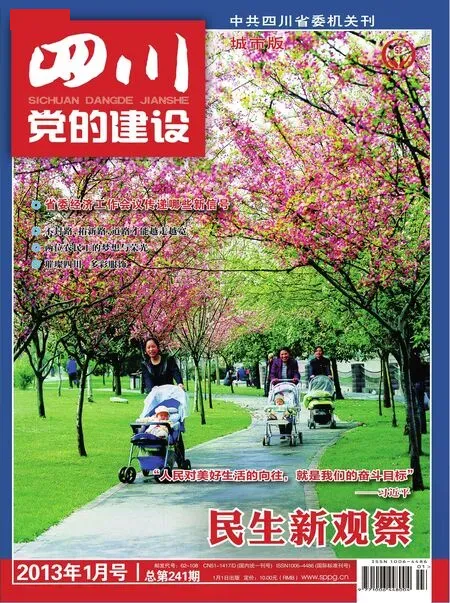國外公共空間的罰與教
□陶短房
最近,“中國式過馬路,就是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紅綠燈無關”成為熱門話題。其實,公共空間禁忌是個復雜的話題,遠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的,我們來看看國外在這方面的經驗。
許多國家在維護公共空間禁忌時,會采取罰款、甚至比罰款更嚴厲的措施,顯得毫不手軟。比如荷蘭,在安靜的公共汽車、列車和地鐵車廂里是不允許大聲打電話、接電話的,如果在列車的“安靜車廂”接電話,可能被罰款55歐元,倘在公共汽車上使用手機,而被司機認定干擾了自己的注意力,或被其他乘客投訴“可能干擾司機注意力、影響乘客安全”,就可能被課以80-120歐元罰款。
但在很多國家,“以罰代管”從整個公共空間禁忌管理范疇上看,仍然是少數的、局部的。且即便在實行罰款的地方,也存在著爭議和反復。
如在英國,許多輿論、公眾對各地市鎮當局繁瑣、苛細的罰款則例感到不便,認為不盡合理。不少人指出,這種細如牛毛的罰款對規范公共空間禁忌行為固然有所幫助,卻也給行政執法部門帶來巨大壓力:嚴格執法吧,要管的事和人實在太多,不但疲于奔命,也會造成公共開支的大幅上升,并影響對更嚴重社會問題的管理;網開一面吧,有法
不依,豈不是比無法可依更糟,一旦規范、法規成為一紙空文,后果同樣不堪設想。
在更多國家、城市、場合和范疇,公共空間禁忌的維護和遵守,依靠的不是嚴刑峻法,而是公眾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對公共道德的自覺遵守。
如在許多城市,“按信號過馬路”已成為習慣和默契,即便剛上學的孩子也知道不能在紅燈時過馬路,更不能隨意亂穿馬路;開門時讓女士先行、主動替后面的人扶門,這些“公共空間慣例”根本不成文,
但在很多地方是約定俗成的;在不少城市,公交車輛上并無明文規定不得吃東西、不得大聲喧嘩,但大多數人卻能自覺遵守;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廣人稀的國家,很多野營、野炊的場所平時根本看不見什么管理人員,但人們往往也能自覺遵守“規矩”,不吸煙、不飲酒,結束活動時將所產生的垃圾清理干凈。
道德和自覺并非從天而降,也不是靠簡單的說教就能養成,而需要各方面的引導,許多國家在這方面有好的經驗。
首先,要通過各種公共規則,讓遵守公共空間禁忌規則者感到處處方便、事事順利,而不遵守“規矩”者則處處別扭、寸步難行。
如按序排隊,“窗口”服務人員對“加塞”者都會“另眼相看”,讓他們非但不能“超近”,反倒成為最后一個獲得服務的人。
其次,設法讓違反公共空間禁忌規則者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迫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許多發達國家城市都規定“行人路面優先權”,不管行人是否違反交規,公共車輛都需讓行,但這些城市也同時規定,如果違規的是行人,一旦因不可抗力果真出事,行人自己要承擔全部責任。
再如針對公交逃票者,不少國家并不主要依靠罰款,而是通過個人信用系統“扣分”的方式進行約束,在信用社會,一旦個人信用分數被壓低,申請各種貸款、報考各種資格證明,都會處處碰壁,弄不好違規者就會買不起房、開不起車、上不起學,如此一來,誰想圖一時方便,就不得不多掂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