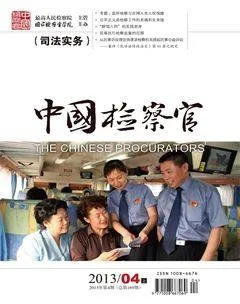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純正身份犯行為定性研究
有
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純正身份犯行為定性,由于同時涉及犯罪主體和共同犯罪兩大傳統刑法理論難題,一直以來都是理論界和實務界爭論的焦點。對此問題的正確分析和認識,不但會幫助我們厘清一些存在模糊認識的刑法基本理論問題,而且也會促使研究的深入,為司法實踐提供引導。
一、身份犯概述及其共同犯罪問題的提出
所謂身份犯,也即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實施的犯罪。根據身份在具體罪名的定罪和量刑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將身份犯分為純正的身份犯和不純正的身份犯。不純正身份犯由于對犯罪主體沒有特定的要求,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的共同犯罪認定不存在爭議。純正身份犯中,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由于侵害的是同一法益,因此也不會產生定性爭議。而在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場合,由于可能同時侵害不同的法益,或者僅有一人的行為直接侵害了法益,因此可能存在罪名認定上的爭議。具體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情形:一是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都具體實施了構成要件的行為;二是有身份者實施了構成要件的行為,無身份者僅實施了共犯行為;三是無身份者實施了構成要件的行為,有身份者僅實施了共犯行為。在第二種情形下,根據共同犯罪的從屬性理論,可以將無身份者的共犯行為納入修正構成要件中考慮,其行為的定性以對有身份者行為的評價為準,這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的認識是較為一致的。但需要說明的是,實踐中也存在將無身份者的共犯行為單獨定罪的司法判例。例如,行為人將他人的肢體故意損傷,然后指使其“碰瓷”詐騙,有的法院將行為人直接以故意傷害罪定罪。實際上,這屬于共犯行為同時構成其它罪名的構成要件行為的特殊情形。由于實行行為具有相對性,此罪中的幫助行為可能是彼罪的實行行為,為實現罪刑相適應的目的,可以采用競合犯理論,對行為人的行為擇一重罪處罰。但是,在行為人的共犯行為不能單獨構成犯罪時,則不存在上述問題。至于上述第一種情形和第二種情形,由于同時涉及對實行行為、犯罪主體、共同犯罪等一系列傳統刑法理論難題的理解,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而對這些問題的正確分析和認識,不但會幫助我們厘清一些存在模糊認識的刑法基本理論問題,而且也會促使研究的深入,為司法實踐提供引導。
二、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的定性問題
解決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定性問題的關鍵前提在于如何評價無身份者的行為,也即在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的情形下,無身份者實施了與有身份者在形式上一樣的行為,在法律上能否認定為特定構成要件的行為,即能否認定無身份者為實行犯?
肯定說認為,無身份者可以構成純正身份犯的實行犯。如日本學者大谷實教授認為,由于沒有身份的人也可以通過參與有身份的人的實行行為來實現真正身份犯罪,所以,如果沒有身份的人和有身份的人共同參與實施犯罪的話,就成立共同正犯。否定說認為,身份犯必須以有身份者的行為為前提,無身份者作為實現構成要件事實的參與者,可以構成教唆犯或者幫助犯,不能成為身份犯的實行犯。折中說認為,對此問題不能構一概而論,而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凡無身份者能夠參與純正身份犯的部分實行行為的,可以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實行犯;凡無身份者根本不能參與身份犯的實行行為的,不能成為純正身份犯的實行犯。[1]
本文同意上述否定說的觀點,認為在特定身份犯中,身份不但決定著犯罪主體的性質,更反映了犯罪的本質,非身份者可能實行與有身份犯在形式上同樣的行為,然而其可能侵害的法益卻因為身份要件的缺失而與純正身份犯不同,因此應當根據其具體情況定其他的罪名或者宣告無罪。但是,誠如上述肯定說與折中說所論述,確實存在部分純正身份犯的部分行為可以由無身份者實施的現象,例如在復行為犯中,就存在目的行為由有身份者實施,而手段行為則可能由無身份者實施的現象。解釋這種現象,除了堅持上述否定說的觀點之外,還需要對刑法中的實行行為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實行行為是一個具有一定爭議的概念,對此存在形式說、實質說、形式與實質統一說等三種主張。形式說認為實行行為是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實質說認為實行行為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而形式與實質統一說則主張結合刑法規定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綜合認定實行行為。本文認為,形式說雖然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則,但由于其本身過于抽象,不具有實際操作性;實質說道出了實行行為的本質,但如若沒有形式概念的限定必然會導致法律虛無;只有形式與實質統一說兼顧了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也符合認識的一般特征。就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而言,雖然無身份者可能也實施了部分與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在形式上一樣的行為,但是從實質角度考慮,其直接侵害的客體并非純正身份犯所要求的特定客體。眾所周知,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犯罪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對犯罪行為處以刑罰的理論支承點,但是刑法規定了不同的犯罪構成,其意義便在于將侵害法益的犯罪具體化與類型化。在純正身份犯的場合下,犯罪主體的特殊身份與一定行為結合,說明了該行為所侵害的特殊法益和行為所表現出的特殊社會危害性,從而影響到行為人對特定犯罪刑事責任的有無。此外,也有學者從自然意義上的行為與法律意義上的行為區分的角度對無身份者不能成為純正身份犯共同實行犯的命題進行了論證。認為對共同犯罪中實行行為的評價應當是規范意義、法律意義的,而不能是自然意義上的。非身份者好像可以實施作為純正身份犯中的實行行為,實際上該實行行為只有特定的有身份者實施才屬于該特定犯罪的實行行為,超出此范圍就不再是特定犯罪意義上的實行行為。純正身份犯的本質在于行為人根據其身份而承擔了一定的義務,身份的連帶性不能超越純正身份犯的本質。[2]可能有人會這樣提出質疑,既然是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了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那么其必然共同侵害了特定的客體,因此無身份的行為也具有實質的內容,應當認定為實行行為。本文并不否認上述情況下,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的行為共同侵害了純正身份犯的特定客體,但是對于無身份者而言,其對特定客體的侵害是基于對有身份者行為的作用,而非其直接侵害了特定客體。因此,對于無身份者而言,其行為在純正身份犯共同犯罪范圍內,只能是共犯行為,而非實行行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在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都具體實施了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的情況下,如果無身份者的行為無相對應的其它犯罪構成,則其僅能構成純正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幫助犯或者教唆犯,但是在具體衡量其刑事責任時,可以依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認定其為主犯、從犯或者脅從犯。但如果無身份者的行為同時符合其它犯罪構成,則在認定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構成純正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基礎上,基于罪刑相適應的考慮,依據競合犯罪理論對無身份者的行為從一重罪處罰。
三、共同犯罪中,有身份者沒有實施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的定性問題
在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犯罪中,可能存在純正身份犯的構成要件行為由無身份者具體實施,而有身份者僅實施了教唆、幫助以及組織等行為的情形。例如在保險詐騙罪中,保險合同法律關系人教唆或者幫助非保險合同法律關系人具體實施夸大保險事故損失并騙取保險金等一系列保險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此種情況下的定性問題,由于涉及間接正犯、共同犯罪等一系列理論命題,存在較大的爭議。由于教唆、幫助及組織行為相對于實行行為而言同屬于共犯行為,而教唆行為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特殊性,為行文方便,本文便以有身份者的教唆行為作為主要分析對象。
對于有身份者教唆無身份者實施純正身份行為,以無特定身份人是否符合其它罪的犯罪構成為標準,可以分為無身份者不可以構成其它犯罪和無身份者的行為同時符合其它罪犯罪構成兩種情形。在無身份者不可以構成其它犯罪的情形下,有身份者的行為屬于利用他人不構成犯罪的行為達到自己的犯罪目的,此時無身份者的行為對于有身份者而言具有工具性的意義,有身份者構成純正身份犯的間接正犯。如果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在行為過程中產生了共同實施純正身份犯行為的犯意聯絡,則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犯罪,實行行為是有身份者的間接正犯行為,無身份者僅能構成共犯行為。例如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教唆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家人代為收受錢財,并為他人謀利益的行為。這種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屬于受賄罪的間接正犯,雖然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家人具體實施了形式上符合受賄罪構成要件行為的“收受他人錢財”,但也只能視為受賄罪的幫助犯。然而,如果無身份者并不具有實施純正身份犯的犯罪意思,完全是被有身份者利用,則無身份者僅僅是被有身份者利用工具,因為主觀上無犯意而在刑法上不予評價。
至于有身份者教唆無身份者實施純正身份行為,無身份者的行為同時符合其它罪犯罪構成的情形,例如無身份者實施的保險詐騙行為,便同時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評價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的共同行為,存在以下分歧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有身份者教唆無身份者實施某種犯罪行為,在兩者都可以構成不同犯罪的情況下,有身份者只能構成無身份者的教唆犯[3];第二種觀點認為,有身份者教唆無身份者實施某種犯罪行為,在兩者都可以構成不同犯罪的情況下,有身份者構成相應的純正身份犯的教唆犯,而不能構成無身份者的犯罪[4];第三種觀點認為,在上述情況下應當區別兩種不同的情形:如果有身份者利用了本人的身份,例如國家工作人員教唆非國家工作人員去盜竊自己保管的公共財物,非國家工作人員構成盜竊罪,而國家工作人員構成盜竊罪的教唆犯,又構成貪污罪的間接正犯,對其應根據想象競合的處理原則,以重罪—貪污罪論處;對于有身份者沒有利用本人身份的,例如國家工作人員教唆非國家工作人員去盜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保管的公共財物,非國家工作人員構成盜竊罪,對國家工作人員應以盜竊罪的教唆犯論處。[5]第四種觀點認為,在上述情況下,對有身份者應當以純正身份犯的間接正犯定罪,而對被教唆者則以純正身份犯的從犯處之。
上述第一種觀點片面、僵化地理解了對純正身份犯的認定。固然在有身份者教唆無身份者實施純正身份犯的情況下,有身份者并沒有實行特定純正身份犯罪的構成行為,但是其畢竟其與無身份者結合共同完成了同一犯罪行為,無身份者也正是基于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條件方完成犯罪的,而且整個犯罪行為也確實侵害了特定純正身份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因此對有身份者一概以無身份者構成的犯罪的教唆犯論處是不合適的。第二種觀點則是過于寬泛地理解了純正身份犯的認定,其承認有身份者構成教唆犯便意味著認可了無身份者行為屬于純正身份犯的實行行為,這與前文已經論述的無身份者不能成為純正身份犯的實行8b9418d246c7d3260d0d137683bfbd1206dc2b06ef1e517a01ef6c67232f856a犯的判斷是相悖的。上述第三、四種觀點引入了間接正犯的理論,都承認在有身份者教唆無身份者實施純正身份犯罪的情況下,應當認定有身份者為純正身份犯的間接正犯,但是在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在何種范圍內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上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本文主張,對于有身份者教唆無身份者實施純正身份行為,如果無身份者的行為同時符合其它罪犯罪構成,則需要在厘清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主觀故意的基礎上,確定兩者在何種范圍內構成共同犯罪關系,并以此決定對兩者刑事責任的認定。如果無身份者并無實施純正身份犯的主觀意圖,完全是被有身份者利用,則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在一般犯罪的意義上構成共同犯罪,但是對有身份者應當以純正身份犯認定,而對無身份者則以其可能單獨構成的犯罪定罪處罰。例如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教唆、幫助不具有保險詐騙故意的非保險合同法律關系人實施夸大保險事故損失、騙取保險金的行為,則兩者在詐騙罪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關系,但是有身份者應當以保險詐騙罪論處,無身份者僅構成詐騙罪。然而在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在行為過程中產生了共同實施純正身份犯行為的犯意聯絡的情況下,僅僅以一般犯罪的構成要件已經不能夠完整的評價無身份者的行為,應當納入與有身份者純正身份犯共同犯罪范圍內予以考慮。此時,無身份者的行為對于有身份者而言具有工具性的意義,因此有身份者構成純正身份犯的間接正犯。而對于無身份者,其雖然實施了與純正身份犯構成要件行為形式上一致的行為,卻并不能被評價為純正身份犯的實行行為,應當認定為共犯行為。但是,由于無身份者的行為畢竟同時符合其它罪的犯罪構成,如果僅以純正身份犯共犯行為評價可能會產生罪行不相適應的問題,為此,可以依據競合犯的理論,從一重罪處罰。
注釋:
[1]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頁。
[2]陰建峰:《共同犯罪適用中疑難問題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9頁。
[3]馬克昌:《共同犯罪與身份》,原載于《法學研究》1986年第5期。
[4]吳振興:《論教唆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頁。
[5]陳興良:《共同犯罪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