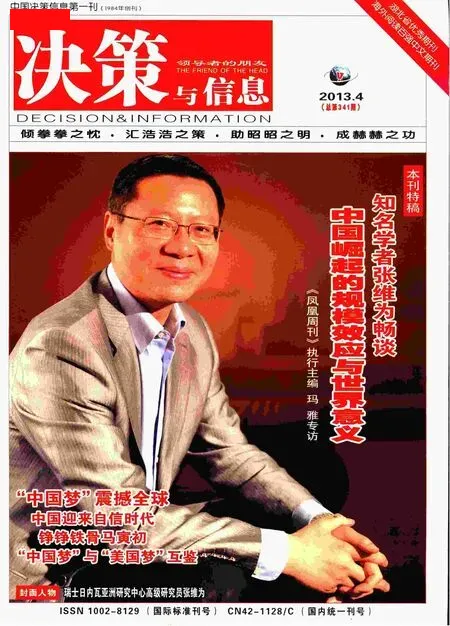中國“紅利家族”剖析
常修澤
(作者: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改革紅利”成了人們議論的話題。如果從更高的層次和更廣闊的視野來思考問題,研究中國的改革紅利,首先應研究由諸種紅利構成的“紅利家族”,特別是“紅利家族”內部的關聯性問題。
“紅利家族”內部成員有何關聯
“紅利家族”內部的分類,就其各自能量變動趨勢而言,至少可分為三組:
第一組,能量趨于“枯竭”的紅利。這其實也是指過去三十多年我們發展所“吃掉”的紅利,或者說所付出的沉重代價。比如資源紅利和環境紅利,過去依靠大量耗費資源、嚴重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如今造成了“天怒人怨”的惡果,表明這兩種紅利到現在已近于枯竭。最近,京津冀地區的漫天霧霾,已經宣告了這條發展思路、這種發展方式的破產。
第二組,能量正在變弱的紅利。包括勞動力(數量)紅利和出口紅利,這兩個紅利雖然還有,不能說完全枯竭,但都在逐步變弱。
第三組,能量需要大大釋放的紅利。我重點關注兩個:一個是改革的紅利,一個是技術的紅利。現在中國正面臨“第三波歷史大轉型”。根據筆者幾年前的研究結論,所謂“第三波歷史大轉型”,是指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資源環境制度的全面轉型。同時,當前中國也正處在人類“第三次產業革命”的過程中。
更重要的是,這兩個“三”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要研究這兩股浪潮的交匯性和對接性,特別要認識到:這兩股浪潮不僅將對中國經濟發展——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增長格局、經濟結構以及經濟體制——構成重大影響,而且也將對中國社會——包括社會進步、社會結構、社會發展方式和社會體制——產生深遠影響。兩個“三”背后的兩大紅利,是值得中國著重挖掘和釋放的。對此,要特別予以關注。
“五點一線”:尋求制度創新的紅利
什么叫制度創新的紅利?或者說,到底怎么樣界定“改革紅利”的內涵?這涉及提出這一命題貫穿的思想邏輯問題。據我看到的材料,一些論者提出“改革紅利”的命題似出于增長主義的邏輯,其切入點是“經濟增長”問題——在人口紅利、資源環境紅利,乃至全球化紅利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減弱,或消解)之后,如何尋求經濟增長新的動力。如果僅就研究中國未來潛在經濟增長率這一角度來說,探討如何尋求經濟增長新的動力,包括“改革紅利”,是很有意義的。問題是,僅僅這一層面的考慮夠不夠?
十八大明確提出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總格局。如按“五位一體”總格局來思考“改革紅利”內涵,其涉及的領域相比增長主義的邏輯,是否更加寬闊些?
我給的涵義是,改革紅利是通過改革或稱制度創新,促進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的進程,使其成果為全體人民所共享,最終落腳到每個人自身的發展上。
具體而言,包括“五點一線”,即五個要點,一條線索:
第一,經濟轉型。包括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結構轉型等,核心是市場化與實現社會公正的平衡,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并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社會共生。核心是尋求社會各階層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能出走,中產階層必須擴大。
第三,政治變革。核心是民主與法制,這將愈發成為今后改革的關鍵,包括政府體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敗當中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推進、黨內民主制度建立等。
第四,文明交融。也就是多元文明的交融,重點是促進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融合,避免文明的沖突。
第五,天人合一。環境產權、環境政治、環境穩定以及生態文明問題,環境產權實質是環境人權。
五個要點,拿什么貫穿呢?或者說落腳到哪?答案是每個人自身的發展。馬克思在闡述新社會的本質要求時明確指出,新社會是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改革開放對中國最深刻的意義,應該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增強農民、進城務工者、企業職工以及社會方面的“主體性”,增進全體公民的社會福祉。這應是“改革紅利”的真諦。要有這樣一個宏觀視野,這樣一個“人本導向”的觀照。
紅利釋放的波動曲線: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改革紅利”并非今天才有。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實際上這個紅利的釋放呈現一個波動過程。我建議,將來應按照上述我的“五點一線”論,分別賦予相應的權重,經科學計算,做出紅利曲線圖。根據我的經驗,初步判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曾經有獲得過“改革紅利”較多的時候,但也有“改革紅利”微薄的時候,甚至有“改革紅利”負能量的時候。
具體說,過去三十多年里,有三次比較大的改革紅利高潮,以及兩次比較嚴重的改革紅利低潮。
第一次改革紅利高潮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期。這一段是改革開放紅利釋放得比較好的時期,特別是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農民的積極性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到中共十三大時達到了高潮。
第二次改革紅利高潮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提出以后,改革開放的力度明顯加大,改革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展開,這一時期紅利比較多。
第三次改革紅利高潮是本世紀初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開始全面進入了全球化的軌道,開放倒逼著中國改革,帶動了不少實際性的改革舉措。
而改革紅利低潮方面,可以說有兩個。一個是1989年至1992年初,這三年多的時間,中國整體是一個改革的低潮,紅利很少,甚至是負的紅利;另一個低潮期是前幾年有一段時間,行政權力明顯地介入市場經濟活動,改革紅利有所減少,雖然有客觀原因,也不能排除主觀上的一些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經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頭”。在改革的“戰車”跨越邊緣性障礙之后,現在需要推進到核心部位的“堡壘”面前。在改革遠未完成的情況下,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潛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重在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對紅利釋放的掣肘
從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推進下一步改革,迄今已經一段時間,人們對改革多有期待。但當前面臨的現實是,由于固化的利益格局的羈絆、掣肘,新一輪改革依然“舉步維艱”。能否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以形成一個人們所說的改革路線圖,正成為社會多方面的迫切期盼。
固化的利益格局對紅利釋放的阻遏、掣肘非常嚴重。這里面非常復雜:我們現在碰到的是一個很大的網,它羈絆著改革,掣肘著改革,以致很難釋放這個紅利。到底這個路怎么走,怎么樣真正地突破現行的僵化的利益格局,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只有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將利益關系調整到位,改革才能真正體現公平正義,才能贏得更為廣泛的社會共識和社會支持,并激發新的改革動力,改革才會有實質性進展。如果不講此邏輯,自覺或不自覺地搞實用主義,到頭來改革難免扭曲變形。
李白詩云:“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中國改革開放的潮流是不可復回的,我們期待著第四次紅利高潮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