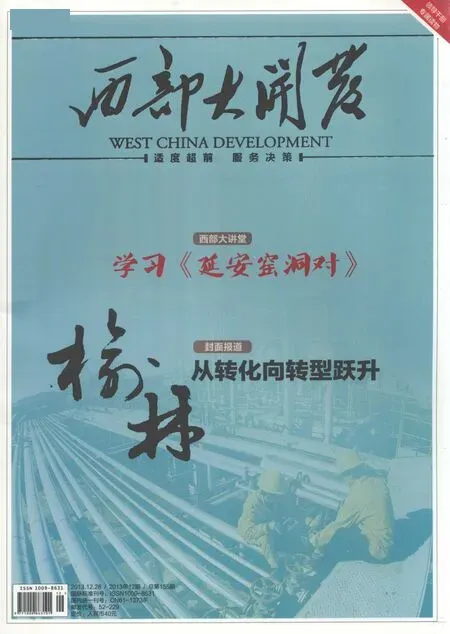華亭縣“一窩蜂”行賄縣委書(shū)記
華亭縣“一窩蜂”行賄縣委書(shū)記
甘肅省平?jīng)鍪腥A亭縣前縣委書(shū)記任增祿的貪污腐敗引發(fā)一場(chǎng)政界地震,同案牽涉129名同僚和下屬,幾乎完整覆蓋了該縣縣委、縣政府各部門(mén)以及各鄉(xiāng)鎮(zhèn)政府機(jī)關(guān),涉案金額超過(guò)千萬(wàn)元,交織出一張觸目驚心的腐敗網(wǎng)絡(luò)。
華亭縣,位于甘肅省東部、陜甘寧交界處,是平?jīng)鍪薪?jīng)濟(jì)最發(fā)達(dá)的縣城。倚賴(lài)其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華亭的煤炭存儲(chǔ)量居于全省之冠,素有“煤都瓷鎮(zhèn)”之稱(chēng),是甘肅省內(nèi)唯一進(jìn)入中國(guó)西部百?gòu)?qiáng)縣(市)的縣份。
2009年7月,任增祿擔(dān)任華亭縣委書(shū)記。
任增祿升遷之路
1982年7月,任增祿作為高考恢復(fù)后的首批大學(xué)生,自甘肅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專(zhuān)業(yè)畢業(yè),被分配到莊浪縣農(nóng)技中心。這一專(zhuān)業(yè)對(duì)口的大學(xué)生身份,在上世紀(jì)80年代的小縣城非常惹眼,這使得任增祿在八年時(shí)間內(nèi)成為莊浪縣農(nóng)牧局副局長(zhǎng)。之后他又用三年時(shí)間,當(dāng)上了莊浪縣的農(nóng)委主任。
1995年,中共中央下發(fā)《關(guān)于抓緊培養(yǎng)選拔優(yōu)秀年輕干部的通知》。為了充實(shí)領(lǐng)導(dǎo)干部梯隊(duì)的戰(zhàn)略部署,這次通知不僅強(qiáng)調(diào)了年輕干部的科學(xué)文化素養(yǎng),還要求“是勝任本職工作的內(nèi)行”,也明確要求在縣級(jí)黨政領(lǐng)導(dǎo)班子中,35歲左右的干部應(yīng)有一定數(shù)量。乘著這一提干“東風(fēng)”,任增祿在1997年升任莊浪縣副縣長(zhǎng)。
在任增祿的履歷表中,這是非常關(guān)鍵的一步,意味著他已經(jīng)不再只是一名農(nóng)口上的普通官員,而是在37歲進(jìn)入了一個(gè)綜合性的領(lǐng)導(dǎo)崗位。這樣的直接晉升在基層并不多見(jiàn),按照縣級(jí)官場(chǎng)升遷的一般路徑,從副局長(zhǎng)到副縣長(zhǎng),中間往往要經(jīng)過(guò)一次鄉(xiāng)鎮(zhèn)一把手的鍛煉。
之后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任增祿的仕途一片舒坦:2003年,他調(diào)任平?jīng)鍪修r(nóng)牧局副局長(zhǎng)、市農(nóng)科所黨委書(shū)記、所長(zhǎng)。2005年,中央開(kāi)始深化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當(dāng)年12月,任增祿來(lái)到華亭,出任中共華亭縣委副書(shū)記、代縣長(zhǎng)。2009年7月,任增祿升為華亭縣委書(shū)記,39歲的任增祿成為中國(guó)1600余位縣委書(shū)記之一。2011年11月19日選舉任增祿為平?jīng)鍪械谌龑萌嗣翊泶髸?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副主任。
共罪結(jié)構(gòu)集體腐敗
一個(gè)小小縣域,共有129名官員向縣委書(shū)記行賄,為什么涉及那么多官員?他們的訴求是什么?他們有著怎樣的身份?行賄之后他們又得到了怎樣的回報(bào)?
根據(jù)任增祿案司法材料,129名涉事官員的行賄目的主要分為:為其工作提供便利、為其職務(wù)調(diào)整提供幫助、為其職務(wù)升遷提供幫助、推薦副縣級(jí)后備干部、將其親戚安排到華亭縣城工作、提供招商引資關(guān)照這六大類(lèi)。
在上述六大類(lèi)中,最多系當(dāng)事人希望任增祿能為其職務(wù)升遷提供幫助,共有60人次,占總體近三分之一;其次系當(dāng)事人希望任增祿能為其職務(wù)調(diào)整提供幫助,共有44人次,占到總體近五分之一;接下來(lái)依次——為其工作提供便利、提供招商引資關(guān)照、推薦副縣級(jí)后備干部,以及將其親戚安排到華亭縣城工作。
根據(jù)司法材料和公開(kāi)資料,這些通過(guò)行賄訴求職位變動(dòng)調(diào)整的干部,最后都實(shí)現(xiàn)了個(gè)人目的,在行賄時(shí)間段里均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調(diào)職與提拔。
以華亭縣硯峽鄉(xiāng)原黨委書(shū)記朱維忠為例,2006年春節(jié)前至2010年春節(jié)前,其向任增祿前后行賄11萬(wàn)元——與此相對(duì)應(yīng),在此期間,他的職務(wù)也經(jīng)歷了自華亭縣交通局局長(zhǎng)(2008年)至硯峽鄉(xiāng)黨委委員、書(shū)記(2009年8月)至縣編委辦主任(2010年12月)再至縣委組織部副部長(zhǎng)的多次轉(zhuǎn)變。
又如華亭縣規(guī)劃局局長(zhǎng)馬驥,在2006年春節(jié)前至2011年9月期間,曾先后向任增祿行賄7.8萬(wàn)元。與此相對(duì)應(yīng),2007年7月起,其職務(wù)從鄉(xiāng)調(diào)任農(nóng)牧局黨委書(shū)記、局長(zhǎng),隨后歷任縣糧食局黨委書(shū)記(2009年11月)、縣糧食局黨總支書(shū)記(2010年8月)、縣規(guī)劃局局長(zhǎng)(2011年4月)。
在這個(gè)賄賂樣本中,部分干部的行賄目的存在多樣性,比如他們的賄賂訴求同時(shí)包含希望能獲得工作便利,以及獲得職務(wù)升遷。這種情況,在總體中占到21起。
首先,明確縣委書(shū)記的權(quán)力邊界,明確縣委書(shū)記和縣委、縣政府的關(guān)系,各負(fù)其責(zé)、互相制約。其次,出臺(tái)具體措施限制縣委書(shū)記的權(quán)力。對(duì)重要項(xiàng)目、重點(diǎn)工程、人事安排使用實(shí)行議決權(quán)和否決權(quán)分離。第三,加強(qiáng)對(duì)縣委書(shū)記的同級(jí)監(jiān)督、上級(jí)監(jiān)督、包括老百姓在內(nèi)的社會(huì)監(jiān)督等。
如何解決縣委書(shū)記不再成為腐敗、高危崗位,李永忠認(rèn)為需要改革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和選人用人體制,目前比較好的方法是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黨代會(huì)常任制的改革。
黨代會(huì)常任制提出后因種種原因中斷,目前一些地方在先后開(kāi)展試點(diǎn)。李永忠建議,進(jìn)行黨代會(huì)常任制改革,黨代表中領(lǐng)導(dǎo)干部的比例應(yīng)不高于60%。在現(xiàn)有的黨內(nèi)權(quán)力架構(gòu)內(nèi),讓黨代會(huì)常任制直接與黨的全委會(huì)對(duì)接,成為黨的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黨的常委會(huì)成為黨的執(zhí)行機(jī)關(guān)并更名為執(zhí)委會(huì)或書(shū)記處;黨的紀(jì)委會(huì)成為黨的監(jiān)督機(jī)關(guān)。執(zhí)委會(huì)與紀(jì)委會(huì)共同向黨的全委會(huì)負(fù)責(zé),黨的三個(gè)委員會(huì)共同向黨代會(huì)報(bào)告工作。選擇有條件且將要換屆的市、縣進(jìn)行黨代表直選。通過(guò)發(fā)展黨內(nèi)民主推動(dòng)和促進(jìn)民主的發(fā)展,實(shí)現(xiàn)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三個(gè)權(quán)力相互制衡,減少因決策失誤或權(quán)力失衡造成的損失。
(本刊編輯劉建據(jù)中國(guó)財(cái)經(jīng)網(wǎng)、《財(cái)經(jīng)》整理)
在行賄的129名官員中,行賄額最高的為48.2萬(wàn)元,最低為2800元。其中前者來(lái)自華亭工業(yè)園區(qū)前黨委書(shū)記王愷昀。在華亭,由于該工業(yè)園區(qū)直屬省級(jí),工業(yè)園區(qū)的一把手便屬于副縣級(jí)干部。調(diào)職到工業(yè)園區(qū)前,王愷昀已經(jīng)在縣政府辦公室主任這個(gè)科級(jí)位子上服務(wù)了三任領(lǐng)導(dǎo),是任增祿突破了他的升遷瓶頸:2009年7月王愷昀被提拔至華亭工業(yè)園區(qū)主任、2010年12月其繼續(xù)得到提拔,擔(dān)任工業(yè)園區(qū)黨委書(shū)記一職。為了感謝任增祿在提拔升遷上的照顧,王愷昀在2008年至2012年春節(jié)前,先后向任增祿行賄48.2萬(wàn)元。
最低的一筆行賄額則來(lái)自華亭縣檔案局局長(zhǎng)甘毓芳,2008年春節(jié)前至2010年春節(jié)前,任增祿收受其賄賂2800元,為其提供工作便利。
雖然每名干部的行賄數(shù)額不同,但結(jié)合行賄目的分析可知,行賄事由與行賄數(shù)額之間存在相關(guān)性,縣級(jí)的政治賄賂呈現(xiàn)出“市場(chǎng)化”局面。
其中,以希望任增祿提供工作便利、幫助親戚安排工作的行賄額最低,平均數(shù)額為1.8425萬(wàn)元與2.25萬(wàn)元;以提供招商引資關(guān)照、推薦副縣級(jí)后備干部為最高,平均數(shù)額為9.7263萬(wàn)元與8.2萬(wàn)元。同類(lèi)行賄的數(shù)額差距十分接近,基本上形成了一個(gè)固定的“市場(chǎng)價(jià)格”。
當(dāng)行賄人一次行賄存在多個(gè)目的時(shí),其對(duì)應(yīng)的行賄數(shù)額也會(huì)水漲船高,吻合了“給多少錢(qián),辦多少事”的潛規(guī)則。
如果對(duì)華亭的行政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縱向解剖,第一分支可以分出縣委、縣政府、縣政協(xié)、縣人大、人民團(tuán)體、鄉(xiāng)鎮(zhèn)、人武部門(mén)以及檢法兩院。將此案中的行賄名單對(duì)照該行政結(jié)構(gòu)觀察,結(jié)果令人咋舌——在所有的第一分支中,僅人武部門(mén)和檢法兩院沒(méi)有工作人員在行賄名單上,而縣委、縣政府以及各鄉(xiāng)鎮(zhèn),是發(fā)生賄賂的重點(diǎn)受災(zāi)區(qū)。
這些行賄人員主要以各部門(mén)的黨政一把手、局長(zhǎng)或主任等科級(jí)、副科級(jí)干部崗位為主。還有五位副縣級(jí)干部也在此列,其中有三位是政協(xié)常委委員,兩位是人大常委會(huì)委員。
大部分行賄人無(wú)恙
2013年6月18日,此案在甘肅省蘭州市一審宣判。蘭州市中級(jí)法院審理查明,2005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增祿利用職務(wù)之便共收受賄賂款、物折合人民幣991萬(wàn)余元,另有411萬(wàn)余元巨額財(cái)產(chǎn)來(lái)源不明。其中,129名華亭官員的名字被列入任增祿案判決書(shū)中,129筆賄賂主要涉及干部任命、人事調(diào)整、工作調(diào)動(dòng)、職務(wù)升遷等,為廣義的“買(mǎi)官賣(mài)官”行為。任增祿因兩罪并罰,被判處無(wú)期徒刑。
在行賄與賄賂呈現(xiàn)幾乎令華亭黨政機(jī)構(gòu)全軍覆沒(méi)時(shí),這129名涉事干部,只有極少數(shù)進(jìn)入司法程序,其中4名最終受到審判。
這四人分別是王愷昀、王華、陶玉宏和趙崗。被查處之前,他們分別擔(dān)任華亭工業(yè)園區(qū)委員會(huì)主任、華亭縣東華鎮(zhèn)鎮(zhèn)長(zhǎng)、華亭縣教育局局長(zhǎng)以及平?jīng)鍪谐墙ň指本珠L(zhǎng)。
據(jù)法院認(rèn)定,陶玉宏同時(shí)觸犯受賄罪與行賄罪,一審被判有期徒刑12年;王愷昀同時(shí)觸犯貪污罪、受賄罪與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6個(gè)月;王華與王愷昀罪名相同,最終數(shù)罪并罰被執(zhí)行有期徒刑10年;趙崗的判決,目前法院未能公開(kāi),據(jù)記者了解,其亦同時(shí)觸犯受賄罪與行賄罪,最終獲刑8年。這四名隨著任增祿一同落馬的官員,一審判決后都未提出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