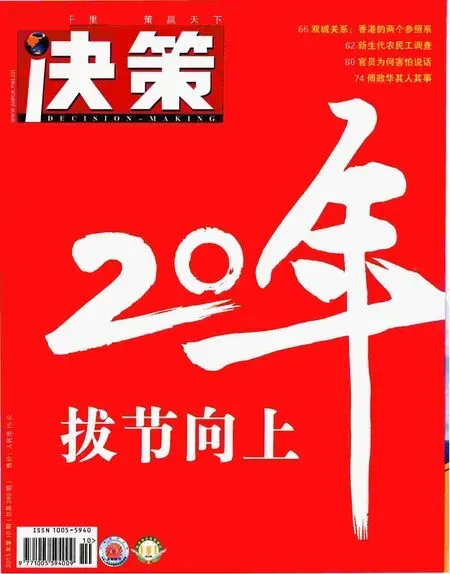智庫:追問與解題
■查 英
1994年,胡鞍鋼和厲有為的“特區之爭”令許多人記憶猶新。
作為“智囊”,胡鞍鋼影響高層決策的事件遠不止這場特區爭論。論戰之前,他的兩部成名作《生存與發展》和《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就曾引起決策者高度關注。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全體調閱了《生存與發展》報告,而《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則成為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參考依據。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是胡鞍鋼現任職務,從1999年他創辦該中心以來沒有變過。
從一個人到一個團隊,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已成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智庫。取代昔日幕僚、文膽、智囊,智庫業已成為影響決策過程的重要因素,在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上世紀90年代,有一份關注戰略發展和宏觀管理的知名刊物《戰略與管理》,當時圍繞著這份刊物所形成的作者隊伍,如杜潤生、王逸舟、林毅夫等一大批知識分子,被看做一個松散的“智庫”。更早一點出現的“智囊機構”則是80年代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其成員調研形成的報告,為1981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準備了系統全面的第一手農村調查數據。特定的年代,另有一部分有識之士通過新聞媒體“內參”的模式影響過高層決策。
在地方層面,截至2012年9月,江蘇高層發展論壇已經舉行過30次會議。歷經陳煥友、回良玉、李源潮、梁保華、羅志軍多任省委書記,至今該論壇已成為江蘇省委、省政府政策咨詢的固定智囊團。
眼下,區域性、全國性的專業論壇,比以往更豐富,智庫的影響通過網絡的傳播也更迅速、廣泛。據統計,中國現有研究機構2500多家,專職研究人員超過3.5萬人,工作人員超過了27萬人。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2000家。
中國智庫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每一次改革之前,往往伴隨一場爭論。再回首,20年20問,每一問都緊扣時代主題。如新型城鎮化的爭論和分稅制改革爭議,城鎮化的目標是什么?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智庫就是一座橋梁:它為社會提出新的思想觀點和價值目標,引導公眾輿論和社會走向;它為政府決策提供咨詢參謀,影響政策;它把學者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產品,實現政治和學術的溝通;它及時反映和匯集社會各種意見需求,起著利益表達的作用。
參照世界一流智庫的運作方式,中國智庫未來的發展還依賴于需求市場的形成及自身質量的提高。有人總結“介于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狀態,往往更能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