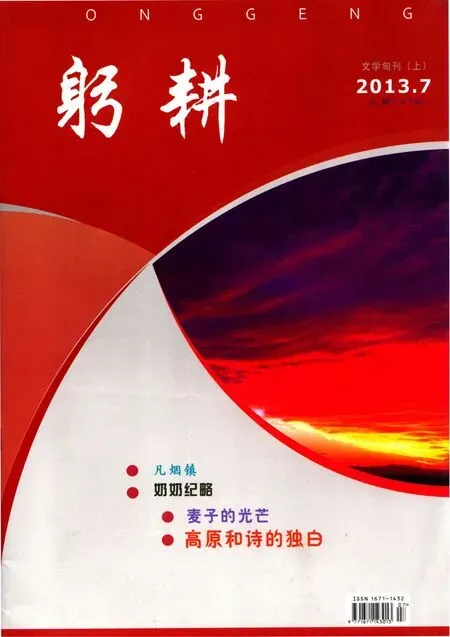奶奶紀略(外一篇)
◆ 周同賓

似乎是毫無緣由地,驀然想起奶奶。我的妻兒都沒有見過奶奶,老家仍然在世的鄉親,見過她的也已不多。我頓時有一種緊迫感,若不為她寫若干文字,不太久以后,她就如同沒在這個世界上生存過一樣。
奶奶沒有名字。娘家姓黨,村里的長輩人都叫她黨姐兒。1954年登記戶口,她的姓名被寫作“周黨氏”。她不認識那三個字,也從未用過那三個字,或許就意識不到自己還會有名字。
爺爺早逝,據說是在地里割豆子,突然吐血,當即死了。爺爺沒有遺言,或許,把一腔鮮血灑在自己的土地里本身就是遺言。爺爺留下八畝半地,三間低矮的每隔二年就得苫一層麥稈的草屋。那時,父親才十來歲,小小年紀就接過了爺爺留下的土地,和有關土地的一切農活。
奶奶是小腳。它出生在大清光緒年間,當然要裹腳,腳也真有那么三寸。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床頭纏腳,用五尺多長四指多寬的裹腳布狠狠地纏啊纏啊,把腳纏成粽子形。她裹腳或洗腳時,從不讓人看見。我見過一次,蜷屈擠壓變形得可怕。他說過小時候纏腳的痛苦,開始纏常常哭,下床、出門都要大人抱著或者扶著。他移動腳步走路,像兩根木棍在地上搗。雨天,路似剛剛發酵的紅薯面,簡直是在黏糊糊的爛泥里杵。奶奶身軀在女人中應屬高大,卻用一雙尖尖的腳支撐著,下地掰玉米、掐芝麻葉、起五更薅麥(為了不留麥茬,更為了多收些柴,小麥要連根拔起。薅就是拔的意思。《詩經·良耜》里就有“以薅荼蓼”,三千多年來音義未變。故鄉的方言里有很多古漢語的孑遺)。母親生于1920年,京城里早就沒了皇帝,可硬是被外婆逼著裹了小腳。“大躍進”中,她就是顛著那雙小腳在水庫工地上,挖土、挑土、抬石頭的。母親到晚年還埋怨過外婆“老思想”。卻從沒聽到奶奶埋怨過誰,好像原本就該如此。
我上中學時,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文章中,把“右傾分子”比作小腳女人,一下子全國批判“小腳女人”,似乎小腳女人都是最可惡的人。那時候全中國的成年女人大部分是小腳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總是想到奶奶,想到母親。不能無視她們的艱辛,她們的血淚,更怎忍心把她們和全民痛罵的壞人連在一起作踐啊。我只是心里想,絕不敢說出。
奶奶會彈棉花,是全村有名的彈花匠。在方言里,棉花簡稱為花。她去各家彈花。軋過的皮棉要紡線,必須彈,那時沒有彈花機。奶奶的工具是一張弓,洋槐木的,彎作初四初五的月牙兒形,用時勒上細而韌的皮弦,一把彈花槌,棗木的,手握的一端稍細,另一端有楞,彈花時就是用那楞撥動皮弦,在結成團的皮棉上顫動,發出“嘣、嘣、嘣、嘣……”悶悶的漫長的響聲,往往,從早飯后,持續到黃昏,如一首單調的樂曲,有一種無盡的沉重感,壓抑感。彈三遍,棉花才變成蓬蓬松松白云狀的棉絮。給別人彈花,中午管頓飯,工錢是一把花捻兒——紡線前把棉絮用高粱莛兒卷成近一尺長的薄薄的筒狀,那叫花捻兒。七斤棉花可織一匹布,彈七斤棉花耗時一整天。
有一幕情景至今不忘,六十余年過去,仿佛猶在眼前。
盛夏的傍晚,滿天瓦片云,被落日燒成了火紅色,反射著炙人的酷熱。黃澄澄的太陽光充塞地面、空中,像熔化了的鐵汁子,燙得狗伸著舌頭張嘴喘氣,南瓜葉蔫蔫地撲塌著,如收起的傘。在門口,我遠遠地看見奶奶從南莊回來了,一手拿把花捻兒,扶著肩上的弓,一手掂著彈花槌,蹣蹣跚跚走著碎步。寬大的粉藍土布上衣,老藍的扎了腿的土布褲子,在強光下顯得鉛一樣慘白。頭頂、兩肩、衣袖,毛茸茸地粘滿棉絮,棉絮上挑著夕陽。走近了,見老人家鼻孔里也鉆了棉絮,已被灰塵沾成灰色。布衫后背的汗漬一直洇濕到下擺,水淋淋地貼在身上。從水缸里舀半瓢涼水喝下,奶奶換了衣裳,坐院里捏下濕了的上衣、褲子上面粘的棉絮,終于積成棗兒那么大一團;絲絲縷縷都舍不得糟蹋。
奶奶每天夜里紡線。椿木做的紡車兒,已古舊成了鐵灰色,暗紅的棗木軸磨得變細。油燈放在錠子旁,燈焰兒只有黃豆大。每年種半畝芝麻,不為吃油,只為點燈和給錠子膏油。冬日夜長,總要再添一次油。坐下紡線前,總要把泡好的芝麻葉搦出拳頭大一疙瘩,手巾包了揣懷里,到半夜暖熱了吃下充饑。嗡嗡嗡,嗡嗡嗡,紡車聲是一支無頭無尾的枯燥的歌兒,始終繚繞在我的整個童年。紡車聲中,我慢慢長大,奶奶很快變老,滿臉深刻的皺紋里,積淀著溢滿兩頰、額頭的艱辛日子。有一天晚上,老人家教我一首歌謠:
紡花車兒哼哼,>
老娘累得腰疼。
小娃夜里踢騰,
被子蹬個窟窿。
大娃褲襠漏風,
鬧著要打補丁。
紡花紡到五更,
房檐掛了冰凌。
從紡出線,到織成布,有一個長長的過程,一家老小只能在寒冷中日日夜夜等待。把嗡嗡的紡車聲說成“哼哼”,更像呻吟,像嘆息,像無言的哭訴。這哼哼聲一直延續著,和抽出的線同樣長,和莊稼人的苦日子同樣長……
還記得一件事。
奶奶有個弟弟,小時候上樹掏鳥窩,摔下來斷了腿,成了拐子。為和其他幾個舅爺區別,向我提起時總稱拐子舅爺,簡稱拐爺。拐爺干不成農活,就學會用牛皮做牛套、籠頭、牛繩、役使牛干活時的皮鞭(據說鞭梢兒的技術含量最高,用一季子也不會斷的),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皮匠,在隔日逢集的鎮上街邊柳蔭下擺攤,邊做邊賣。有一次,我跟父親去趕集,見了他,馬上想到年畫《八仙過海》里的鐵拐李,他比李鐵拐更胖些。把手上的活兒地上一丟,拍掉身上的碎皮子,斜斜地站起,拐兩步去給我買了一笸籮兒水煎包子(賣水煎包子的平底鍋就支在他的皮貨攤旁邊)。我吃撐了,肚子好大。他說:“別吃了,剩下的拿回去。”說著,伸手折根柳條兒,捋掉葉子,把包子穿成串,又綰成了圈兒,遞給我提著。
一天,村人趕集回來說,拐爺明天要來我家。我立即想起圓圓的兩面焦黃的水煎包子,不禁流口水。次日上午,我正要用梢頭抹了椿樹膠的長竹竿去粘知了,扭臉看見拐爺從西南角的草灘上一瘸一瘸走來,背的布袋在身后左甩右甩。手里還提著一捆兒用麻扎了的尺把長的金黃的油條,隨著腳步前甩后甩。奶奶噔噔噔踩著碎步迎到大門外,接過布袋和油條。拐爺在院里石桌邊坐下,奶奶去灶屋打荷包蛋。瓦盆里只剩一個雞蛋,剛好母雞叫,又從雞窩里收一個。按禮法,來了貴客應當打六個荷包蛋。奶奶很遺憾,深感對不起表爺,絮絮地解釋說,一群雞被黃鼠狼拉走兩只,剩下的一入秋就不好好干活兒,攢的雞蛋前天換鹽了……那個年代,養雞主要為下蛋換鹽,農諺說,雞蛋換鹽,兩不見錢。拐爺打開他的布袋,里邊是十幾個熟透的紅柿子,在他身后一路擺來擺去,已成了一團糊糊,就讓我倒碗里吃,一再交代:“少吃點,吃多了肚疼。”我剛吸溜了小半碗,拐爺把盛荷包蛋的碗遞給我,還剩一個:“娃吃,娃吃了長大個兒。”挨近他,聞見他身上有一股牛皮味,或者說一股臭味,(所以有諺語“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的說法),好像仍坐在他的皮貨攤邊。我對那臭味不惡心,反倒更有一種親切感。聽說拐爺來了,半個村子的男人都來給他打招呼,他們都是他的老主顧。
1958年“大躍進”,全民不得安生。拐爺的皮貨攤子被迫收起,干了一輩子的手藝再沒用場。“人民公社”派他去修攔河壩,四個人四根繩拉一百多斤的石夯,拉起一人高,在大壩上狠砸。為了顯示“躍進”的氣勢,還要跟著石夯起落喊口號。瘸了腿的人個子矮,拐爺就得拼命用力。在那個晚霞似血的黃昏,眼看就要收工,一頭栽倒,頃刻死了,就在工地附近,草草挖坑埋掉。那年頭,死人似乎很正常,口號里就喊道:“頭可斷,血可流,鼓足干勁爭上游。”……
沒了皮匠這一行,牛籠頭、牛套之類壞了就只能以麻繩、草繩湊乎。好像沒人懷念拐爺,因為牛是集體的,集體的事兒馬馬虎虎即可。除了奶奶,好像更沒有人提起拐爺。奶奶想去拐爺墳前燒幾張紙,一百多里路,她不可能走到;即便走到,那墳很可能沒了。淺淺一堆土,一場雨過后就會淋平。
拐爺終生未娶。
印象中,奶奶說過很多話,甚至常常嘮叨。我記得的只有幾句,都是鄉諺。
奶奶說:“人操好心,神有感蔭。”
她認為操好心,神看著;作惡事,天報應。我家是中農,一般年景,糧食夠吃,還有剩余。那年春梢,嬸子家揭不開鍋,提著草筐來借二升高粱。奶奶用瓢給舀了滿筐。足有三升多,嬸子說用升子量量, 奶 奶說 擓 回去先吃,不夠了再來。老人家樂于助人。土地改革那陣兒,地主家的老太太趁著夜色,拿一包衣服送我家隱藏,都是土布褲褂,只一件陰丹士林長衫算得上體面。奶奶當即把衣服塞進床下的桐木箱子,而后送老太太到大門外。父親害怕,一再埋怨,奶奶說,地主咋啦?地主家的東西也不是偷來的,搶來的。
奶奶說:“記仇兩天,記恩百年。”
意思是說,別人對不起自己的事兒,睡一夜到第二天就不必再計較了。別人對自己做一件好事,應當記一輩子。不記得奶奶和誰有過嫌隙,她不會對不起任何人。只記得奶奶一再提到,爺爺死后,父親年幼,挑不動水,她每天用瓦罐去井上打水。一個夏天,連陰多日,村路上泥漿尺把深,奶奶雙腳插進泥里拔不出來,沒走兩步,摔倒地上,沾一身泥水,瓦罐也摔破。老成爺看見,連說“可憐,可憐”,把奶奶扶進家。一會兒,挑來兩桶水,赤著腳,褲子卷到膝蓋上,半截腿都是泥。倒進瓦缸,扭頭就走。那年隆冬,一天夜里,老成爺家灶屋失火——老成奶做黃酒,把酒壇放在灶膛邊,為加溫,挨酒壇熰了草末子,誰知草末子燃著了柴,灶屋立即起火。老成爺把棉被塞水缸蘸了水,蓋在正房的房坡,才保住正房。老成爺喊救火時,父親起床去了,什么也沒救出,米面都燒光了。第二天早晨,奶奶說,囫圇籽兒糧食咋吃?濕被子夜里咋蓋?不一會兒,我看見母親抱兩條棉被,奶奶用柳條筐提了半筐苞谷糝,里面放了一瓢小米,朝老成爺家走去,橘色的霞光灑滿她倆頭上身上。老成爺死后,奶奶仍不忘他的恩德,多次述說擔水的事兒,和他的家人關系仍然熱火。
奶奶說:“椿頭菜綰纂兒,老婆餓成黃臉兒。”
這是說的荒春。椿樹發芽晚,直到四月里,枝頭才吐露出攏成纂兒狀的青紫色的雛葉,那就叫椿頭菜。這是麥熟前最難熬的一段日子。大部分人家吃食都緊,常常挨餓。奶奶對饑餓的印象特別深,多次提起民國十八年(1929年)的饑荒,人吃人,小妞頭上插根草在集鎮上賣,一升苞谷就就能買走。還說到三十一年(1942年)的饑荒,先是澇,后是旱,接著是蝗災,螞蚱飛過來把日頭都擋了,滿天都是黃的,落地里一片唰唰聲,瘆人,一會兒就吃光莊稼,再去另一塊地。蝗蟲過后連一把草也沒收,只土里的還沒長成的紅薯保住了。從秋后到次年麥收前,日子越來越難,餓死人沒有數。
奶奶熬過了那兩場饑荒。
衣裳破了,縫縫補補還能穿。沒了吃食,不到七天就要死。奶奶最怕挨餓。
老人家還說過一首兒歌:
地里活,家里活,忙壞老頭和老婆。
拿根長繩拴日頭,你想落,不得落,
——一天能干兩天活。
這應是“長繩系日”典故的農家版。莊稼人一年四季忙,冬天也不閑。父親伺候牛驢,出糞,拉末子(即墊牛圈積肥的土),丟了筢子掂掃帚。母親織布,縫補衣裳。奶奶除了外出彈棉花,就是紡線、纏線、絡線,為織布做準備。奶奶沒看過戲,聽過藝人說書,沒去東鄰西舍串過門,來了人,招呼坐下,就邊紡線邊拉家常,兩不誤。奶奶曾有一個比喻:莊稼人啊,就像牛,受苦受累、使死使活伸長脖子曳一輩子,直到走不動。人比牛強些,牛老死剝皮吃肉,人老死躺到墳里歇息。
奶奶終生沒走出過方圓十里。
還記得奶奶說過有關政治的話。一次說:“毛澤東坐朝(我記得很清,她沒說“毛主席”而是直呼其名),好處是打死了崔二旦、老王泰(崔、王是我們那一帶最有名的土匪、桿子),天下太平,再也不怕半夜來搶,來拉票兒。壞處是地都充公,一大群人一塊兒干活兒,都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吃不飽飯活該。”上世紀五十年代前幾年,是奶奶一生最舒心的時候,全家男耕女織,日子紅火。正是在1955年,我家又買了五畝地。可只收了一季莊稼,來了個“合作化”運動,攏進集體了。還有一次,聽到拐爺慘死,奶奶說:“啥大躍進,不是躍進,是要命。”(在方言里,躍進的‘躍’讀‘要’)自“大躍進”開始,家里沒了鍋灶,奶奶住進了敬老院。頭幾個月還能吃飽,后來就不行了……
1959年秋期,我去臥龍崗上的一所專科學校上學,吃的當然是商品糧,每頓飯一個白面饃。1960年春節放假前幾天,忍著餓每天省下半個饃,最后攢了三個饃,早飯后裝進書包步行回家。離家70里,走到下午餓得邁不開步,吃了一個,下好大決心不吃,還是吃了。日落前到家,見奶奶睡在堂屋東間靠山墻的地上,鋪的是麥草,一塊坯上墊著舊衣作枕頭,臉沒血色,蒼白頭發蓬亂。我拿出饃,給奶奶一個,給父母一個。母親掰開,讓我吃了半個,另半個又掰開,給父親一半。奶奶大口大口吃,一會兒就吃完了,唇上沾的碎屑也舔近嘴里。而后,切切地看著我,渾濁的淚順眼角流下,滴濕土坯上的舊衣。我看見她的手指細而尖,瘦干的胳膊上條條青筋好似死了的蚯蚓。我后悔路上吃掉了一個饃……那是個慘淡的春節,沒有饅頭,更沒有肉菜,只吃了一碗紅薯面包紅薯葉的餃子。一天后父母就讓我回校,母親懇求管食堂的大隊干部,幾乎跪下,給我要了一個紅薯面摻糠蒸成的饃,路上作干糧。
大概我走了不多久,每人每天還能從大食堂領到兩瓢稀湯時,奶奶就去世。下葬沒有棺木(她的棺材十年前就已備好,“大躍進”中拉走,劈開,扔進了煉鋼爐)。父親最后悔的是,沒把灶屋的門取下,擋在墓坑上,不讓泥土砸了奶奶的臉,每提起總嘆氣,愧疚不已。莊稼人稱棺材為“老屋”,奶奶死后沒有屋住啊。令父親稍感寬慰的是,在食堂斷糧前,早已沒柴燒火,就趁著夜色去扒故去的先輩們的墳,扒出棺木當柴燒,煮紅薯葉、葉柄和秧子,而奶奶死后,卻沒受折騰,沒被掘墓動尸。
奶奶死時父母沒告訴我,大概一來沒法捎信兒,二來怕我回去沒飯吃。直到暑假結束前幾天(暑假期間校方不準學生離開),我才回家,在爺爺奶奶合葬墓前叩頭燒紙。我想象不出奶奶死前的情狀,父母從未說過。我只強烈感覺到,老人家躺地下,黑土重重擠壓著,一定很不舒服,怎好歇息?
記得,我小時候一個夏天,一個算命先生一手拿木杖探路,一手提一面上帶小錘的小鐋鑼時時叮叮敲著(叮叮聲是招攬生意的廣告),從我家門前經過。突然下了暴雨,奶奶正在石榴樹下紡線,立即去把瞎子領回家避雨。錐子雨下了兩天,算命先生在我家住了三天,夜里睡磨房,白天坐堂屋說閑話,說他的年輕時候的苦難經歷,奶奶感動得唏噓不已。先生還掐著指頭、仰著空洞無物的眼,念念有詞地認認真真地給全家四口算了命。那幾天,除了早飯,頓頓炒菜。第四天,地上沒了泥才送他上路。給父母算命的結果我已模糊,只記得,瞎子預言我將來要當大官,奶奶大半輩子受苦,臨老要享福。
看來,被鄉民尊為“小諸葛”的先生絕對是算錯了。我直到范進中舉的年紀,才混個副科級,奶奶最終卻是那樣……
1987年春,進城跟我們同住的母親說,爺奶的墳本來已小,被承包那塊地的村民犁耙得更小了,必須立塊碑擋住。碑上要刻名字,問爺爺叫啥,母親不知道,特地回老家遍詢村中高壽老人,皆無印象。墓碑上的爺爺只好以“周公”二字代之(又過數年,我才在一本民國初年手抄族譜的最后一頁,找到爺爺的名字“周金波”)……
2013年4月10日
老屋
深秋,帶兒女還鄉。掃墓畢,在遠房侄兒家吃飯。飯后,兒女要回自己家看看。過一條新修的路,繞兩座院落,一片疏林,就到了我們自己的家。家已空,算不上家,只能說是舊居。黑土和草根打成的院墻,早被二十年風雨侵蝕傾圮,只看見礓石砌就的墻基,上面積了蚯蚓拱出的土粒,蝸牛爬過留下的白印。老屋猶在,門落鎖,鎖已銹。十三格的木窗,木質已成鐵灰色,蜘蛛密密結網,織一層紗。門口的地上,無人的足跡,有干了的綠苔,枯了的野草。
兒女年輕,卻也感傷。他們生在城里,滿周歲,次第回來跟著爺爺奶奶,待上學,才返城。在這里,有他們早已消逝的童年。那時是娃娃妞妞,如今已長大成人。他們都沒說話,只默默滿院察看,似要尋覓當初的遺留。好像找不到,一切都被歲月消解遮掩。他們的爺爺奶奶,已先后魂歸村外的黑土地;人去了,昔日的生活也去了。家只剩下外殼,憑回憶怎能把它填滿?愈是回憶,家愈虛空,舊時的景象愈是遙遠。一番回憶,只引出長長的嘆惋。
我也無言,久久在老屋前后彳亍,步履蹣跚。兒女們或許不知道我心里更蒼涼。我在這里落生,胞衣就埋在院里的石榴樹下——石榴樹早已不存。在這里,我度過雖貧寒卻快樂的童年,步入雖苦澀卻亢奮的青春。這舊屋,這小院,一直是我精神的歸宿。多少次在文章里,描繪過兒時的生活,筆端流下親切的情感,傾吐對家的思念,那思念剪不斷理還亂。到如今真正到家一看,卻原來,那些都是想象,都是虛幻;萬千思念并沒有最終的著落,像漂泊的船,纜繩已無樁可拴。失去的,永遠失去了,失去的不僅僅是飄入高空的炊煙、放了豇豆的小米飯的香味、雞和狗、母親的織布聲、父親飼養的牛驢,是整個兒農家生活的溫馨和艱辛,還是一種文化,還是我得以安心立命做人作文的原初依據。
最早,我家只三間草屋,茅檐低而豁,土坯墻擋不住鉆進的北風。打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父親就準備蓋瓦房,一次又一次省下錢買磚買瓦,一次又一次碰上“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大饑荒,磚瓦被拉去充公。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終于建成三間苫了藍瓦的新房(為了省錢,仍是土坯壘墻,只用青磚包了墻皮,鄉下人管那叫“里生外熟”)。那過程,艱難而漫長,一如李順大造屋。如今,瓦壟已凌亂,墻也裂了縫,檐下有明顯的雨漏痕。老屋真的老了,在周圍一座座鋼筋水泥建成的樓房的對比中,越發顯得寒磣。
我家的宅基地超過半畝,原有雜樹大大小小百余棵,組成一片林子,枝葉扶疏,綠蔭如翠蓋。我小時候,曾在林中摘構桃,捋榆錢,掃樹葉。兒女小時候,曾在林中捉知了,撲蝴蝶,藏貓貓。每棵樹都和我們兩輩人的童年有關。如今,那么多的樹大都不知去向,我數數,還剩九棵,南一棵北一棵,孤零零的不成林。樹下拴著別人家的牛,跑著別人家的雞鴨。可能是羊,啃掉了榆樹的皮,可能是豬,拱出了楝樹的根。沒了主人,樹也活得不自在。那棵構樹,干更加彎曲,枝大半干枯,身上被蟲子蛀出窟窿,浸殷紅的津液,酷似行將死去的駝背老翁。那棵桑樹,已經中空,而且皸裂,木縫里長了野生的木耳,還有一坨坨蕈類植物。屋角那棵椿樹,女兒在家時,只有茶杯粗,曾猴兒似的爬上爬下玩;而今,已長成水桶粗,結一樹帶翅膀的椿谷谷。猛看見另一棵椿樹上有鳥巢,像是斑鳩的窩。忽想起我小時候樹上就有斑鳩窩,不知道這斑鳩是那斑鳩的幾代子孫。主人離去,鳥兒還守著故園,替我看家。忙去那樹下看,見有螞蟻排著長隊沿主干蜿蜒行進。它們一定是我兒時的螞蟻的后裔。這卑微的小生靈永遠不離故土。
我家世代務農,自列祖列宗到我父親母親,輩輩都是莊稼人。從我這一代起,居然離土離鄉了。雖然住進城市,我總自認為仍是鄉下人,常以草民百姓的視角,看茫茫塵世間的事事物物。其實,在鄉下,我沒一寸可耕的田地,也無須拼盡力氣土里刨食,早已不是地道的鄉下人。我和土地、莊稼、農事活動,已無任何聯系。我和故鄉的牽連,只剩下一座老屋,九棵老樹,還有一顆老邁的心。進而想到,我的兒女對老家或許還會留些印象,那印象將漸漸淡去;我兒女的兒女就不可能再承認這里曾是家了。
有鄉親勸我重新修葺老屋,我說,不必了。有鄉親勸我索性賣掉,我說,更不成。就讓它這樣存在下去,衰敗下去,起碼可以作為家的象征,作為早已破碎的舊夢的見證,總能為我的馀生留下一個想頭。
臨別,起一陣風,枝頭殘留的黃葉紛紛飄落,簌簌有聲,像是嘆息,像是叮嚀,像是切切囑咐我,這里畢竟是根,是人生旅程的起點站,即便走到天涯,也不要斷了一絲記掛。
2004年2月4日
附記:
癸巳歲清明節前,我又還鄉,見老屋后房坡已凹陷,怕是夏天一到,一場大雨就會淋塌。是該修繕了,祖宗的遺產在我手里毀掉,于心不忍。所幸墻壁仍然完好堅固,當即決定,卸下瓦,更換不能再用的檁、梁、椽子,再苫上舊瓦。動工日,數十位鄉親都來幫忙,不二日即完工。我要給他們錢,回說:“拿錢是打俺臉。”無奈,只好以好煙好酒招待,筵席一直持續到半夜。鄉親們醉而歸,我心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