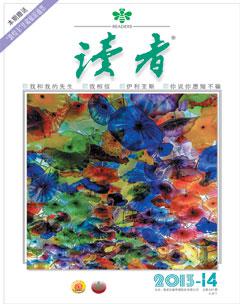投筆從戎的聯大人
劉宜慶

抗戰期間,在兩次入緬作戰的熱潮中,西南聯大教授的“學二代”也紛紛參軍,或當譯員或任駕駛兵;聯大3位常委正在讀大學的兒子都率先做榜樣:張伯苓之子張錫祜早已成為空軍飛行員;梅貽琦之子梅祖彥和蔣夢麟之子蔣仁淵都志愿去參戰部隊當軍事譯員。不僅如此,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之子查瑞傳,任參戰汽車部隊駕駛兵;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之子馮鐘遼,去參戰部隊當軍事譯員。
當形勢危急需要聯大“學二代”從軍時,這些學者大儒毫不猶豫地把兒子送到前線和戰場。
不僅聯大的“學二代”,當時整個文化學術界的“學二代”大多有從軍的經歷。聯大哲學系的熊秉明是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的公子,后來成為著名的藝術家、法國巴黎大學教授,當時他也棄學從軍。聯大學子陶渝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陶孟和的公子,當時也和同學一起當軍事譯員。
梅貽琦4個女兒中,除了長女出嫁,小女尚幼外,在聯大讀書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從軍運動中報了名,在西南聯大一時傳為佳話。
聯大歷史系劉崇鋐教授也送子參軍,這位前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待人和藹可親,親自送孩子入伍。
盡管目睹和體驗到軍隊中貪腐等陰暗面,但聯大學子依舊投筆從戎,為抗戰做出的貢獻,彪炳史冊。
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戰績,美國總統授予戰功卓越的人員銅質自由勛章(由于當時郵路不暢,很多人未能收到勛章和證書),名單上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義等高級將領,下至軍官、技術人員和軍事翻譯員。在52名受獎的翻譯官中,西南聯大學生有16人,他們代表西南聯大所有從事翻譯員工作的同學獲得這項榮譽,這也說明軍事翻譯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的作用。
1938年9月28日,日軍對昆明進行空襲,聯大租來做宿舍的昆華師范學校被轟炸。于是,在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聯大掀起報考空軍飛行員的熱潮。當時,我國空軍飛行員犧牲者甚眾,當局決定在大學生中招考飛行員。許多聯大學生勇赴國難,踴躍報考,先后有幾十位聯大學子被錄取。他們走進昆明巫家壩空軍航校大門時,都清楚地意識到,這將是他們英勇報國的開始。
經過短期飛行訓練后,聯大出身的飛行員到美國繼續接受各種飛行訓練,包括初、中、高級的教練機飛行訓練和畢業后的作戰飛機訓練,為期不到一年。
他們分批回國參戰,和飛虎隊一起痛擊日寇。其中犧牲5人:
戴榮鉅,1939年考入地質物理氣象系,受訓歸來在湖南芷江的空軍第5大隊,1944年6月在長沙戰役中殉國。
王文,1941年考入機械系,受訓歸來在陜西安康的空軍第3大隊,1944年8月在保衛衡陽戰役中殉國。
吳堅,1939年考入聯大先修班,1940年入航空系,受訓歸來在陜西安康的空軍第3大隊,1945年在陜西與日寇飛機作戰時殉國。
崔明川,1941年考入機械系,1943年在美國飛行訓練時,飛機失事撞山殉國。
李嘉禾,1940年轉學入物理系二年級,1943年在美國飛行訓練時,不幸失事殉國。
據馬豫《緬懷在抗日空戰中犧牲的聯大人》一文載,戴榮鉅犧牲后,他所在的空軍中隊給其兄發去撫恤公函,大隊長也給烈士家屬寫了慰問信。撫恤函全文如下:
榮鉞先生偉鑒:
抗戰軍興群情奮發,令弟榮鉅愛國熱忱,投效空軍服務本大隊,其志殊為可嘉。不幸于本年六月隨隊出發,在長沙空戰,壯烈殉國,實屬痛惜。除報請航委會從優撫恤外,特函唁慰。希轉達令翁勿以過悲為盼。
戴榮鉅、王文、吳堅3人的名字沒有刻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從軍學生名單中,但他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犧牲地點,鐫刻在了張愛萍將軍題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紀念碑上。
在1944年應屆畢業生被征調時,外文系彭國濤去美國第14航空隊,經濟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電機系孫永明去緬甸孫立人軍中當翻譯。中國航空公司招考飛行員,西南聯大學生應考被錄取者有11人。他們經過短期訓練后,即參加舉世聞名的駝峰航線的運輸任務,擔任副駕駛員穿梭來往于中印之間。中國航空公司的主駕駛員多為“飛虎隊”的飛行員轉過來的,所以中國航空公司被稱為駝峰航線上的“飛虎隊”。
駝峰航線的運輸線沿線氣候條件惡劣,并且為避開緬北日機的襲擊,不得不在沒有無線電導航臺和明顯地標的航線上進行夜間飛行,因此飛機常常失事,因公殉職的人員中不少是聯大學子。
聯大的屋頂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眾多大師,也培養了沖向藍天翱翔的飛行員。有的犧牲殉國,有的成為新中國航空事業的骨干,我們不應忘記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
(豆 豆摘自江蘇文藝出版社《大師之大——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