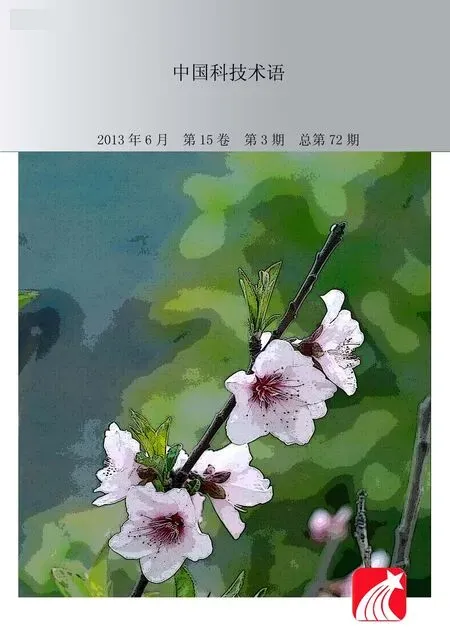認知術語學視域下的中醫術語
陳 雪
(黑龍江大學遠東經貿導報,黑龍江哈爾濱 150080)
引言
根據術語學的觀點,一個學科術語的規范化程度直接反映一個學科的發展水平,一門科學越“科學”,術語就越完善。而中醫藥學因其悠久的歷史,術語具有一些特性。比如形式獨特且不簡短,有時是字,有時又是短句,如“神”“木克土”“人生有形,不離陰陽”;而術語的意義往往較為廣泛,一詞多義的情況較多,如“氣”;有些概念相對模糊,如“陰”“陽”,且沒有明確界限;還有一些同義詞,如“內風”也稱“肝風內動”或“虛風內動”等。根據近現代發展起來的傳統術語學理論來看,中醫術語顯然不符合術語學對理想術語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標準,如單義性、準確性、簡短性、系統性、不能有同義詞等,這甚至也成為各界質疑中醫科學性的論據之一。
隨著認知科學的發展,近一二十年認知術語學的產生對傳統術語學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從認知角度來看,中醫術語因具有濃厚的中國古典哲學、傳統文化以及古漢語特點,具有很高的認知研究價值,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對生命現象的特有的認知方式和體會。
一 認知術語學理論源起與發展
術語學的發展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20 世紀30年代的萌芽階段;70年代的確立階段;90年代的發展階段。也許不同術語研究者對于術語學發展階段的劃分會存在不同觀點,但絕大多數術語學家都承認,今天的術語學處在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即認知術語學階段。
20 世紀90年代末,認知術語學(когнитивн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首先產生于具有雄厚術語學研究基礎的俄羅斯,是認知科學和認知語言學在術語學研究領域的新拓展。
1993年俄羅斯術語學家格里尼奧夫(С.В.Гринев)在《術語學引論》一書中使用“認識論術語學”(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這一術語,研究專業詞匯在科學認識中的作用,并指出術語在科學認知中具有記錄知識、發現新知和傳播知識的功能。該著作可以看作是認知術語學產生和發展的基礎。1998年著名學者阿列克謝耶娃(Л.М.Алексеева)在《術語和隱喻》一書中首次提出“認知術語學”這一術語。同一時期,西方學者也開始把“社會認知術語學”作為與傳統術語學相對的概念提出來。此后,“認知術語學”這一術語開始被術語研究者積極使用。
2006年,俄羅斯術語學家塔塔里諾夫(В.А.Татаринов)在百科詞典中收錄了“認知術語學”,并指出[1]:
在認知術語學框架下,術語被看作是人類認知活動的結果,是人類對知識進行加工和結構化的產物。術語能夠記錄人類獲取的信息,成為認知的工具,因為它能夠總結科學事實、積累知識并傳播給下一代年輕學者。它的研究基礎是范疇化、概念化、概念模式、隱喻化和世界圖景等問題。
認知術語學從認知科學中引入隱喻、隱喻化、概念化、概念空間、范疇化、世界圖景等一系列概念,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范疇機制、研究方法、理論問題和發展趨向。它不僅是術語學的一個分支方向,它還是全新的觀點體系,是對傳統術語觀的顛覆和重構,它對很多傳統術語學的基本問題給予重新認識。
首先,認知術語學突破傳統術語學的語言學界限,把術語看作是表達專業思想和思維的客體,是專業信息的載體和存儲形式,它不僅承載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結果,而且是未來認知活動的手段,是專業領域認知和交際的單位。
其次,術語隱喻現象在傳統術語學框架內被看作是術語構成的個例,是術語構成的手段之一;在認知術語學研究中則被看作是概念生成及系統構建的基本思維方式。
再次,傳統術語學把術語多義現象看成是一個需要根除的“缺陷”,而從認知術語學角度來看,多義現象是通過人類認知手段由一個詞的中心意義或基本意義向其他意義的延伸,是人類范疇化、概念化及隱喻思維不斷發展的結果,是科學概念及相應術語發展的普遍現象。
綜上所述,認知術語學對很多傳統術語學中的基本問題給予重新闡釋,它將為中醫術語研究帶來新的視角和空間。
二 中醫學是一門獨特的科學
論據一:俄羅斯著名術語學家列依奇克(В.М.Лейчик)指出[2]:
術語系統并不僅是與概念系統相聯系,而且是與其背后的科學理論相聯系。客觀現實的多元性和不可窮盡性以及每個理論體系的有限性,導致同一個知識領域內可能同時存在多個理論體系,每個理論體系都有自己的一套術語系統,能夠覆蓋它所描述的客觀知識領域。
例如語言學中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功能主義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都是不同的理論體系,都有自己的一套術語,它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相輔相成,相互補充。中醫學與西方現代醫學對于生命現象這個研究對象完全建構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對人體和病理有自己的一套解釋系統,醫學實踐中有很多中西醫結合的例子。實踐證明,它們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
論據二:“一門科學理論的術語首先是以某一自然語言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它是該語言群體對世界的認識的體現形式。”[3]而中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由漢語建構的世界,其語言特質與漢語的文化特質相關,反映了漢民族生活現象的世界。它與西方現代生物醫學的哲學基礎、思維模式、認知方式都不同,術語系統的構建模式也因此不同。中醫基礎理論建立于陰陽、五行等基本概念之上,氣血、經絡等基本概念都是中醫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華民族關于生命現象的世界圖景。
論據三:隱喻是人類重要的認知方式,尤其是抽象思維的工具。從認知角度看:“科學隱喻不僅有助于快速掌握研究對象,是描述科學理論的語言手段,還有助于人們探求知識、記錄知識,是概念化的重要手段。”[4]從科學歷史的發展軌跡來看,幾乎沒有任何科學理論是基于純粹的邏輯建構。從生物學中分子的雙螺旋體結構,到核物理學中的夸克,我們很難想象沒有隱喻的“科學語言”。而綜觀中醫術語的內涵,可以說隱喻無處不在。同時,相對于其他對象科學的擬人觀(即以人的身體結構、功能、形象、性格等特征比擬非人類事物),中醫學對人類機體的隱喻思維則是擬物觀,即在中醫學上,人的軀體就是縮小的世界,人與宇宙是同構的,從人體推及自然,人與萬物的構成和運動規律是一致的,自然、情緒、社會生活、動物、植物、氣象、兵法和等級制度等都被用于中醫的認知原型。可以說,準確把握中醫術語的隱喻特質是理解中醫理論的重要一環。
綜合以上術語學分析,中醫是一門歷史性和人文性高度融合的、最具中國特色的學科,其術語具有鮮明的傳統文化特色。
三 中醫術語的特點
俄羅斯著名哲學家弗洛連斯基(П.А.Флоренский)曾指出:“任何一門科學的實質就是該科學的術語系統,術語的發展史恰恰反映了這門科學的發展史。”[5]中醫學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其術語因此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學術語的特點,朱建平教授曾撰文將中醫術語的特點概括為“歷史性、人文性、定性描述、用具體名詞表達抽象概念”[6]。
1.歷史性
中醫術語多為古代漢語,中醫術語可以是字、詞、短語,還要考慮到古今詞義的演變等,如“內風”在古代指因房勞汗出,風邪乘襲的病證,今指肝風內動,即由臟腑機能失調而引起具有動搖、震顫特點之各種癥狀的病理變化,與肝臟關系最為密切。
2.人文性
中醫術語大多包涵了較多的中國傳統文化,如術語“三子養親湯”中,“三子”是指紫蘇子、白芥子、蘿卜子三種藥材,主治老年人中氣虛弱,運化不健。因其用三種果實組方,以治老人喘咳之疾,因此寓其“子以養親”之意,蘊含了漢語言主體的民族傳統文化。
3.定性描述
中醫術語包含大量的自然語言和生活語言,用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和事態來表述或比喻人的生理、病理、診斷和治療的原理等。多為定性描述,很少定量描述,如氣虛、火旺等都是一個定性的描述,無法用確定的數值來衡量。
4.濃厚鮮明的古漢語特色
中醫術語多為古代漢語,由于漢文字的特殊性,中醫術語中的詞法、句法非常靈活,極富彈性。有很多概念的術語表達不完全符合形式邏輯及現代術語學的要求。此外,中醫術語往往意義廣泛,一字多義。如“氣”是中醫中使用頻率相對較高的一個術語,“有人將《黃帝內經》中的‘氣’分為270多種,其概念內容很難清晰界定”[7]。
5.獨特的抽象思維方式
漢語言文字和民族文化與中醫學科體現的抽象思維方式是互為影響的,尤其體現在隱喻思維模式上。如五行是古人在長期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對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樸素認識基礎上,進行抽象而逐漸形成的理論概念,指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運動變化。因此醫學上所說的五行并非指這五種具體物質本身,而是五種物質不同屬性的抽象概括。
四 中醫術語的外譯
2012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出中醫藥文化建設的“十二五”規劃,意味著提升中醫藥文化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已被列為國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方面。在強調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導向下,中醫術語的外譯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它是推動中醫走向世界以及平衡“文化逆差”的必經之路。
術語翻譯不單單是完成兩種語言表達手段之間的轉換,還要實現學科領域內的科學概念之間的對應,不同語言相應學科領域的概念之所以能對應,其理論前提是科學的國際性和科學認識的普遍性。此外,在傳遞概念基礎上,還應該保證所翻譯的術語相互聯系成一個整體,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概念體系。從概念出發、從概念系統出發是術語學的一條基本原則。[8]
也就是說,不同語言間術語表達手段的轉換具有不同于一般語言的突出特點,因為術語同時屬于語言系統和專業知識系統。在翻譯過程中必須考慮語言和非語言的綜合因素。
然而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以及中醫所具有的濃厚的中國古代文化底蘊,其獨特的理論概念在目標語言中沒有對應詞,中醫術語的外譯遇到了巨大的挑戰。因此需要做好以下兩點:
首先,中醫學迄今已有兩千余年的歷史,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它的很多理論的科學性已逐漸被證實,因此在很多中醫術語翻譯過程中,不僅考慮雙方語言特點,還應考慮中醫理論體系的繼承性,不要單個解決術語翻譯問題,而要注意保持術語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制定統一可行的外譯處理原則和方法。對基于這些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及名詞的譯介應保持中醫固有特色,不能以西代中,也無法取代,如氣血、經絡、三焦等中醫獨有術語在西方現代醫學中缺乏對應詞。另外,基于不同理論體系的中、西醫術語,還存在名同實異的情況,如中醫的心、肝、脾、肺等概念的內涵與西方現代醫學中概念有很大不同,這種情況尤其需要注意。
其次,中醫術語的規范工作需要語言學家和中醫學者的共同努力,進而,其外譯也不應僅局限于漢語言使用者,還需要目標語國家的漢學家和中醫工作者的合作。對于一些翻譯原則和方法不宜過于教條,除了考慮保持我國文化傳統、思維習慣和語言特色之外,目標語國家的語言習慣和認知特點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對于同一個術語外譯,中國人的翻譯和外國人的翻譯肯定會有不同的地方,尤其對于中醫這樣一門具有濃厚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學科。因此做好與目標語國家相關領域研究人員的協調和溝通工作,在不破壞中醫理論精髓的前提下選擇更為恰當和合適的表達手段,對于中醫的傳播和交流更有好處。
[1]Татаринов В.А.Обще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А.Татари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РоссТерм[М].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2006:82.
[2]Лейчик В.М.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предмет,метод,структура[М].Белосто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елосток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7:100-101.
[3]Романова Н.П.Язык наук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и источник познания[С]//Татаринов В.А.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ТОМ3).Москва: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2003:218.
[4]Алексеева Л.М.Метафоры,которые мы выбираем (опыт описа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тосферы)/Л.М.Алексеева[C]// любовью к языку:сб.науч.трудов.-М.Воронеж:ИЯ РАН,Воронеж.гос.ун-т,2002:293.
[5]Алексеева Л.М.Философия термина в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C]//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и знание.МатериалыⅡ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Москва,2010:18.
[6]朱建平.中醫術語規范化與中醫現代化國際化[J].中華中醫藥雜志,2006(21):7.
[7]邱鴻鐘.中醫的科學思維與認識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73.
[8]鄭述譜,葉其松.從認知術語學角度看中醫術語及其翻譯[C]//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翻譯專業委員會第三屆學術年會論文集,201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