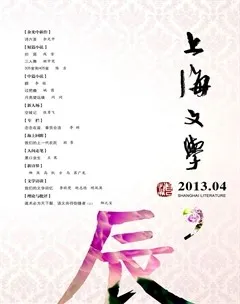道術必為天下裂,語文尚待彌縫者(上)
一
中等水平以上讀者“看不懂”當代中國某些人文社會學科的論著,已是司空見慣,但回想起來,這也有一個漸變過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后,以人文學者為主的“第四代學人”(當時社會科學還剛復蘇)也招來過“看不懂”的抱怨,那基本是青年學者知識及話語系統急速變換所致,屬于從“現代”延續下來的正常現象。這以前,胡風的理論與批評就曾以險怪著稱①。再早一點,青年魯迅“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章太炎的文章(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自稱“瞎嚼蛆”的吳稚暉行文也極富跳躍性②。但這主要還是難懂,根本“看不懂”的并不多,像章太炎的令人“看不懂”則是曲高和寡。上述諸家很少被指為生造詞語、玩弄概念、用詞不當或文理不通,實在令人費解的個別學者要么像所有時代文理不通者一樣很快淡出,要么改弦易轍,重新為人接納。從晚清“新學”勃興到80年代,學術理論文章“看不懂”的現象并不嚴重。
1990年代以后,人文社會科學得到政府大力扶持,一派“繁榮”景象。文史哲等傳統學科很快告別了90年代初的惶恐與憤激,猶如絕處逢生,因應社會需要的新興學科更迅猛發展,由“帶頭人”負責的“學術梯隊”和相應的學術機構紛紛建立,國內外學術會議川流不息,各種簇新的“話語”和學者的肉身一樣到處“旅行”,項目如山,頒獎頻繁,出版方便,著作如林,但恰恰這時候學術語言的問題日益凸顯,看不懂、無法溝通的抱怨此起彼伏,有時還升級為嚴厲指責,即認為許多學術文章令人“看不懂”,并非學問高深,常人難得通解,或苦心孤詣,出現了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的艱深晦澀,而是某些作者學養不夠,準備不足,滿足于搬弄空洞的連自己也不懂的話語概念,甚至缺乏起碼的語文素養。學界和網上不時公布一些著名學者用詞不當、概念模糊、文理不通、不知所云的“硬傷”,令人觸目驚心,而在語言表達上心中無數,下筆狐疑,“方其搦管,氣倍辭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③,也是不少學者羞于啟齒的虛癥。“學術繁榮,語言退化”,似乎成了“盛世學術”尷尬而難解的悖論。揆其要害,無非兩點:一是缺乏基本語文素養,二是過分依賴某些學科新近建立的一套夾生而封閉的話語體系,致使學術語言脫離民族歷史的語言脈絡和當下日常的語言母體,流于空虛玄遠。第二點又有兩種可能,一是雖依賴概念和話語,卻愿意淺易明白,可惜能力不及,結果仍不免模糊難懂,甚至變得文理不通起來。這是“非不為也,乃不能也”。第二則屬于魯迅所謂“貴乎難懂”的“作文秘訣”,故意叫人看不懂,迎合國人“崇拜‘難’的脾氣”,同時也有助于“修辭”(“遮丑”)以確立“學者”的地位。久而久之,便只能一“難”到底,再也寫不出“人話”來了,而若有人把他們的“修辭”翻成白話文,往往空空如也,根本不通(魯迅《南腔北調集·作文秘訣》)。這就并不是“非不為也,乃不能也”,而是“既不能也,亦不為也”。
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者的語文素養和話語方式問題已關乎學術文化的根本與全局,不容再回避了,但學術界對此一直比較麻木,大多數人身在其中,感覺不到,誠所謂“久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臭”,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只要有學術、有思想,語言差一點又有何妨?正是這種割裂學術和語言、以為學術可以離開語言,甚至只要學術而不顧語言的觀念直接導致并且一再縱容了學術語言的滑坡。其實一國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倘若與中等水平的廣大讀者之間出現語言的隔閡,甚至令后者完全看不懂,對后者來說,該國有無人文社會科學便是一個疑問。一國之人文社會科學者倘若相互之間無法溝通,學者們在彼此隔絕毫無交流的狀況下自說自話盲目生產,則該國有無真正的人文社會科學,就更值得懷疑。
從局部的不甚嚴重的“看不懂”突變到大面積的比較嚴重的“看不懂”,分界線在1990年代。這是我的一個尚待論證的初步假設。倘若假設成立,處身90年代以來學術潮流的我輩就有必要回過頭去,研究晚清至20世紀80年代這一整個歷史階段中國學術共同體在學術語言上究竟提供了哪些經驗與教訓,以為殷鑒。
但現代中國學界古今中西之辯、階級階層之別、宗派集團之分大大超過當代,有無“學術共同體”首先還是一個疑問。不過,倘若著眼于現代學者共同置身的先秦以降歷時性語言背景和“五四”以來共時性語言環境,著眼于學者與學者之間、學者與一般讀者之間語言上的可溝通性,著眼于這種可溝通性既表現為語文層面的文從字順,也表現為學術話語層面的生、熟、難、易、深、淺之間的融通,則似乎又可以說存在著一個由相對穩定的語言認同所維持的學術共同體。
二
姑舉數例說明之。
1、 《新青年》集團和林紓、《甲寅》雜志、“學衡派”圍繞“新文化運動”的爭論,1980年代以來的研究不可謂不深入,但一個顯然的事實始終未曾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被有意遮蔽了:當年那些激烈的論爭者們一直都在不斷跨越“文言白話”的鴻溝,都沒有把對方當堂·吉訶德的風車來搏斗,也沒有抱怨“看不懂”,他們并非徒然擊打空氣,往往倒能夠搔到對方的癢處,彼此要講什么也心知肚明。知識界因語言和話語問題引發的千年未有的大分野為何奇跡般地并未導致基本語言認同的喪失?
我想主要因為文白兩大陣營盡管觀點相左,知識譜系大相徑庭,所屬社會政治的派別壁壘分明,白話和文言作品的情感經驗和想像天地也相去甚遠,但主張白話的能操文言,保守文言的也并非不能用白話。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本身就是淺近文言,林紓1897年創作的幾十首《閩中新樂府》則被胡適稱為“當日的白話詩”予以揭載(胡適《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1920年代文言衛道士吳宓到了30年代已公開主張對白話文不妨“‘異量之美’,兼收并蓄”,他還欣賞《子夜》的語言,認為“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種可讀可聽近于口語之文字,近頃作者所著之書名為語體,實則既非吾華之語亦非外國語,惟有不通之翻譯文字差可與之相近”,茅盾本人對吳宓的評價也頗為首肯,甚至說“《子夜》出版后半年內,評者極多,雖有亦及技巧者,都不如吳宓之能體會作者的匠心”(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吳宓的學生錢鍾書則認為“茍自文藝欣賞之觀點論之,則文言白話,驂驔比美,正未容軒輊”,白話文的流行還會增進文言的彈性,反過來文言也會影響白話文,比如現代小品文就取法晉宋以迄明代的小品而“盡量使用文言”,他甚至預言“將來二者未必無由分而合之一境”(錢鍾書《與張君曉峰書》)。文言白話在現代學人那里“明隔暗通”,論爭雙方擁有遠遠超過后來同在白話世界討生活的人們彼此之間的語言認同。晚清士人歷數“言文分離”的害處,其中一點叫做“手口異國”④,不免形容太過,但今日許多長篇大論盡用白話,而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國民能夠聽懂看懂的,恐怕倒真的寥寥無幾了。
再看新文化陣營內部,胡適和魯迅同治小說史,一寫白話,一操文言,并不妨礙彼此呼應、相互欣賞。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護法,始終關心新文學發展,晚年日記還大段摘引巴金小說《電》、《雷》原文(《蔡元培日記(下)》),但蔡元培平日著述、書信、日記,仍以文言和“語體文”為多,他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撰寫的總序以及回憶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堪稱優美的白話文,但若衡以胡適的白話文標準,恐怕都還不夠“白”。蔡元培有言:“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后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可見對這種亦文亦白的文體實踐,蔡元培是有充分自覺的。在現代像蔡元培這樣兼跨文白兩界的現象十分普遍,他們的文章往往“文白夾雜”。過去根據簡單的進化論,總認為“文白夾雜”是現代白話書面語的初級階段,或借用魯迅的自謙的說法,認為“文白夾雜”是白話文進化過程中的一個“歷史中間物”,其實“文白夾雜”的現代作者們雖然還不能做到絕對的“白”,卻比較善于融匯各種語言因素而基本達到“文從字順”的境界,也基本能夠避免令人“看不懂”。
2、 現代學者大量的優秀“語體文”著作從另一側面證明當時中國學術文化界雖有文白之爭,卻“明隔暗通”,無論主張白話還是保守文言的人都不難在“語體文”中部分地找到他們所主張的語言的理想和所固守的理想的語言。
關于“語體文”不妨多說幾句,這至今仍是尚待確切定義的概念。就其脫離文言舊軌而比較接近口語來說,一般認為“語體文就是白話文”固然不錯,但現代學者“語體文”著作(如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馮友蘭《貞元之際六書》、陳寅恪考據文章、錢穆《國史大綱》等)即便和同時期白話文著作相比,文體差異也一望可知。“語體文”作者不想充分口語化或白話文化,但他們所寫的畢竟又不同于文言文,不僅加入許多口語因素,所保留的文言因素也大大縮減并通俗化了。“語體文”的前身或許是清末“新文體”,但現代學者的“語體文”主要闡發學術思想,已脫盡“新文體”的報章氣息,告別政壇而退守書齋的梁啟超本人的“語體文”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明顯不同于早年專為報章而寫的“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文體”。部分現代學者不肯徑用已經流行的“白話文”概念而另稱其文章為“語體文”,乃是故意要和白話文有所區別,對此熊十力的意識就很明確,他說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雖是語體文,然與昔人語錄不必類似。此為理論的文字,語錄只是零碎的記述故。又與今人白話文尤不相近。白話文多模仿西文文法,此則猶秉國文律度故。大抵此等文體不古不今,雖未敢云創格,要自別成一種作風”(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初印上中卷序言》)。或者可以說,“語體文”是在白話文流行之后,一些不愿躋身白話文作者行列而又自覺不能再寫純粹文言文的現代學者有意探索的介乎文言白話之間的一種特殊文體。錢穆雖無熊十力那樣的文體自覺,但1930年代中期修訂《國史大綱》時也感到過去《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用文言已不甚適合,《國史大綱》需面對更加廣大的讀者,他們雖“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錢穆《國史大綱·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卻往往“于本國文字素養太差”(錢穆《國史大綱·書成自記》),這就迫使錢穆不得不使其慣用的文言文淺顯化,增加“語體”的成分。單純從文言或白話的角度很難給“語體文”下一個準確定義,因為“語體文”作者們有意“別成一種作風”。一定要追本溯源,僅就其長于說理的一面而言,現代學者“語體文”與其說源于“新文體”,毋寧更近于中譯《圣經》的“淺文理本”。不同學者“語體文”風格也很不相同,他們既然不把“語體文”看作文白之間臨時的過渡品或替代物,而是經之營之,矢志靡它,其文化精神自然灌注其中而極富個性,比如王國維、陳寅恪表面上屬于淺近文言實則具有語體(乃至歐化)性質的論著,讀者既可以帶著學術問題去研究,也完全可以當做寄托作者人格的“美文”來欣賞。“先生之著作,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而與此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同樣不朽的應該還有他們的文章格調罷?胡適說陳寅恪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嫩(懶?),不足為法”(胡適1937年2月日記,引自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很可能是不滿陳寅恪始終不肯寫白話文,以及所謂“遺少”氣味(胡適語,參見余英時《陳寅恪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但“遺少”與否同文章好壞無關,而白話文也并不合適做“語體文”的標準。據說錢鍾書認為“從文言的標準看,陳氏的文言文就顯得不夠典雅”(參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這恐怕也用錯了標準,因為陳寅恪文章是一種別致的“語體文”,而非錢氏心目中的文言文。以“述學之語”而論,陳文美感實在十分彰顯,不僅有從孟子、韓愈而來的浩然之氣(絕無現代白話文以及某些現代學者的文言文習見的鄙吝、油滑、做作、賣弄),更有源于孟、韓而又暗中吸取西文語法、幾乎為陳寅恪所獨具的那種一唱三嘆與清明周致。在整個現代中國學術語言演變史上,陳寅恪的文風高標獨舉,罕有倫比,其論著可當特殊種類之“美文”欣賞的何止《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贈蔣秉南序》、《柳如是別傳·緣起》等議論而兼抒情之作(這些文章胡適和錢鍾書都寫不出)。陳文之美感,不單源于類似其詩作中俯拾即是的興亡之感與文化托命意識,更深植于《四聲三問》、《從史實論切韻》、《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東晉南朝之吳語》、《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元白詩箋證稿》等論著所顯示的對漢語言文字之特點及其與中國文學之關系的深切把握與獨到見解⑤。在現代學術史上淬煉其“語體文”而能“成一家之言”的何限陳寅恪一人,此處僅以他為代表,略述這種常遭誤會的特殊體式的“述學之語”所蘊含的現代中國學者的語文認同。
3、 我一直覺得,很可能因為知識界和大部分官員在文白問題上“明隔暗通”,國民政府才不肯聽從胡適勸告,棄文言而就白話(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而是安居文言天地,意識不到“五四”以后全社會的語言轉變,失掉了以白話為一元主導的更大范圍的新的語言認同,遂于政治軍事敗北之前,在語言文化上先輸一城。相反,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中共與國民政府公文往來,中共領導人與國民黨高層或民主人士通信,基本以文言為主,有意遷就后者的語言政策和語言習慣⑥,而內部則力求使用日益成熟的白話文⑦,這實在是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文言白話“明隔暗通”的情勢,用文言的手段與國民黨政府周旋,在自己控制的領域則清醒地依靠“五四”以來以白話為一元主導的全新的語言認同。靈活的語言策略不僅確保了中共語言文化取向在全民族范圍的先進性,也極大地鞏固了自身組織的嚴密性,提高了具體工作的有效性,從而在政治軍事全面勝利到來之前,已然贏得了語言文化的勝利。
倘若上述猜想屬實,豈不更反證了文言白話“明隔暗通”如何保障著知識界和政府各部門的可溝通性,乃至被蒙蔽的國民政府直到敗退臺灣之前都未能察覺正在崛起的以白話文為一元主導的新的語言認同的偉力嗎?一邊是文言白話“明隔暗通”,一邊是白話文一統天下,兩種語言認同的共存深刻影響了兩大政治集團的命運,卻并未造成知識界語言溝通的困難。
4、 1923—1924年“科玄之爭”,參加者流品甚雜,彼此知識背景和學術取徑差別很大,對話往往難有交鋒,整體學術水平并不高,胡適為后來結集的《科學與人生觀》作序,甚至說這場論戰差點“成了一場混戰”,陳寅恪則譏之為“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英文”(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但大家并未抱怨“看不懂”對方文章,更未感覺到語言溝通上有障礙。現代哲學家們都很注意盡量不為讀者設置語言障礙,“科玄之爭”中的梁啟超、張君勱、梁漱溟、丁文江、陳獨秀、吳稚暉是這樣,在一般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美學史研究領域用白話文或“語體文”撰述而影響較大的胡適、金岳霖、馮友蘭、熊十力、賀麟、張蔭麟、宗白華、朱光潛等也莫不如此。現代中國哲學旨在匯合中西,融通古今,同時對廣大讀者負有啟蒙任務,這就迫使哲學家和哲學研究者們在語言表達和話語運用上努力做到“深入淺出”、“為淺人說法”,“極高明而道中庸”。
近來哲學界頗有人批評現代中國哲學尚未“走出翻譯時代”,因為現代中國哲學主要通過翻譯來建構自己,而這就是“一切精神贗品、思想譯本的根源”,“我們身處的這個翻譯時代遠未終結,而能夠守護思想的、真正的現代漢語也尚未到來”(丁耘《走出翻譯時代》,《知其不可譯而譯之》)。這自然也有其所見,但論者似乎忽略了現代中國哲學家們如何沉潛往復,殫精竭慮,努力將“拿來”的西方哲學與中國既有思想融會貫通,憑借漢語言文字所涵蓄的中國智慧加以闡發說明,務使其能為中才以上的讀者所理解。“心通而辭達”的“翻譯”并用漢語加以重新表述的功夫本身就是哲學探索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舍此即無從建構所謂中國自己的哲學。抗戰期間馮友蘭《貞元六書》借西方哲學方法(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和部分的馬克思主義)整理中國古代哲學,在此基礎上建構“新理學”體系,提出他對當時中國社會、家庭、政治、戰爭、道德、藝術、教育各方面的見解,一時激起不少爭議,而馮氏也盡顯其過人的文字功夫⑧,他能將一切概念都放在中西哲學和文化大背景前解析開來并充分調動“五四”以來白話文資源而使之成為明白曉暢的日常談話⑨。再如熊偉譯海德格爾,不僅為80年代以后海德格爾的翻譯熱、研究熱開了先河,許多譯名也給后來者以啟迪,如譯Dasein為“親在”,就不易為后起譯家隨便改換。當代中國哲學家在“哲學學”上固然不難后來居上,但僅就語言文字論,先賢仍有后學所不可及處。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們大多并不具備現代中國哲學家們的語言文字功底。
5、 現代甲骨2Bk8nwUDuZitx8vsNX64a5J/tk/RCMEdWWsKaOk+tV4=學有“四堂”之說,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郭沫若(鼎堂)的身世、經歷、學養、方法、趣味相差極大,但學界公推他們是甲骨學四大重鎮,他們之間或彼此欣賞,或有所商兌,學術語言上并無分裂與隔絕。再看甲骨學和古史辨,信古和疑古,作為現代“上古史學”雙翼,對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史學”之建立關系甚大,雙方觀點有時冰炭難容,但“述學之語”仍可相通。和上述古文字學、現代新史學相關的現代時期歷次讀經與反讀經的爭論也有類似情況。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文化運動許多領袖人物如蔡元培、魯迅、陳獨秀、曹聚仁、周予同、傅斯年等都先后著文反對“讀經”,其中郭沫若與胡適的學術訓練不同,政治立場的分化昭昭在人眼目,郭沫若還曾撰《駁〈說儒〉》,尖刻地諷刺胡適《說儒》于甲骨文金文不懂裝懂,但正是這兩位所寫的反讀經的文章,不約而同引王國維為例,認為就連王氏都承認《詩經》、《尚書》有許多地方看不懂,又怎能鼓勵普通人或中小學生讀經(胡適《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郭沫若《沸羹集·論讀經》)?當時已屆暮年的章太炎寓居蘇州,力疾為諸生講國學,見到胡適等反對讀經的文章后,不管他們抗議無知軍閥和政府教育部門的背景,對以王國維的話為借口而主張“不配讀經”的論述方式大加撻伐。章太炎認為不必將王國維“奉以為宗”,因為經學之于王氏也“本非所長”,即使王國維的話符合事實,也不能作為后人不配讀經的借口,當年高郵王氏父子就并非先認全了經書上的字才來讀經,而是“奮志為之,成績遂過前賢遠甚。使高郵亦曰我不配讀經,則亦終不能解矣”。他的結論是要在胡適等人“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之后立即加上一句:“以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讀經”(章太炎《星期講演會記錄》第五章《再釋讀經之異議》)。其實郭、胡與章太炎的觀點并非完全相左,他們說“不配讀經”,只是說經典太難,不適合一般人和中小學生,并未說不許學者去研究,而章太炎所謂“不得不急急讀經”,也并未否認經書之難讀,或主張一般人乃至中小學生“急急讀經”,其所囑望的也是少數學問精深的學者。無論如何,上述爭論皆顯示了胡適、郭沫若、章太炎等對共同的語言傳統中那些看不懂的部分的敬畏,所謂“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許慎《說文解字敘》)。反推過去,他們對共同的語言傳統中可以讀懂的部分的珍惜愛重也不言而喻。正是這種對民族語言遺產“橫豎是水,可以相通”的態度形成了現代中國學者相對穩固的語言認同。
6、 1928年,后期“創造社”諸君子用魯迅當時已開始接觸但自知還不甚諳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批評魯迅,諷刺他“醉眼陶然”,看不清社會現象,魯迅則毫不客氣地指出對方在軍閥和民眾之間態度曖昧,這里留一點朦朧,那里留一點朦朧,論爭不可謂不激烈,以至一方首領污蔑魯迅是法西斯蒂加封建余孽的“二重的反革命”[杜荃(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數年之后魯迅也給對方送去了“才子+流氓”的雅號(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對創造社理論批評的文風并不怎么恭維,創造社的批評家成仿吾對魯迅的語言也一直有所非議⑩,但無論當時還是日后,雙方都沒有說對方發生了嚴重的語言問題,或宣布交流有障礙。
7、 20世紀20年代中期瞿秋白和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理論家大打理論戰,一用白話,一用文言,并未減卻論爭的白熱化程度,足見雙方在文白易趣、理論背景迥異的復雜政治理論話語層面的可溝通性,這自然有賴于他們在政論語言上化難為易、化生為熟、化深為淺的功夫。戴季陶罵瞿秋白“癆病鬼”,卻不敢說瞿秋白文句不通;瞿秋白痛恨戴季陶的反動思想,也不能說戴季陶缺乏語文基本功。1930年代初期,瞿秋白從政治領導崗位退下來,暗中指導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寫下大量文學論文,攻擊“五四”興起的白話文乃是胡適之流學閥買辦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但他自己使用的也是這種白話文,并非所主張所向往的“大眾語”,以至于胡適反唇相譏:“現在許多空談大眾語的人,自己就不會說大眾的話,不會做大眾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眾化,這真是不會寫字怪筆禿了”(胡適《大眾語在哪兒?》)。無論與政治上的對手如戴季陶還是文化上的勁敵如胡適之間,瞿秋白都一直保持著基本的語言認同。這也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在語言上的一個共同點。
以上七例涉及語言論爭、哲學、史學、政治評論、文學批評諸多領域,自然不能涵蓋現代學術之全體,但也足以說明現代學術界在日趨分裂的同時仍能維持基本的語言認同。
但這并非說現代學者的語言千篇一律,毫無差別。實際上隨著學術演進,現代中國“述學之語”和同時期的“文學語言”一樣都有激烈分化,但這種分化并未造成不同的學術領域和文學流派以及學術文學與社會語言母體之間彼此脫離,乃至發生學者、作家和讀者的交流困難,而是分化中仍有溝通,參差不齊中仍隱然見出一種秩序。這方面還可以舉兩個極端的例子。胡風理論批評文章個性強烈,不易讀解,但這并不影響他在1930年代批評周作人、林語堂等一大批作家(參見胡風《林語堂論》,《“靄理斯的時代”問題》),也不影響被批評者提出反批評(周作人《靄理斯的時代》)。到了抗戰時期,胡風的文風也沒有影響他與重慶各界文化人士共事交往。趙樹理和張愛玲的小說語言一土一洋,趨于極致,但假設二人有機會接觸對方作品,也不會發生“看不懂”的問題吧?
文學、學術在分化,文學語言和學術語言也不得不發生劇烈分化,但操不同語言的作家學者仍能保持有效的語言溝通,他們一方面大膽拆除漢語言文字的藩籬,吸納巨量的外來語言要素,改變千年如斯的書寫和欣賞習慣,同時努力維持漢語言文字生命所系的基本同一性。這個局面可用一句話來概括:“道術必為天下裂,語文尚待彌縫者。”前句典出《莊子·天下》,我改“將”為“必”,因這已是后世學術發展所一再昭示的事實。后句出自陶潛《飲酒》第二十首:“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過去重視現代學術界的分野、分化、分裂,忽略了現代學人以其基本的語言認同所完成的“彌縫”之功。周作人特別欣賞陶潛用“彌縫”一語評價孔子的勞績,“這彌縫二字實在說得極好,別無褒貶的意味,卻把孔氏之儒的精神全表白出來了。”(周作人《自己所能做的》)張愛玲也說“我們中國本是補丁的國家,連天本是女媧補過的”,她愿意在“補丁的國家”和“補丁的彩云的人民”中“沉到底”(張愛玲《中國的日夜》)。周、張兩位對中國思想傳統和生活(情感)方式的描繪頗多相通之處,也頗能借過來說明現代中國文化人對大變動中的漢語言文字的愛惜敬重之情以及竭力使其獲得新生的虔誠努力。
① 胡風對其理論批評文章的“難讀”也有充分自覺。他堅信新文學既然是世界進步文學在中國新拓的一個支流,就勢必要在與各種主客觀的舊勢力痛苦“掙扎”、“搏斗”中開辟道路,無論內容或形式都不可能是現成的,而必須是探索性創造性的,創作和理論批評的語言令人感到陌生,因此也就十分自然,比如那種明顯的歐化句式。胡風的語言冗長、糾葛,卻并無多少實質上的“不通”。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提到胡風在理論上有拘泥的傾向,文字不肯大眾化,并沒說這種傾向造成了文理不通、用詞不當。這是我們在討論現代文學創作和學術理論批評的“難懂”時應該注意的一點。
② 被胡適稱為“科玄之爭”的“壓陣大將”的吳稚暉,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中宣布他看不起那些“不能叫人簡單了解,存心擺他學者的臭架子”的各種“學”,“一變成‘學’,便必定容易忘了本旨——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而他自己則是“鄉下老頭靠在‘柴積’上,曬‘日黃’,說閑空的態度”,是柴積上日黃中的“瞎嚼蛆”。引文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出版、羅家倫與黃季陸主編之《吳稚暉先生全集》(卷一)第1頁至第94頁;對“吳稚暉體”的分析,參見郜元寶《惘然集》,第18頁至第26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③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劉勰原是描述文學創作中言不稱意的現象,這里借來指學者找不到合適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
④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三《學術志》(二)“文字”篇:“居今之日,讀古人書,徒以父兄、師長遞相授受,童而習焉,不知其艱,茍跡其異同之故,其與異國之人進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辭者,相去能幾何哉?”。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于是文與言判然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為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
⑤ 吳宓《空軒詩話》有言,陳寅恪“《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及近作《四聲三問》一文,似為治中國文學者所不可不讀者也”。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⑥ 國民黨高層和民主人士也有寫白話文的,如吳稚暉、馮玉祥等,但究屬少數,而“黨國要員”們的文言也有深淺難易之別,某些人(如陳布雷)的文言文已近乎“語體文”,但與純粹的白話文仍有根本不同,這里只能概乎言之。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及其前后,中共與國民黨高層書信往來多用文言,直至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廖承志致蔣經國公開信,仍沿襲這一習慣。1949年以后臺灣當局的公文雖仍以文言為主,整體上已經由深轉淺,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給廖承志的復信就是一例,但由此更可以見出中共高層針對國民黨的語言策略之歷史養成的慣性力量。
⑦ 毛澤東從1940年代“延安整風”開始,就一直關注黨和國家重要媒體和領導人的文風問題。建國初期,他還應胡喬木之請,委托胡喬木專門就各大區領導的公文寫作風格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力求使公文寫作達到簡練明晰的境界,并直接指示安排呂叔湘、朱德熙在《人民日報》連載《語法修辭講話》。該報還專門為此配發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明確指出:“我們的學校無論小學、中學或大學都沒有正式的內容完備的語法課程。”“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現思想,在今天,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一段時間內全國范圍掀起了學習語法、教學語法、研究語法的高潮。也就在這種氛圍中,《中國語文》、《語文學習》、《語文知識》等相繼創刊。學校普遍加強了語法教學,機關干部、工人、部隊也開始以《語法修辭講話》和其他語法著作為教材,動員范圍之廣,史無前例。
⑧ 何炳棣認為馮友蘭之所以能以北大出身而居清華大學要津達二十年之久,除了頭腦清晰、深通世故和善于辦事之外,另一個十分重要原因就是“國學根底雄厚,文言表達能力特強”,他認為出于馮友蘭之手的一些“公文”對清華大學的發展功莫大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則是不朽的“至文”。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185頁,中華書局2012年6月第1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開頭很像毛澤東撰寫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文的句式,這是偶然巧合還是有先后影響的關系?值得探討。另何氏所謂“文言表達能力”大可擴張為“文字表達能力”而不必限于文言文。馮氏在現代哲學界享有盛名與其特出的文字功底有關,正如1980年代以來李澤厚的廣受歡迎,也離不開他在文史哲三界均罕有倫比的辭章功夫。肯定馮、李的辭章功夫,并不會導致對他們的哲學理論水平的低估。
⑨ 馮友蘭對哲學語言的重視固然受到維也納學派影響(同時鼓吹維也納學派最有力的還有在昆明主編《學術季刊》的洪謙),但與其扎實的中國語文修養也大有關系,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往往有賴于傳統的文字訓詁,許多地方都能提出一己之見。這也不限于哲學,他對李商隱“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解釋就發人所未發。這個特點實為當時許多哲學家所共有,馮氏就曾借用沈有鼐的說法,認為“六十而耳順”應為“六十而已順”,“耳”是“而已”急呼而成的合字。馮氏又能利用“五四”以來的白話文資源,他在嚴格的語法意義上使用“底”字,就使人自然聯想到魯迅的獨特的翻譯文體。馮友蘭的這個特點被康生看到了,他說“馮友蘭的哲學,說什么抽象的意義,實際上他的哲學并不是什么哲學,說好一點是語言學,只是玩語言上的詭辯”。見1958年6月5日《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開的政治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此處引自陳徒手《馮友蘭:哲學斗爭漩渦歷險記》,《書城》2012年12月號,第6頁。
⑩ 成仿吾《紀念魯迅》(1936)認為“他(按指魯迅)的文學與寫作都不通俗,不易為一般所了解”,《成仿吾文集》第277頁,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