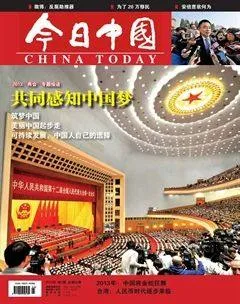讀書與做官
凡是上世紀(jì)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在學(xué)校讀書、教書的人,大概都參加過對“讀書做官論”的批判。當(dāng)時的批判者都認(rèn)為:“讀書做官論”的老祖宗就是孔子,而《論語》中“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讀書做官論”的理論基礎(chǔ)。因此對其開展了批倒批臭的口誅筆伐。按照當(dāng)年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工農(nóng)兵學(xué)員著述的《〈論語〉批注》中的解釋,“學(xué)而優(yōu)則仕”譯成白話就是:“學(xué)習(xí)好的人就可以做官。”依據(jù)這種解釋的大批判,使舉國上下都認(rèn)為讀書做官是極為丑惡的事情,從而導(dǎo)致“讀書無用”風(fēng)潮出現(xiàn),學(xué)校教育遭到極大破壞。以至當(dāng)時還出了一位由于考試交白卷被樹為榜樣、成為英雄的人物。
幾年前,我在報上讀到一條消息,說的是一位國有企業(yè)負(fù)責(zé)人調(diào)到某省任副省長,標(biāo)題是:“商而優(yōu)則仕”。顯然標(biāo)題延續(xù)了文革中對“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荒唐解釋,是說“經(jīng)商辦企業(yè)好的人就可做官”。直到幾個星期前,我在報上看到一篇寫“做學(xué)問與做官”的文章。文章批評中國知識分子,“做學(xué)問并不是為了學(xué)問本身,也不是為了用學(xué)問服務(wù)于社會,而是拿學(xué)問作為換取世俗地位的籌碼”。作者痛斥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特點(diǎn),認(rèn)為,“這個特點(diǎn)與中國文化中‘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理念一脈相承”。顯然作者對“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理解仍然是:學(xué)問好的人就可以做官,就可以換取世俗地位。
為什么對“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荒唐理解可以延續(xù)至今呢?我以為,沒有對半個世紀(jì)前文革中荒唐的批判進(jìn)行正本清源,以恢復(fù)歷史本來面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學(xué)而優(yōu)則仕”出自《論語·子張》。原文是這樣的:“子夏曰:仕而優(yōu)則學(xué),學(xué)而優(yōu)則仕。”
這段原文透露了兩個信息。其一,“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子夏說的,不是孔子說的。子夏是孔子最優(yōu)秀的學(xué)生之一,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和傳播者。當(dāng)然,這句話到底是子夏自己的思想,還是重復(fù)了孔子對他的教導(dǎo),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白紙黑字,歷朝歷代的《論語》讀本都是這樣記載的。因此,把這句話強(qiáng)加在孔子頭上進(jìn)行批判,是不公平的。其二,子夏在這里說了兩句話,是兩句關(guān)聯(lián)密切的話,而不是遭到批判的那一句話。如果按照文革中《〈論語〉批注》的解釋,“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學(xué)習(xí)好的人就可以做官”,那么,“仕而優(yōu)則學(xué)”就應(yīng)該解釋為:“做官好的人就可以學(xué)習(xí)”了。是拜師學(xué)習(xí),去學(xué)校學(xué)習(xí),為什么官做好了反而要倒退回去學(xué)習(xí)呢?很顯然,把兩句話聯(lián)在一起,就解釋不通了。
子夏的兩句話:“仕而優(yōu)則學(xué),學(xué)而優(yōu)則仕”,共計(jì)10個字,但只使用了5個漢字。第二句話是把第一句話中的“學(xué)”和“仕”顛倒了一下位置而已,中間3個字沒變化。也就是兩句話的句式是一樣的。我們逐字解釋一下。
“仕”和“學(xué)”在每句話第一個字的位置上,應(yīng)該是名詞屬性。“仕”可以解釋為“在朝廷做事的人”,這種人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被稱為“仕”,也可以理解為“有小官職的人”。“學(xué)”可以解釋為“讀書人”,或“在學(xué)堂學(xué)習(xí)的學(xué)生”。
“仕”和“學(xué)”在每句話最后一個字的位置上,應(yīng)該是動詞屬性。“仕”可以解釋為“出仕”,春秋戰(zhàn)國時代,出去為朝廷做事稱為“出仕”,也可以說是“出去當(dāng)個小官”。“學(xué)”可以解釋為“讀書”或者“學(xué)習(xí)”。“而”和“則”是兩個連接詞,在兩句話里每個詞都可以做同樣解釋。“而”是虛詞連接,可以不做具體解釋。“則”可以解釋為“就”、“就可以”、“就應(yīng)該”都行。
這兩句話的關(guān)鍵在“優(yōu)”字的解釋。漢代《說文解字》上講:“優(yōu),饒也。”饒是富饒的饒,是多余、富裕的意思。顯然,在漢代以前,也就是《論語》產(chǎn)生的時代,“優(yōu)”字不做“優(yōu)秀”講,而是做“多余、富裕”講。《論語》在宋代被朱熹收入“四書集注”(即我們常說的“四書五經(jīng)”的“四書”)。朱熹在《論語章句集注》中注釋:“優(yōu),有余力也。”朱熹準(zhǔn)確地詮釋了“優(yōu)”的含意。
根據(jù)上面我們逐字的解釋,“仕而優(yōu)則學(xué),學(xué)而優(yōu)則仕”應(yīng)該解釋為:“為朝廷做事的人有了余力時就應(yīng)該讀書學(xué)習(xí);讀書人有了余力時就應(yīng)該出仕,為朝廷為國家做點(diǎn)事。”
我們這樣還原了原著的本意,與荒唐年代批判的所謂“讀書做官論”還有什么關(guān)系嗎?應(yīng)該說,“仕而優(yōu)則學(xué),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儒家的教育觀念,也是儒家政治觀念。
從教育角度看,“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讀書人有了余力,可以報效國家,出仕為官,把學(xué)來的知識(包括道德修養(yǎng))用于實(shí)踐,不致于越學(xué)越脫離社會實(shí)際,是我們常說的學(xué)以致用;而“仕而優(yōu)則學(xué)”是要求為國家做事的官員有了余力,要多讀點(diǎn)書,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提高自己,是一種繼續(xù)學(xué)習(xí)。從政治角度看,“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儒家主張的:讀書人有了余力,應(yīng)該盡可能地出仕為官,在為國家效力的過程中,推行儒家的“仁政”;而“仕而優(yōu)則學(xué)”是儒家主張的:為官者要不斷增加學(xué)識,開闊心胸,提高施政水平。
子夏把“仕而優(yōu)則學(xué)”放在“學(xué)而優(yōu)則仕”之前,似乎在強(qiáng)調(diào)為國家做事的為官者的學(xué)習(xí)更為重要。看看今天我們身邊的各級干部——為國家做事的為官者們——整日忙于會議、忙于政績者有之,整日迎來送往、吃吃喝喝者有之,甚至上了某種學(xué)校,也是花大量時間請客送禮、串門跑官,哪里還有功夫讀書學(xué)習(xí)呢?我以為,“仕而優(yōu)則學(xué)”的觀念還是很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
反觀把“學(xué)而優(yōu)則仕”當(dāng)作“讀書做官論”橫加批判的荒唐年代,不就出過這樣的官員,當(dāng)著外國人的面問下級:“寫《本草綱目》的李時珍同志今天來了嗎?”連李時珍是明朝人都不知道的人能做很大的官,是不是很荒唐呢?今天,已經(jīng)沒有人懷疑當(dāng)官之前必須讀書了,文憑已經(jīng)成為“出仕為官”的門檻。是不是有了文憑就具備了報效國家的文化和學(xué)養(yǎng)了呢?須知,儒家所講的“學(xué)”,是包括知識技能(即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和道德修養(yǎng)(即所謂四科:文、行、忠、信)兩大方面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仕而優(yōu)則學(xué),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人類文明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