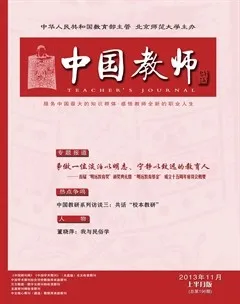今天,我們該如何讀《弟子規》
中山大學要求新生入學時,須向院系輔導員提交閱讀《弟子規》的感想,招致爭議一片:反對者如袁偉時教授,直斥《弟子規》是文化垃圾,是培養奴性的工具,是毫無操作性可言的陳腐教條;中山大學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現代大學校園的一出笑劇,也是一出令人心痛的悲劇。贊同者認為重溫那些樸素的道理與準則,能使現代大學生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有益于規范他們的行為方式,既有利于傳統文化的承傳繼絕,也是現代大學自主辦學的有益嘗試。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現代大學生該不該讀《弟子規》,而在于以怎樣的情懷來對待和以怎樣的態度去閱讀它。
把包括《弟子規》在內的古典文本當作心性之學、當作道德之學來看待,認為誦讀這些道德色彩極為厚重的古代典籍,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改善,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建構,甚至能夠療治當今社會的亂象,這是現今很多倡導和參與讀經活動的人們的主要目的。中山大學的用心顯然也基于此。實際上,這種愿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國民素質的提高、社會的道德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合力。寄望于弘揚傳統文化,或者背誦《弟子規》來解決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不過是一些人不切實際的想法。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讀經的社會,即便是全社會讀經,也沒能提升人們的道德境界,凈化社會風氣,療治社會的亂象,挽救一個又一個王朝的危亡。我們應該客觀看待、審慎評估古代經典在當代道德建設中的作用,不能過高估計它的價值,不能過分夸大它的功用,不能對它寄予過高的期望。閱讀《弟子規》并不能解決當今大學生的道德問題,不能解決他們不孝敬父母、不尊重師長、不寬容同學等問題。我們不能不顧變化了的情勢,不分辨其一般原則和具體內容,不加轉化地生搬硬套,原封不動地拿來就用。
如果把《弟子規》當作道德之學來看待,學習《弟子規》是為了了解和掌握其中的規條,用來指導自己的日常行為,那么,對于《弟子規》只能是虔誠地敬畏和恭謙地接受。因為它的原則出自圣人之口,具體儀則源于賢者之手,是道德的指南和行為的準則,除了記誦、踐行之外,是別無審視、探究的空間的,更不必說質疑和批判了。雖然一些人會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實際上,這里對學生的要求,首先還是不加懷疑地相信和接受。因為有了這樣的前提——學習《弟子規》會有益于規范我們的言行,學校不接受自由的思想,學生不敢有獨立的精神,所以才出現很多學生從網絡上復制作品、獨立完成較少的狀況。于是就出現了很滑稽的現象:在道德教育的名義下,干的卻是自欺欺人、背離道德的勾當。浪費大量的資源不說,還導致大家普遍的對道德的輕忽和褻玩。不適當的道德教育,造成了道德的虛偽,其惡果甚至比道德教育的缺失還嚴重。包括中山大學在內的我們社會普遍的做法,實在是得不償失。
還有一種視角,就是把《弟子規》當作一種知識之學、文化之學來看待。也就是說,學習《弟子規》不是為了踐行其中的眾多的規矩,不是為了力行其中的“勸”、力戒其中的“禁”,盡管這里的訓誨勸誡會對我們的道德心性有潛移默化的作用;而是把它當作透視清朝初年道德教化的一扇窗口,理解古代道德教育內容和方法的一條途徑,認識傳統禮儀和習俗的一個渠道。這樣,即便是已僵死的教條便有了生機,哪怕是最陳腐的道德也就有了意義。比如,人們一再作為詬病例子的“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喪三年,常悲咽;居處變,酒肉絕”,這是古代的禮制,是古人的習慣或道德準則,與現代人是否踐行無關。而學習《弟子規》,正是為了認識古代中國的禮儀規范,了解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探究中國的古代文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弟子規》就不是一個遵奉的對象,而是一個探究的對象。遵奉的取向重在記取和掌握,并用于約束自己的行為,在生活中踐行,它的前提是相信和接受。而探究的取向則是為了了解和認知,明白它說了什么,為什么會這么說,這么說的意義何在,它的前提是質疑和批判。讓學生學會批判性思維,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獨立自主地運用自己的理性,超越這樣那樣墨守陳規的條條框框,正是大學的意義所在。從這個意思上說,《弟子規》這個歷史上與《三字經》爭奪啟蒙課堂的讀物,大學生不僅應該讀,而且必須讀。它的那些規條在現代具有怎樣的價值?對于我們當今的文化建設是否有和有怎樣的價值?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再者,《弟子規》憑什么能與《三字經》爭鋒,并在特定的地區一度使《三字經》“幾廢”,它的魅力何在?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很多人認為讓現代大學生去讀過去五六歲小孩念的傳統啟蒙教材很可笑。實際上,視這種現象為可笑才真正地可笑。現代大學生的國學素養普遍較低、傳統文化知識較為缺乏,而傳統的啟蒙課本知識豐博,編寫得體,很多讀物就像是一部百科全書,是傳統知識結構的縮影。其深厚的人文意蘊、豐贍的知識結構、精致優雅的祖國語言、巧妙精工的組織形式,是一些有知識、沒文化的現代啟蒙讀物難以望其項背的。它們之所以能進入啟蒙的課堂,并深得一代又一代兒童的喜愛,主要是因為表現形式淺顯通俗。它們過去培育了包括眾多杰出學者和優秀文人在內的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現在依然是人們了解傳統文化、學習傳統知識的有效途徑。我曾在課堂和各種場合,力勸人們讀《幼學瓊林》,如果把這本書讀熟了,傳統文化知識會比自己的同學和同事豐富很多;如果把這部書讀通了、讀精了,國學素養甚至會超過很多教授。
在某個特定時代,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往往是特定社會意志和追求的反映,也是一個時代性格氣質的最典型、最集中的體現。通過考察歷代啟蒙讀物和社會變革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舊時兒童閱讀的作品,其實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扇非常有效的窗口。歸根結底,傳統啟蒙讀物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載體。通過傳統的啟蒙讀物,我們可以了解我們的教育歷史,了解我們身上的文化基因。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國學經典教育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何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