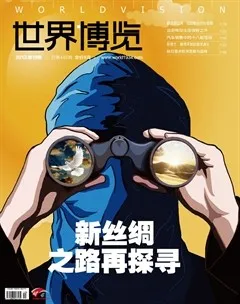拉伯世界的改革者和獨裁者

身高接近1米90、長著一雙深邃的藍眼睛的巴沙爾·阿薩德一點也不像人們心目中的暴君。但正是這位看起來安靜謙和,甚至有些羞怯笨拙的年輕的敘利亞總統,被指控為所有阿拉伯獨裁者中最肆無忌憚地鎮壓民眾民主訴求的魔鬼。有關他對自己同胞使用化學武器的消息是近來國際輿論的焦點,他的“垂死掙扎”無情地粉碎了那些曾天真地期待他成為一個開明改革者的幻想。
巴沙爾在英國求學時的老師、眼科醫生埃德蒙·舒倫堡近日在接受《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采訪時悲傷地表示自己無論如何都難以相信“那個我認識的年輕人會下令使用化學武器……這可能是那個政府中其他人的決定。”
我愿意相信,舒倫堡醫生心目中的那位年輕人與今天西方報紙上的敘利亞總統都是真實的,它們折射出這位阿拉伯世界年輕獨裁者的復雜人生的不同側面。
1994年,巴沙爾的父親、有“中東雄獅”之稱的敘利亞前總統哈菲茲·阿薩德著意培養的接班人——長子巴西勒在前往機場的一次車禍中遇難。老阿薩德不得已,決定召回當時正在倫敦學醫的巴沙爾,培養他成為新的接班人,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2000年,當不滿35歲的巴沙爾·阿薩德從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父親那里承繼大位,成為這個被稱為“阿拉伯世界心臟”的國家的新領導人時,他曾經被敘利亞、中東乃至全世界寄予厚望。年輕、開明、溫和、現代……這是上任伊始的巴沙爾留給敘利亞人民的第一眼好印象,而他的西方教育背景也使外部世界相信,他能夠在這個族群復雜、教派繁多的社會里繼續推行世俗化路線,處理好與以色列和西方的關系。
巴沙爾似乎也愿意響應民意,他在就職之初就承諾,會穩步推進民主政治和自由選舉,給老阿薩德30年鐵腕統治下專制僵化的敘利亞注入更多政治和經濟自由。在巴沙爾的領導下,敘利亞經歷了短時間的一段寬松期:數以千計的政治犯被釋放,新聞管制明顯放寬,集會和結社自由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放開……
在經濟上,巴沙爾雇傭了一批曾在美國留學工作過的精英人士和IMF供職的經濟學家出任內閣成員,明確宣布敘利亞將改革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推行私有化,走市場經濟之路……
當時這一系列“改革新氣象”被興奮的阿拉伯知識分子稱為“大馬士革之春”,明智的巴沙爾也很樂意自己被視為這場席卷全社會的“大馬士革之春”的催生者和贊助者。尤其受到阿拉伯世界青年歡迎的,是他在公眾面前表現出來的積極反腐的形象、務實親民的作風,以及對互聯網等現代科技的重視。
這位年輕的總統在就任之初便雷厲風行地打擊腐敗,剔除了不少老派官員,在很短時間內令老阿薩德留下的陳腐低效的敘利亞官僚體系有所起色。為了表現出不同于父親高高在上的威權軍人領袖形象,他在媒體和公眾面前一直都是西裝領帶,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銀行家或公司經理。他經常自己開車,甩開保鏢帶上家人到普通超市購物,或出現在尋常飯館里和老百姓聊天。他和夫人阿斯瑪還喜歡像西方人那樣,在周末帶著孩子,騎自行車去郊外野餐……這些都讓長期生活于政治上高壓專制的敘利亞乃至阿拉伯民眾備感耳目一新。
巴沙爾有一位頻繁出鏡的美貌妻子,這在保守閉塞的中東阿拉伯社會里顯得格外與眾不同,也給他的形象平添了不少柔性的光彩。她就是1992年巴沙爾在倫敦學醫時遇到的阿斯瑪·阿赫拉斯。
阿斯瑪出生于英國,擁有英國國籍和一部分英國血統。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在西方媒體眼里,這位喜歡時裝設計的敘利亞第一夫人是西方現代化與阿拉伯傳統完美結合的典范。對于那些熱切地希望巴沙爾成為改革者的人來說,阿斯瑪經常出現在鏡頭上的迷人形象強化了這一愿景。
但10多年后回頭再來看,巴沙爾沒有讓敘利亞人民過上好日子。他的那些改革被證明僅僅是浮于表面的,改革的步伐不僅緩慢,而且其中的大多數實際上在襁褓中即被扼殺,巴沙爾的統治面目也日益向舊式的“鐵腕”回歸。
在“大馬士革之春”的初期,巴沙爾曾親自組織了一個“改革論壇”,倡導執政黨和反對派、知識分子間的建設性對話。但是,當“論壇”的話題漸趨激烈且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執政的阿拉伯社會復興黨內部——表達出他們對這場“公民運動”的同情和關注之后,巴沙爾立即宣稱它破壞了“穩定”,并莫須有地指控運動背后有境內外伊斯蘭宗教極端分子的“敵對勢力”推手,隨即鎮壓了此次運動。那些幻想借“大馬士革之春”掀起一場更大規模的民主改革運動的興奮的知識分子不是入獄便是流亡,從此一蹶不振。
自那以后,巴沙爾本人的言辭也越來越謹慎,“民主”只是有氣無力的口頭愿景。此外,他還一再表示:敘利亞“優先考慮的是經濟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經濟上,敘利亞政府雖然引入了一些市場機制,放松了一部分管制,對某些領域實行了私有化,但它不愿意放開那些國有壟斷行業,向民間和外來資本提供平等競爭機會。這使得敘利亞盡管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增長,但大多數老百姓并沒分享到它的成果,貧富分化愈演愈烈,中產階級的財富迅速縮水,貧困人口的生活雪上加霜。到“阿拉伯之春”革命爆發前,敘利亞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兩美元。
一些觀察家相信,巴沙爾的改革之所以夭折,以至于敘利亞會淪落到今天這樣不可救藥的境地,是因為在這位年輕的西方流行文化愛好者背后,有著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和保守勢力——其中包括他的家族勢力——的羈絆和掣肘。執政至今,巴沙爾確實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推出過不少“新政”,但每當有風吹草動,他幾乎毫無例外地選擇了退縮。
但更多人認為,經過老阿薩德的精心栽培和10多年的執政,巴沙爾已經牢牢掌控了敘利亞政局的領導地位。他最初的那些“改革”只是他博取民心的策略,而在各領域掌握政治經濟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是支撐他時至今日統治地位依然穩固的根本力量,才真正與他坐在“一條船上”,也是他必須竭力拉攏的。
我深深地相信,上述兩者都說出了事實的真相,而且它們其實只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古往今來一切渴望有所作為的獨裁者,無一不試圖對每況愈下的現狀作出重大改變以圖振興,然而沒有一個改革者會想要通過改革來削弱自己的統治。而他們的改革能否真正取得作為,則取決于他們自己能否在這兩方面求得很好的平衡,將舊有體制所蘊含的正面能量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進而拓展體制的疆界。
“巴沙爾” (????,Ba??ār)這個詞,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帶來好消息的人”。但很遺憾,歷史將證明,一度幾乎集天時、地利、人和于一身的巴沙爾·阿薩德不僅是一個蹩腳的改革者,也是一個缺乏運氣眷顧的獨裁者。這位昔日的優秀學生和出色大夫沒能為自己和敘利亞開出一張治國良方,就像所有專制體制下的失敗統治者一樣,他的人生注定是一場贏家通吃和沒有退路的決斗。他通過一步一步的參與,主動或被迫地塑造并強化了這一罪惡體制,而他本人最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個千瘡百孔的罪惡體制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