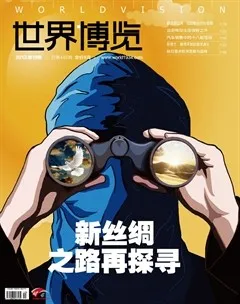無憂宮:腓特烈大帝的夏宮
“無憂宮”,這個名字對于那座位于波茨坦的宮殿來說真是恰到好處。宮殿的德文名字“Schloss Sanssouci”中,“Schloss”的意思是宮殿,“Sanssouci”則是法語“無憂、莫愁”的意思,從字面上一眼就可以知道宮殿名字的意義,念起來,每個字節在唇齒間跳躍著,清脆上口,但直到我親眼見到它的真容時,才能懂得何為無憂。
“我在葡萄山上的小屋”
無憂宮的宮殿坐落在一座小丘之上。與許多氣勢磅礴的歐洲宮殿略有不同,明朗的黃色外墻加上小巧而精致的外形,讓人第一眼看到時就有一種輕松愉悅的感覺。站在小丘上放眼望去,是沿著宮殿拾級而下,是一層層逐漸擴散開的葡萄山,種植著來自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國的葡萄藤,而在階梯中的168個玻璃罩子里面,則被種上了無花果樹。碧綠的葡萄藤盤纏在臺階的架子上,襯著在陽光下顏色顯得頗為嬌艷的宮殿,美得不可方物。
山下,羅馬神祗的大理石雕像圍繞著一座噴泉,不過無憂宮的主人腓特烈大帝卻從未能親眼看見噴泉噴水。因為在18世紀,還沒有足夠的技術讓噴泉噴出水來。今天,我站在噴泉的旁邊,也未能看到噴泉,但是平如鏡面的蓄水池卻讓葡萄山上的無憂宮能夠在水中顧影自憐,因此少了噴泉打擾反倒是一樁好事。“它是我在葡萄山上的小屋。”腓特烈大帝曾經這么提到他的夏宮,樸素的言語之間透露出的是一種喜愛之情。想來不管是站在小丘上望向遠處的樹林與風車,還是站在池邊欣賞兩重宮殿,觀者的心中怎會有憂愁駐足?更何況是作為如斯美景的締造者,心中的怡然自得可想而知。
腓特烈大帝既是普魯士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鐵血君主,在藝術上也頗有造詣。在對待這座宮殿與園林上自然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說這座宮殿是他個人意志與喜好的一個體現。宮殿的草圖乃是出自國王本人之手,而在建筑師根據草圖絞盡腦汁提出要建成一座巍峨磅礴的宮殿時,卻遭到了國王的反對——因為國王想要的,只是一座洛可可風格的一層建筑,能夠滿足他個人需求的私密居所,在這里,他可以很方便地就得以步下露臺,親近自然。此外,在追求藝術美感的同時,國王還非常講究實用性,比如在無憂宮旁邊就有一座菜園,方便這位喜歡吃新鮮蔬菜水果的君主的需求。
施工期間,國王還親自監工,不斷跟建筑師在細節上進行指示。在1747年宮殿尚未完全完工,腓特烈大帝就舉行了落成典禮,而且從此以后每年4月到10月都住在這里。法國大哲學家伏爾泰也曾是腓特烈大帝的座上賓,如今宮中伏爾泰的臥室與陳設還一如當日。不過貴婦就別想來享受無憂宮了,更不用說他那分居多年的妻子、能與國王住在這座宮殿者,唯有他所指定的男賓,以至于這座宮殿曾被戲稱為“無婦宮”。
風格混搭的宮苑
無憂宮景區占地面積290公頃,因此值得游覽的地方并不止無憂宮一座宮殿。游覽整個景區的最佳方式應該是騎車,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后世君王留下的中國樓、夏洛滕霍夫宮、新宮、橘園等宮殿散落在這片廣大的地方。而我這種隨性之人,也便只好問著路人,研究著沿途的地圖,靠自己的雙腿有多遠走多遠了。
中國樓是個讓中國人看了就有些啞然失笑的東西。所謂樓,其實是一座圓形的亭子,遠遠看過去疑似一個旋轉木馬亭。亭外,有著歐洲人想象中中國人的雕像。但實際上,它們完全是一些不知所云的形象,雕像上還鍍上了一層金,看上去更加詭異。腓特烈大帝向來對東方充滿向往,搜羅了大批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把這亭子也鍍金裝飾得無比金碧輝煌——大約是出自當時對中國遍地黃金的描述。所以,我們姑且理解一下當時人對神秘的中國那份難言的憧憬吧。
反倒是最后修建的橘園宮讓人又生眼前一亮的感覺。據說是威廉四世送給妹妹夏洛特和妹夫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驚喜,作為暖房和夏天的休息室。艷陽之下,高臺之上的宮殿,其風格在我看來頗具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阿拉伯風情,建筑物周邊種植的花草都與別處不同,加之宮殿名為“橘園”,實在是很有異國情調的一個地方。
比起無憂宮的精致,后來修建的新宮就遜色很多。盡管走在溪水潺潺,樹木肆意生長的林蔭大道上,忽然發現遠處林木中間出現了紅色宮殿的一角,煞是驚喜,但走進卻覺得有些乏味了。這座巴洛克風格的大型宮殿美則美矣,卻少了無憂宮那份靈氣。二戰的戰火在此也留下了許多的痕跡,燒成灰黑的雕像和仍然在整修中的宮殿,訴說著戰爭的殘酷,故而也再沒有“無憂”的心境了。